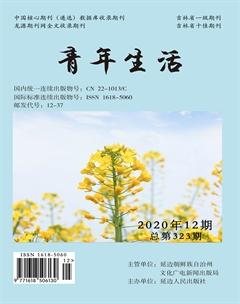論侵害生命權的精神損害賠償
薛童
摘要:本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闡明精神損害賠償的概念和功能,肯定以物質賠償對精神損害的可救濟性;第二部分,分析在侵權致死案件中死者和近親屬的法律地位,并對比域外求償權主體的劃定范圍獲得相關立法啟示。第三部分,借鑒域外立法經驗,提出適合本國國情的計算精神損害賠償金的原則和方法。
關鍵詞:精神損害;物質補償;人格平等
1. 精神損害賠償概述
1.1. 界定與功能
1.1.1 精神損害賠償的概念
各學術范疇都普遍承認精神歸屬于物質相對應的意識領域,是以社會存在為基礎的人的意識活動、內容和成果的集合。[1]法律保護相關主體在的生理活動、心理活動中的精神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在內的非財產利益。總之,精神損害賠償是民事主體在人身權益遭受不法侵害,而要求侵權行為人主要通過財產補償的方法予以救濟和保護的民事侵權賠償制度。
1.1.2. 精神損害賠償的功能
(1)補償功能[2]
侵權救濟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補償損害,精神損害賠償同樣突出地表現了侵權責任的補償性。損害事實發生后法律以其強制力要求加害人履行主要以貨幣為表現形式的財產性損害賠償,以此來補償直接或間接受害人所遭受的人身權益的損失。由于精神損害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不現實、不客觀的無形損害,而物質性賠償不可能也不能夠完全填平非財產性的精神損害,具有無法克服的局限性。
(2)預防功能
預防功能又被稱作為威懾功能。德國法學家馬格努斯認為“損害賠償金的威脅可以迫使潛在的不當行為人更加謹慎的行事以避免未來損害的發生。”[3]法律設定的條件與后果將使大眾對何種不法行為將承擔的相應法律后果有更為清晰的認識和判斷,并以此為標準規范和約束個人所做所為,對潛在的侵權人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
(3)懲罰功能
懲罰功能作用于做出侵權行為的一方,在填平受害人損失后額外追加的補償,實現懲罰加害人的目的。在精神損害賠償中“由于損害是難以量化的,對過錯程度的考慮本身就是賠償金帶有了懲罰的性質。”[4]對于重大過錯、主觀惡意較強的嚴重侵權行為加重處罰,利用自由裁量保障具體個案的公平公正。
(4)撫慰功能
主要針對受害人的心理、感情創傷的撫慰。在受害人的人身權益遭受不法侵害后,生理和心理上都留下了無形的精神創傷,影響了受害人的正常生活。“通過改變被侵權人的外部環境而克服其內環境即心理、生理以及精神利益損害所帶來的消極影響。”[5]受害人在獲得精神損害賠償后可以獲取專業的心理治療和物質享受,恢復飽滿的精神狀態。
1.2 精神損害與物質賠償的悖論
精神損害的賠償根本上是以客觀的、物質的財產性賠償來彌補主觀的、意識的精神損害。兩者在本質上的巨大的差異性引發了對于精神損害能否給予物質賠償的思考。人身權益是每個社會成員生存發展的基礎,而金錢作為商品市場的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當其被作為衡量人所遭受精神損害的尺度,曾被認為是對高尚人格的侮辱和踐踏。
伴隨社會經濟的發展,金錢越發普遍的被運用于解決民事糾紛,物質賠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精神損害的認識得以逐漸形成。沒有救濟的權利就不是真正的權利,法律尊重和保護人身權益,就必須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救濟途徑,而不能放任不管。“將生命喪失排除在可賠償的損害之外,與生命應受到最完善保護的法律政策完全相悖”[6]。精神損害賠償“使受害人在其他方面得到精神享受是唯一可以采用的是受害人得到滿足的方法。”[7]盡管制度的構建存在諸多障礙,但無疑是可行和必要的。
1.3 我國關于精神損害的立法
在擺脫對精神損害賠償的種種錯誤認識后,我國逐步嘗試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法律框架。《民法通則》中第一次間接確認了精神損害制度,但沒有將生命權納入法律保護的范圍。 此后,其他部門法中散見關于侵權死亡情形下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但稱呼各異,認定賠償范圍不一,計算方式不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精神損害賠償解釋》)中將受損的人格權、身份權納入精神損害賠償救濟的法定范圍。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人身損害賠償解釋》)中突出了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非財產性特征,確定近親屬有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救濟。2009年出臺的《侵權責任法》和《民法典侵權責任編(草案)》中明確規定了人身權益的精神損害賠償,肯定了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普遍適用性,但仍存在大量立法空白。
2. 侵權死亡的精神損害求償權主體
2.1 近親屬賠償請求權的基礎
我國法律承認和保護與死者近親屬因死亡事實而受損的精神利益,《民通意見》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在內。父母、子女為請求賠償的第一順位,其他近親屬為第二順位。
關于近親屬的精神損害求償權的法理基礎存在“繼承學說”和“固有學說”。[8]兩種觀點。“繼承學說”主張受害人生前合法人身權益受損時,受害人即刻擁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死亡事實又引起了請求權繼承的發生。“固有學說”主張近親屬是基于自身所飽受的生離死別的精神痛苦而享有賠償請求權,而并非對死者權利的繼受取得。相比之下,“固有學說”對近親屬求償權來源的解釋更具有說服力。“精神損害賠償應支付給受害人本人方能體現對其精神損害賠償的的價值,受害人事后死后死亡將喪失撫慰的目標”[9],即使瀕死過程中受害人的精神賠償請求權成立,但這種具有明顯人身依附性質的請求權不宜由其他任何主體繼承。侵害生命權的行為既剝奪了受害人的生命權利,受害人的近親屬而言無疑也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既要承擔可得經濟利益的喪失,又要承受生離死別所帶來的精神痛苦,近親屬本人精神損害的事實才是其獲得賠償請求權的基礎。出于人性化的考量,在瀕死過程中死者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可認定為加重近親屬精神痛苦的情節,作為衡量精神損害賠償具體數額的酌定因素。
2.2 求償權主體的范圍劃定
“死亡損害賠償應當反映一個家庭成員的生存對其他家庭成員的身份利益,應當對近親屬的財產損失進行補償,對精神損害予以撫慰,以填補因身份關系意外斷裂而產生的利益真空。”[10]基于社會現狀、法治理念等差異化因素,各國立法及司法實踐對求償權主體范圍作出了不同的劃定。
2.3“狹義”與“廣義”的近親屬
狹義的近親屬指與受害人最親近的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美國大部分州的立法中都承認近親屬有權因喪失親權獲得賠償。包括失去的相互間的情感交流、應有的關懷等精神活動的缺失和痛苦,“將法定受益人局限在很小的范圍內,甚至有些武斷的進行劃分和認定。”[11]從案件的處理結果上來看,將有權獲得精神損害賠償的近親屬限定于死者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廣義說下的近親屬還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等,希臘法律甚至將范圍擴大一切與受害人有親近關系的親戚(如岳父母),存在認定范圍略寬的問題。
2.4事實上存在的親近關系
有些國家更加看重個案的情形,以相關主體是否真正具有與受害人頻繁真摯的感情溝通和穩定的親近關系作為精神利益是否受損的依據。在法國的實務判決中檢驗求償權主體是否適格的標準,是以受害人的真實生活狀態去觀察,而不是以表面上依托法律建立起來的親近關系。受害人的合法配偶也可能因長期分居、感情完全破裂、不忠誠等實際情況而無法取得精神損害賠償,而在一定程度上違背道德要求的非婚同居伴侶,基于長期親密而穩定的陪伴而有權求償。[12]筆者認為應否定非婚同居伴侶的死亡精神損害求償權,否則不能體現法律對合法配偶關系的尊重,違背社會的法感情,不利于維護正常的家庭內部秩序。
2.5其他判定標準
在美國的一些州立法中,侵權死亡的精神損害求償權主體還需要滿足特殊的“現場性要求”,只有目睹死亡事故過程的在場近親屬才有權提出賠償的請求,大大降低了對死者近親屬精神損害進行救濟的可能性,并且是非常殘忍的。另外,以德國、奧地利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提出只有因受害人的死亡而導致必須接受治療的精神疾病患者才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對精神利益的保護程度過于落后。
3. 侵害生命權的精神損害賠償金計算
3.1 域外可借鑒的原則及方法
3.1.1. 美國法:最高限額原則
美國法確立了精神損害賠償的最高限額原則,明確設定針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最高數額上限。聯邦政府以及各州立法對該限額的上限存在兩種規定方法:一是規定單一精神損害項目賠償的最高限額。如1986年佛羅里達州的一項法令中規定對痛苦的賠償數額上限為45萬美元;二是針對某幾個項目作為一個整體的所有精神損害賠償金規定最高限額。如1986年里根提案中將身心創傷、精神痛苦、感情不幸以及伴侶喪失等精神損害數額限定在10萬美元以下。[13]從案件的處理結果上來看,受害人往往能得到巨額的精神損害賠償。
3.1.2. 日本法:定額化賠償與限幅數額
日本法學家西原道雄反對當時實務屆以財產經濟補償作為侵權死亡賠償的核心部分,認為這是將人格物質化的表現。“差額說”下的可得利益的計算往往會因為偶然因素而不能達到適當補償的效果,有違人格平等的原則,應將賠償進行定額化。[14]在定額的基礎上綜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過錯、經濟狀況等因素,由法官裁奪確定一個合理的賠償數額,以謀求個案公平公正的處理結果。日本法在此后了制定數額明確、固定的賠償金表以及各類精神損害的上下限幅賠償額。
3.2 精神損害賠償標準的立法啟示
我國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忽視法律對于精神領域的調整,精神損害數額普遍偏低。另外在賠償數額上缺乏明確具體的計算標準,自由心證下的裁量空間缺乏一定的法定限制,個案的判決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專業素養,我國良莠不齊的法官隊伍恐難以擔此重任,個案的公平正義難以得到切實保障。另外,過分追求個案的的獨特性進行衡量會導致司法效率低下,大量案件堆積,并且不可避免的出現相似案情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差距懸殊的尷尬局面,整體上的公平正義也難以實現。
大眾對于精神人格平等的訴求應該體現在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構建當中,我們所期望的統一性、平等性,在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中更容易尋找到一片適合的土壤生長,一個“全民大體相當的賠償數額”是經得起推敲的解決方案。不能認為死者因年齡、受教育程度、收入狀況、戶籍等存在差別,導致其近親屬的損害程度不同。情感是相通的,死亡對近親屬所造成的精神損害在很大程度是接近的,則大致相當的精神損害的財產性救濟應當可以確定一個基本一致的定額,筆者認為20萬元的賠償數額是比較合理的。同時,基于個案結果合理性的考量,采用限幅數額的原則,明確法官可以根據已查明的事實情況在定額上下30%以內進行變動。建議可通過分析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情節判斷過錯和惡意程度。其次考慮當地的經濟水平和當事人雙方的經濟能力,不過分加重侵權人的經濟負擔,增強判決實際履行的可能。
4. 結語
生命已逝,但非萬事皆休,推動侵害生命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走向成熟是法律制度設計體現精神人格平等的踐行。應當立足我國國情,承認精神損害的可救濟性,借鑒域外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經驗,確定合理的求償權主體范圍,提高賠償數額,建立統一的限幅定額化精神損害賠償標準。
參考文獻:
[1]王利明主編:《民法·侵權行為法》[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2][德]馬格努斯主編:《侵權法的統一:損害與損害賠償》[M],謝鴻飛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3]王軍:《侵權損害賠償制度比較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4]宗志翔:《侵權責任與賠償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5]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6][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下卷)[M],焦美華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下卷)[M],張新寶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宗志翔:《侵權責任與賠償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9][日]加藤一郎:《撫慰金比較研究》[J],《比較法研究》1982年版.
[10]孫啟福《死亡賠償制度的嬗變及反思——以死亡賠償金及精神撫慰金為視角》[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
[11]張新寶、郭明龍:《論侵權死亡的精神損害賠償》[J],《法學雜志》2009年第1期.
[12]趙敏:《近親屬請求死亡賠償的法理基礎》[J],《公安法治研究》2010年第4期.
[13]胡筱芳:《美國侵權法上不法致死的賠償》[A],載王軍主編:《國際商法論叢》(第九卷)[C],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4]劉士國:《論人身死傷損害的定額化賠償》[J],《法學論壇》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