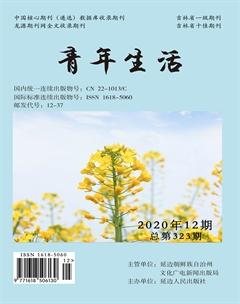離去是自我的救贖
戴鑫源
摘要:“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寥寥幾字概括出作者來著凡人世間一回,并未感受出這世間的美好。在這種沉郁絕望的創(chuàng)作基調背后,潛藏著其本人獨特的審美態(tài)度。那便是“真情流露”物哀文化。同樣正是在這種傳統(tǒng)審美意識的影響下,再加上作者個人經歷,終于外化為作者“向死而生”的文學訴求。
昭和不滅的金字塔
太宰治的活躍時期,正是二戰(zhàn)前后日本社會動蕩不安,民生凋敝的復雜時期,也是對明治之后接受西方思想文化洗禮的大反思時期。這個時期的日本,不僅有著未遭覆滅的封建貴族思想的殘余,也蔓延著西方各種文化思潮,而左翼運動和共產主義思潮也沖擊了日本傳統(tǒng)社會。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tài)交織于這一狹窄的歷史空間中,孕育了諸如太宰治這樣一位特立獨行的作家。
太宰治是日本戰(zhàn)后“無賴派”的代表作家,原名津島修治。津島家當時是津輕首屈一指的大地主,父親雖然屬于貴族階級,但母親體弱多病,太宰治自小便在親戚照料下長大。父親的嚴厲與母愛的缺失造成了他敏感脆弱且憂郁的的性格特征,他的童年并不快樂。“我偽裝成騙子,人們就說我是個騙子。我充闊,人人以為我是闊佬。我故作冷淡,人人說我是個無情的家伙。然而,當我真的痛苦萬分,不由得呻吟時人人卻認為我在無病呻吟。我想和那些不愿受人尊敬的人同行。不過,那么好的人可不愿與我為伍。”這是太宰治在《奔跑吧,梅勒斯》一文中所說的,這句格言式的話語恰好成了太宰治人生和文學的最好注腳,也從某個角度勾勒出了他一生的心理軌跡。而太宰治的文學也大可分為三個時期。
1.頹廢叛逆
這一時期與作者年少時期的經歷分不開。代表作品有《魚服記》,講述津輕的花季女孩諏訪與父親在荒無人煙的山林中過著貧苦的日子,因被父親強暴而投河自殺,本以為能化作一條大蛇逃離令他煩惱的塵世,但沒想到她卻化為鯽魚,最終吸入潭底的漩渦的故事。《魚服記》當中的諏訪,本來是沒有自我意識的,但是當目睹了一個學生失足跌入深潭后掙扎的情形后,她開始對生命的本質有了困惑,進而產生了對生存意義的質疑:
“爸爸!諏訪叫道:你活著是為了什么?父親疑惑地聳聳肩膀,看了看諏訪認真的臉龐,喃喃地說:我也不知道。諏訪一邊咬著芒果的葉子,一邊說:那不如去死好了!”
這看來是不經意的少女的童稚之言,卻蘊藏著諏訪內心深處自我毀滅意識。在遭受父親強奸后,她終于投身于深潭之中化作了一條鯽魚。對此,日本學者淺野三平指出:“變形或許是人類心底隱藏的愿望。”因為人們將變形視為自由,解放,象征著從壓抑的現實逃離。在回到作品中,從擁有毀滅意識的主人公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方式下走向自我毀滅,繼而以變形的方式獲得了重生。
2.積極輕柔
《奔跑吧,梅勒斯》是他中期作品當中的代表作之一,講述了為了給妹妹慶祝婚禮的梅勒斯前往都城,卻聽說這里的王因不信任人而殺人的事,單純正直的梅勒斯為了鏟除王而夜入王城,不久被縛。隨后他請求緩刑三天以回家舉辦其妹妹的婚禮,條件是以摯友賽利奴第烏斯為人質。并在遭遇困難之際懷疑過是否要背叛自己的摯友,最后選擇堅信友情。這部作品是太宰治少有的明朗健康之作,但“死亡”這一太宰治文學的永恒主題,依然占據著這篇小說的主線。主人公梅洛斯在得知國王暴虐殘忍之后,決心除掉國王,在被逮捕之后,國王出于假意,同意梅洛斯將朋友作為人質來交換自己三天的時間,如果3日之后梅洛斯未曾歸來,國王將下令處死他的朋友。在歸來途中,梅洛斯明知前方是死亡,但毅然決然地奔赴約定。自始至終,梅洛斯就具有死亡的意識。在被逮捕指出,面對國王的詰問,他豪言“其實我已經做好了赴死的準備,絕不會乞求活命的!”而在準備奔赴諾言的途中,“我今天晚上就會被殺死!我是為了赴死而奔跑!”他的死亡意識并非為了自我毀滅,而是為了朋友的信念和對人性美好的信任。因為在途中他屢有動搖的想法時,他及時地摒棄了那些想法。最終,在趕到刑場時,他由與死亡角力的過程中獲得了重生的洗禮。最后在面對無畏死亡而一心向死,只為證明誠實守信的存在的梅洛斯,他終于獲得了救贖;“你們戰(zhàn)勝了我的心!城市絕不是空虛的妄想!”
3.自我毀滅
1946年在給其師井伏鱒二的信中,太宰治首次提出“無賴派”這個字眼,可以說奠定太宰治在日本文學歷史上地位的作品,幾乎都是出自后期。《人間失格》正是這個時期的作品。《人間失格》全作由作者的序言,后記以及主人公大庭葉藏的三篇手記構成。描寫主人公自幼年至中年,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毀滅的深淵。文中葉藏以酗酒,自殺,藥物麻醉等種種方式放逐自己,逃避與世間事物的一切聯(lián)系,是一個極端充滿毀滅意識的人物。在大庭葉藏的身上,“道化”體現的淋漓盡致。由與深重的死亡意識和生存的消極反抗,葉藏選擇了自我毀滅。“我已經喪失了做人的資格!”葉藏的毀滅是由心到體的漸進過程。而他的重生亦是建立于自我意識的毀滅中的。在經歷多次的信仰破滅之后,葉藏感慨:“只是一切都將逝去”。這正是他重生的開始。唯有直面死亡,才能獲得美的重生。在小說的后記中,酒店老板娘稱葉藏為“神一般的好孩子”。而這正是太宰治“向死而生”的審美觀使葉藏在美的層面獲得了重生。
斜陽下永恒的余暉
日本四周環(huán)境之美,氛圍之美,這些真實與虛擬的美,就是物哀文化。“悲與美是相通的”,這是物哀文化強調的重點。有一個詞叫做“邊緣人”,指的是精神上的先行者,有自己獨特的思想與信念,也因為其思想與信念的獨特,使得平常人對其行為活動等難以理解。太宰治通過日本傳統(tǒng)的“私小說”形式,創(chuàng)作了大量關注邊緣人物的小說,也可以說這些邊緣人物其實就是太宰治自己,小說中的文字其實就是太宰治自我的告白。日本文學評論家奧野健男評價太宰治曾說:“無論是喜歡太宰治還是討厭他,是肯定他還是否定他,他的作品總擁有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在今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筆下生動的描繪都會直逼讀者的靈魂,讓人無法逃脫。”
總的來說,太宰治作品中的“向死而生”的審美訴求,從對現實生活的恐懼,到生而為人的虛無感負罪感,因抓不到生活的意義而墮落頹廢,終至死亡,這便是太宰治文學的整體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