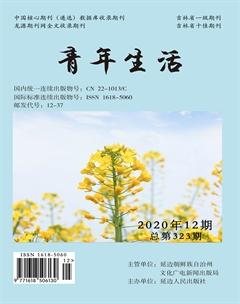從文本《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看傳記批評
曹顏佳
摘要:傳記批評認為 “作者是文本之父”即作品的生命是作者賦予的。若從傳記批評的角度審視《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便會察覺文本相當程度上觀照了茨威格的現實經歷 , 但創作者的生命境遇更是彼時政治、經濟、文化語境共同的產物。本文擬參照茨威格感情經歷及同時期作品對文本《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進行解讀,對茨威格的創作動機和作品意義作出闡發。
關鍵詞:傳記批評;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社會歷史
一、茨威格生命中的兩個“陌生女人”
所謂傳記批評, 即是說一位讀者在作家—作品—讀者的系統中,站在作品之外,通過研究了解作家出發對作品進行讀解。讀者在解讀、 研究作品時 , 要仔細全面了解研究作者生平 、創作經歷 、創作目的、人格乃至生活態度等傳記性材料,然后對照作品,從中挖掘相關內容 , 達到對作品蘊含意義的真正理解 。
茨威格的個人經歷及情感態度便顯然投射在他蜚聲國際的著名短篇《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文本中的陌生女人身上帶有他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和巴黎情人馬塞爾的影子。
男主人公R作家則與茨威格有諸多相似之處。二者的出身、教養、職業的相似:英俊外表、富裕家庭、優雅談吐。甚至茨威格人生中也有相當時長是游歷花叢的浪漫主義者。兩者同樣有性格中的相似性:“你既是一個輕浮、貪玩、喜歡奇遇的熱情少年,同時又是一個在你從事的那個藝術方面無比嚴肅、很有學問的長者。”[1]R作家對自由的絕對要求都指向了茨威格本人的價值觀和對生命的理解。
而弗里德里克就是那個寫信的陌生女人,她內外兼修,對茨威格可謂深情。難得的是她的愛秉持“我愛你,與你無關”的態度,甚至對茨威格和巴黎情人馬塞爾糾纏的事也抱以足夠的寬容“無論從你那兒來的是幸福還是苦難,我對這兩者都已歡快的下定了決心。你用不著愛惜我,我是堅強的。”[2]多么像陌生女人——“我不埋怨你,我愛你,愛的就是這個你:感情熾烈,生性健忘,一見傾心,愛不忠誠。”[1]甚至弗里德里克對女兒患病的內心焦灼都與陌生女人相似。
茨威格像R一樣,四處游歷,讓弗里德里克無盡等待,在巴黎和女帽師情人馬塞爾過著銷魂蕩魄,激情如熾的生活。甚至兩人企圖擁有共同的孩子,因為馬塞爾“最想有個孩子,為了從頭開始再活一次,全身心地獻給這孩子…”[2]而茨威格對這樣坦率的女子懷有無限敬意。驚人的美貌,如熾的激情,甚至重見茨威格時“高興地發抖”…這些都與那個陌生女人相似。由此可見,文本故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兩位情人和茨威格本人的現實糾葛的文學再加工。
認識R之前,陌生女人的孩童時代是“陰凄凄、亂糟糟的一團, 它像一個地窖, 堆滿了塵封 霉濕的人和物, 上面還結著蛛網, ”[1]而弗里德利克在遇到茨威格之前 , 生活也平淡得令人乏味,盡管她的個人條件及家世已領先同時代的大多數女性。和官員溫特尼茨的結合未曾帶給她快樂, 兩人存在不可調和的價值觀和興趣的差異。弗里德里克在1912年7月25日寄給茨威格的未署名的信,也從現實蔓延到了創作中。但現實中,兩人開始了相識相知相戀的過程,而故事中,作家對此這個陌生女人一無所知。
R從未認出過這個陌生女人,盡管她已經生下了R的兒子,她平靜接受他的忘卻, 安靜等待機會。陌生女人一直未婚, 這樣就能隨時回到 R 的身邊,她無怨無悔。弗里德利克和陌生女人類似, 面對愛情的消逝沒有自怨自艾, 同樣平靜接受。弗里德里克從容、令人激賞, 她和茨威格保持住了感情最初的體面與優雅, 茨威格過世前仍然在和弗里德里克通信。
由此可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的文本內容與茨威格情感經歷具有高度相似性,但讀者在閱讀之中既要站在作品之中也要跳出作品之外,陌生女人不等于弗里德里克,R作家也不等于茨威格,畢竟小說的創作動機不在于自敘羅曼史,讀者應從更深層的歷史語境下來觀照作品人物及內涵。
二、重返奧地利的復雜心境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出版于1922年,這一別開生面的愛情故事,確實是文學羅曼史上不可多得之作。3而作為一戰的親歷者、歐洲文明的堅定捍衛者、奧地利帝國的子民,茨威格為何在這時創作出一篇仿佛是映射私隱的羅曼故事呢? 創作動機又是什么?筆者試圖參照同時期作品來了解小說的創作動機。
《馬來狂人》作為茨威格同時期的作品,主人公德國醫生也和陌生女人一樣,是極端情感的個例。文中的醫生曾經供職于萊比錫醫院,本來前程遠大,卻因為一個女人而斷送了自己的事業和聲名。《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的陌生女人瘋狂地愛著對她寡情的R直到燃盡生命。兩者都結局慘烈,殉了內心的至高理想。
《瑪麗恩巴德悲歌》也是茨威格此時期的短篇傳記作品,文本書寫了歌德晚年在告別愛情后轉向自身,將畢生的理想,追求,執著熔鑄成不朽的史詩之作——《浮士德》的故事。茨威格在一戰期間及一戰后還完成了《三大師》人物傳記,在薩爾茨堡作的序中明確表達了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他心中的三位19世紀最偉大的長篇小說家,他試圖不談政治轉向為偉人作傳,在歷史中尋求自身。在復雜的現實語境中,同時期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顯然不只是一個羅曼故事。
茨威格在一戰結束后返回奧地利,這似乎是一個艱難的決定,這從《昨日的世界》中可見一二。[3]他面對奧地利動蕩的政治經濟環境:一戰蹂躪后百廢待興,呈現無秩序混亂狀態,“我又從和平的環境回到戰爭的恐懼中——而所有的人都以為戰爭已經結束”[3]政黨共存,國家也處于獨立與不獨立的尷尬境地。經濟秩序更是混亂:物資匱乏、通貨膨脹,人們甚至倒退到以物易物的狀態,外國人蜂擁而至在奧地利的混亂中再攪和幾把。可怕的是,人心也混亂了:“世德不存,唯有這樣一條準則:隨機應變、八面玲瓏、無所顧忌。”[3] 而在這混亂的三年中,茨威格筆耕不輟。筆者以為,外在世界的搖搖欲墜更使茨威格關注起內在之物,唯有精神力量,生存意志能支撐人們橫過的歷史。茨威格看到人們要求生活連續性的意志遠遠勝過貨幣的不穩定性,人們開始更看重生活的真正價值,比如關于工作、愛情、友誼和自然風光。人們也同樣意識到唯有藝術才能永恒。
茨威格由此意識到一個民族所需要構筑的強大的精神
(下轉442頁)
(上接441頁)
世界,筆者以為這也促成他創作《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文中陌生女人對至高愛情理想的不懈追求,正如奧地利人民的生存意志一樣強悍。
三、陌生女人與隱喻
戰后的世界也不可避免地迎來了文化轉向:青年人們決定不受任何傳統的束縛,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走向未來建立新秩序。周圍的一切都染上激進、革命的色彩,各個藝術領域都開始了大膽試驗。奧地利帝國的“尊崇年老”傳統也向“認可年輕”轉型。茨威格也看到了這些變化,還有其中蘊藏的一些不理智,他決定回到自己的書齋安靜寫作,并開始反思自己的早期唯美主義創作傾向:“這樣一個糊弄自己的年歲已經過去。我已人到中年,不再是光許愿的年齡”。[3]種種因素都促成了茨威格本時期作品內轉,包括當然包括《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筆者以為《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還包含著作者對帝國消逝的隱喻:陌生女人對R一生追隨,直到水落石出,直到一生凋零。追到R終于知曉了她,終于在R身上刻下印記:“他感覺到一次死亡,感覺到不朽的愛情:一時間他心里百感交集,他思念起那個看不見的女人,沒有實體,充滿激情,猶如遠方的音樂。”[1]這是對一種崇高的體驗,茨威格贊美她,懷念她,正如他對古老奧地利帝國逝去的傷情。
茨威格出生成長在奧地利帝國的文化鼎盛時期,深受熏染。他也在戰后歸國途中,看到奧地利帝國的最后一位繼承人被驅逐出境。這是一代古老帝國的落幕,也是一段歷史文明的落幕。誓要打破老舊的共和國的年輕人,不會明了自己揮別了一段怎樣的文明閃耀的歲月。歷史讓茨威格感受到了失落,還有“生命不可承受之輕”。
綜上所述,在傳記批評的視野下看待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一方面它為我們提供一面鏡子,使后世讀者可以借此管窺茨威格的內心或真或假的一面;另一方面,現實語境又對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對思想內容的的選取和表達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們借助作者的經歷對作品有了更深一層的解讀 , 同時也反過 來在對作品新理解的基礎上對茨威格本人產生了新的更豐富深刻的認識 。
參考文獻:
[1][奧]茨威格著,張玉書譯.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M].上海譯文出版社.
[2]張玉書.茨威格評傳:偉大心靈的回聲[M].高等教育出版社.
[3][奧]茨威格著,舒昌善,孫龍生,劉春華,戴奎生譯.昨 日的世界—歐洲人的回憶[M].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