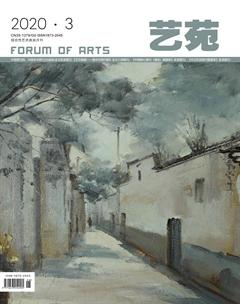從科學普及到中國特色
【摘要】 從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西方典型科幻主義結合的角度入手,剖析我國科幻電影的演進走向與未來發展,考量中國國情與東方傳統文化對科幻類電影的雙重關系與互動,并在此基礎之上探究中國科幻電影《流浪地球》中西方科幻元素與傳統中國文化的結合。”
【關鍵詞】 本土科幻電影;傳統文化;文化結合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一、中國科幻電影之起源
中國科幻電影的發展,始于20世紀60年代第一部科幻影片《小太陽》的上映。電影講述一群北方的孩子探討如何讓春天來得更早一些,在科學家的幫助下,他們造出了小太陽并發射到了太空,春天提前來臨了。事實上,該片在當時并未被看作是科幻電影,而是被歸為科教片的范疇。影片的科學氣息非常濃厚,這在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也引發了大眾對科學技術的思考,但是作為一部真正的科幻電影,影片缺失了對社會現實的反映,憑空虛構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世界,難以引起觀者的共鳴。從科幻電影的源頭——科幻文學的角度來看,60年代正處于中國科幻文學發展的“第一時期”[1],本土科幻文學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傳播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其創作思想強調功能性而忽略文學性。受科幻文學作品的影響,許多科幻電影的創作過程中也存在類似問題。如上述《小太陽》等都具有脫離社會實際等一系列“硬傷”,難以看作是真正的科幻電影。
20世紀70年代上映的科幻片《生死搏斗》與《珊瑚島上的死光》代表了我國在科幻電影方面取得的初步發展,此時本土科幻電影開始與社會形態和現實人性結合。前者反映主人公不畏強權、勇于抗爭的精神;后者表現了科學家熱愛祖國、愿意為科學事業獻身的一系列優秀品質。隨后80年代,本土科幻片《錯位》《霹靂貝貝》等科幻作品登上銀幕。但從90年代初開始,本土科幻電影變成了鳳毛麟角般的存在。在這期間,整個中國也只有《紫雨風暴》《再生勇士》等寥寥十幾部科幻片。[2]縱觀20世紀整個中國科幻電影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其主要呈現出一個起伏不定的狀態,沒有取得根本性的成就。從數量上看,對比國內每年平均五、六百部的電影產量,科幻片在其中所占比例較低。從作品本身看,本質上是對西方科幻電影的模仿。類型片的區別在于風格、題材和價值觀念方面各有一系列的程式[3],科幻片作為一種大類型片也有其“程式”,而中國在20世紀上映的大部分科幻片都是使用西方的固定“程式”,沒有對其做出突破。20世紀本土科幻電影創作者們沒有拍攝出真正的中國式科幻電影,沒有發展出屬于我們自己的科幻電影“程式”。
二、中國科幻電影的障礙與突破
多年來,西方國家為何可以拍攝出大量膾炙人口的科幻電影,乃至使其成為一種熱門的主流電影派系,而在中國科幻類題材卻鮮有佳作?從國情上看,中國社會對電影主流觀念與西方科幻片的思想存在差異。20世紀國內的許多優秀電影作品大多是表現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訴求,而西方科幻作品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那么看重,反而更加強調人與自然以及客觀世界的關系。就像凡爾納的多部小說改編而成的科幻電影一樣,觀眾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人類對未來和外部世界的渴望,而不是東方人所習慣的細膩情感表達。從另一方面看,中國導演以及市場對電影往往強調其現實意義,而不是其娛樂審美功能。
還應當指出,20世紀一些科學技術特別是工業設計領域的落伍成為了中國科幻電影發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礙。眾所周知,20世紀我國科技領域的許多技術較西方落后,其中自然包括了科幻電影所必須的一些相關技術。中國想要拍出大型科幻片的“硬件條件”先天不足。另一方面,滯后的科學技術也極大地限制了創作者的“科幻想象力”。“科幻片”的定義是:“以科學幻想為內容的故事片”“其基本特點是從今天已知的科學原理和科學成就出發,對未來的世界或遙遠的過去的情景作幻想式的描述”。[4]這個定義表明了科幻片中的想象其實是對已有的現代科技的合理推演,科幻電影創作者們在創作中的想象力都是建立在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基礎之上的。
不僅如此,西方國家的歷史相對較短,其大多是海洋文明或是殖民建國,基于此西方國家難以追溯自己的歷史,相比回憶他們更愿意描繪一個未來,所以才可以孕育出如此之多優秀的科幻電影作品;而東方文化悠久的歷史在給予我們創作靈感的同時,也使我們的思維習慣于追溯過去,難以表現出一種狂放的現代性。更進一步而言,東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之處決定了傳統“西方式”科幻電影難以在中國得到良好的發展。西方文化帶有著主觀意識來建設改造客觀世界的目的性,如西方最早的文學作品《奧德賽》,這本書重點反映出的是“經幻想加工過的自然現象以及古希臘人同自然的斗爭和勝利”[5]。從中不難看出西方文化自起源就將人與自然世界看為兩個獨立的個體,在兩者存在沖突時西方人勇于斗爭,斗爭的結果則通過科幻作品來表現,這是人基于現實對未來做出的合理想象,它可以是美好的也可以是具有警示性的。相比較下,東方文明從未將自然與人看作是相互獨立的事物。就像中國文化體系起源中的“道”,它是指世間萬物都具有的一種共同規律,而“中國人認識這種規律所使用的方法是‘取象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6],即以身體和自然世界為源抽象出一些圖形或文字。中國文明中最基本的“道”就是我們從人類性別器官上所提取出的乾坤兩卦,這種“道”存在于世間一切事物之中。由此可見,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沒有將人與自然割裂開來,人與自然具有同樣的“道”,兩者之間沒有本質沖突,科幻作品從現實意義上來講缺乏產生的條件。伴隨著改革開放,西方科幻電影的引入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在這些背景條件下,國人應對這種變相“文化入侵”的方法只能是拍攝出真正屬于自己的科幻大片,發展出一套完整的中國特色科幻電影體系。而深刻在國人骨子里的懷舊情懷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的統一性,這些與西方有根本區別的意識形態其實正是我們建設這一體系的根本價值所在。
三、從《流浪地球》看科幻電影的新思路
2019年《流浪地球》的橫空問世代表了東方思想與西方視效的成功融合。《流浪地球》與其他的一些好萊塢科幻片的設定一樣同樣是地球面臨毀滅、人類尋找新的家園,但卻是第一個人類逃亡帶上地球的,這是與西方科幻的不同之處,也是東方文化中“故土難離”的體現。很多的國家和文化都會對自己的故鄉有特殊的情感,在中華文化當中這種情感體現得尤為明顯,電影中的一句話“人類在宇宙間離開了地球,就像嬰兒在沙漠里離開了母親!”,其中所包含的情感與“明月何時照我還”等中國傳統詩詞的表達無二。對待“家”這個話題,我們相對比較“保守”,西方人則更加靈活變通。《流浪地球》與西方同題材科幻片《星際穿越》(2014)相比較,一部是中國科幻的崛起之作,一部是西方科幻的傳統代表,后者的主題和《流浪地球》非常相似,但在面臨同樣是地球出現危機的問題時,該片中的人類卻是通過一艘宇宙飛船來尋找新的星球完成人類遷徙,而且影片后面情節也未再涉及地球,顯然創作者忽略了地球的故鄉性質。其次,橫向來看《星際穿越》的劇情中除開地球,共涉及到兩個外太空星球以及一個黑洞,后三個地點是影片中主要情節的發生點,而地球只是起了一個故事引入及情節推動的作用,所占篇幅遠不及這三個地點。由此可見,地球本身在影片中的重要性較低。該部影片所突出的是“尋找家園”而不是《流浪地球》中的“守護故土”。通過上面的分析論證,很明顯發現西方傳統科幻作品與中國科幻作品在“家”這個問題上處理的根本性不同,這種獨特的家園情結是整個東方文明體系下的人們心中的共鳴點。
值得一提是,除了故土是家的組成部分,親人同樣也是家的一部分,相較中國對家庭觀念的注重,《流浪地球》中祖孫三代齊上陣的情況在西方電影中很難見到。西方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決定了他們不依附家庭,而是傾向于一種自我依賴。以《星際穿越》為例,從影片主要人物結構上看,《星際穿越》中有庫珀、艾米莉亞、墨菲、布蘭德教授,其中除庫珀與墨菲是父女關系之外,其余人之間均無血緣關系,而是工作伙伴或戰友。作品是以庫珀為紐帶將墨菲與布蘭德、艾米莉亞聯系起來組成主要人物結構的,影片中既體現了父女親情,也體現了友情與愛情,整體而言是混合的情感。對比《流浪地球》,劉培強、韓子昂、劉啟、韓朵朵四人之間既是故事主要人物,又組成了一個傳統的東方式家庭,影片中所體現的情感整體來講單純性更高,重點表現了父子情、爺孫情、兄妹情三方面,這與中國人數千年來傳統思想中的大家族情結的共鳴度極高,充分展示了一個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下的科幻片角色結構的新模式。
結 語
20世紀,由于西方傳統科幻電影的沖擊,中國科幻電影發展趨于緩慢,直至改革開放后,電影創作者們逐漸從科學普及的中心視角轉移到人性與現實上,才使得本土科幻電影有了新的發展態勢,但直至20世紀結束也未拍攝出真正能夠引起本土觀眾共鳴的中國式科幻片,其創作思維仍停留在模仿西方科幻電影的定式之中。其原因既有國情的影響,也有東方傳統文化特點的因素。到了21世紀,創作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東方式科幻電影是本土科幻電影發展的出路。《流浪地球》的成功展示了本土科幻片的一種新思路,影片之所以能夠贏得觀眾的認同,在于其將西方科幻文學與中國傳統思想體系融合。任何文化體系都有自己的發展方式,不同地區應該體現文化上的異同,想在影片中體現中國色彩,創作者在進行本土科幻作品創作時就必須具有傳統意識,進行“東方式”的思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創作出引起本土觀眾共鳴的上佳作品。
參考文獻:
[1]孟繁博.科幻文藝對科學文化傳播的現狀及對策研究[D].大連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2]盤劍.國產科幻片闕如與中國電影發展之“坎”[J].電影新作,2013(6).
[3]路易斯·賈內梯.認識電影[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7.
[4]許南明.電影藝術詞典[K].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
[5]朱維之.外國文學簡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6]陳兵.佛教心理學[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作者簡介:婁胡恩,四川大學電氣工程學院學生,研究方向是海上風電功率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