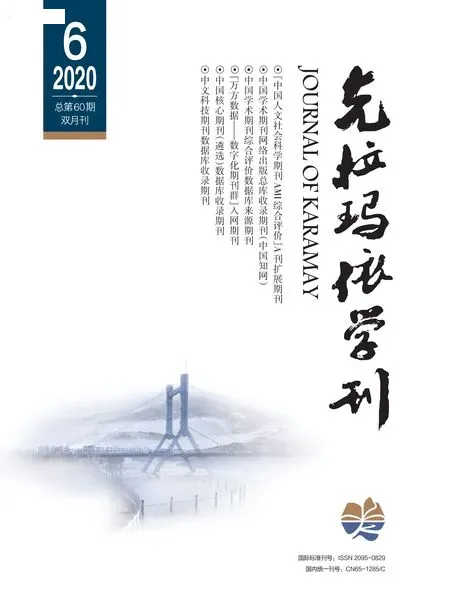當(dāng)代精準(zhǔn)思維的三重維度分析
周金鳳
(中共北京市物資總公司黨校,北京 100053)
精準(zhǔn)思維既是一種分析的思維方式,又是一種務(wù)實(shí)的工作態(tài)度,在2020 年9 月8 日的全國(guó)抗疫表彰大會(huì)上,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指出我們?cè)诜酪咧小熬珳?zhǔn)管控”“精準(zhǔn)復(fù)工復(fù)產(chǎn)”[1]。“精準(zhǔn)”不僅是防疫取得成效的重要手段,也被證明是精準(zhǔn)扶貧的有效方式。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多個(gè)場(chǎng)合提到做事要“精準(zhǔn)”。如果我們?cè)诠ぷ髦袧M足于一般化,滿足于差不多,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不能解決真正的問(wèn)題。筆者認(rèn)為,精準(zhǔn)思維有著歷史發(fā)展與時(shí)代進(jìn)步的要求,還有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指導(dǎo)下的科學(xué)性,而在具體實(shí)踐中,我們首先要樹(shù)立務(wù)實(shí)意識(shí),才能發(fā)揚(yáng)精準(zhǔn)思維、運(yùn)用精準(zhǔn)思維。
一、歷史維度:精準(zhǔn)思維方式是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新超越
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關(guān)注整體和直覺(jué)邏輯,這種思維方式創(chuàng)造出了一系列發(fā)明,卻存在對(duì)科學(xué)的綜合分析不足。雖然近代以來(lái),中國(guó)傳統(tǒng)方式經(jīng)歷了向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變革,但思維方式對(duì)一個(gè)民族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今天,我們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也難以避免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影響。比如某些情況下,在工作中偏重于整體性而忽視對(duì)事物內(nèi)部細(xì)枝末節(jié)的分析,不注意分析的工作方法,認(rèn)為做事“差不多”即可,對(duì)待工作大而化之,對(duì)待不同的具體事務(wù)不是一一分析而是以籠統(tǒng)的方法解決。而全面深化改革的時(shí)代需要我們必須強(qiáng)化精準(zhǔn)思維,值得注意的是,提倡精準(zhǔn)思維方式是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一次變革和更新。注重精準(zhǔn)思維方式,絕對(duì)不是對(duì)綜合思維或整體思維的忽視,而是要最大化地實(shí)現(xiàn)二者的互補(bǔ)。
(一)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中“精準(zhǔn)”的缺乏
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所具有的籠統(tǒng)的整體直覺(jué)性妨礙了思維的精準(zhǔn)化發(fā)展。在中國(guó)科技史研究中,有一個(gè)著名的“李約瑟難題”①:盡管中國(guó)古代對(duì)人類科技發(fā)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xiàn),但為什么科學(xué)和工業(yè)革命沒(méi)有在近代的中國(guó)發(fā)生?其實(shí)在科技領(lǐng)域中,有許多發(fā)明或發(fā)現(xiàn)都誕生在古代中國(guó),但是中國(guó)古代并沒(méi)有成體系的科學(xué)系統(tǒng),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加上沒(méi)有現(xiàn)代學(xué)校體系,政府也不重視,導(dǎo)致很多技術(shù)失傳,國(guó)人沒(méi)有將科學(xué)技術(shù)提升到理論高度。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就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重經(jīng)驗(yàn)、輕邏輯、輕分析,這種思維方式自然也就缺乏精準(zhǔn)性。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中“精準(zhǔn)”的缺失主要有兩個(gè)特點(diǎn),一是整體性,二是直覺(jué)性。
1.整體性。所謂整體性就是說(shuō)它傾向于對(duì)感性經(jīng)驗(yàn)作抽象的整體把握,而不是對(duì)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作具體的概念分析。這種思維方式趨向于尋求對(duì)立面的統(tǒng)一,中國(guó)哲學(xué)雖然也講統(tǒng)一中的斗爭(zhēng),但總的傾向是不主張斗爭(zhēng)和分歧,而習(xí)慣于融會(huì)貫通地在總體上把握事物,尋求一種自然的和諧。這使得中國(guó)古代哲人不太注重細(xì)節(jié),表現(xiàn)出中國(guó)古代思想家“整體”的思維方式。如在先秦哲學(xué)中,“天人合一”把人對(duì)外部世界的認(rèn)知和人自身的主觀情感統(tǒng)一起來(lái),這就使傳統(tǒng)思維帶有強(qiáng)烈主觀性,古人尋求的是外部世界與自我的統(tǒng)一,而不是對(duì)外部世界的探索和認(rèn)知。在這樣的認(rèn)知之下,沒(méi)有必要對(duì)部分做進(jìn)一步的分析。老子講“道”,“道”有整體之意,無(wú)所不備,包容萬(wàn)物;莊子講“天地與我并生,萬(wàn)物與我為一”[2],天地是一個(gè)整體,人與世界是一個(gè)整體;《周易》把一切自然現(xiàn)象和人事吉兇納入一個(gè)系統(tǒng)中,即由陰陽(yáng)所組成的六十四卦系統(tǒng)……這些都體現(xiàn)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重整體輕分析的特點(diǎn)。
2.直覺(jué)性。“追求整體統(tǒng)一的思維習(xí)慣使古代哲人在認(rèn)識(shí)客觀事物時(shí)滿足于通過(guò)直覺(jué)得到一個(gè)總體印象,而不習(xí)慣于作周密的詳細(xì)分析。”[3]這就是直覺(jué)性。我們平時(shí)所說(shuō)的靈感、第六感就是一種直覺(jué)性思維。道家最先提出了直覺(jué)思維的問(wèn)題,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4],“道”不是可言說(shuō)、不能用概念來(lái)認(rèn)識(shí)的,怎么去領(lǐng)悟這個(gè)不可言說(shuō)的“道”,老子講:“圣人不行而知,不見(jiàn)而名,不為而成。”[4]就是說(shuō)圣人是安心修煉的,并不會(huì)用多余的時(shí)間到處游走,只要順天道,事情自然就成功了。即,是說(shuō)外在自然是一個(gè)整體,不可分析、不可證明,只能感覺(jué)、體驗(yàn)、內(nèi)省,靠著直覺(jué)體悟來(lái)認(rèn)識(shí)“道”。中國(guó)化的禪宗也把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直覺(jué)性發(fā)展到了極點(diǎn)。禪宗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jiàn)性成佛”,“不立文字”指的是要真正的體悟禪宗的要旨是不能執(zhí)著于文字,真正的要旨并不在這些文字著述里,只要頓然發(fā)現(xiàn)自心佛性,便達(dá)到了成佛境界,而不必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的繁瑣修行階段。
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的整體性和直覺(jué)性特征使得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成為一種直觀的方法,在這種思維的指導(dǎo)下,能夠?qū)陀^世界有一個(gè)比較樸素的、基本的把握,掌握其基本規(guī)律,這對(duì)綜合性科學(xué)和諧統(tǒng)一的發(fā)展都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但是也因?yàn)檫@個(gè)總的印象不是建立在嚴(yán)格分析、求證的科學(xué)基礎(chǔ)之上,因而只能是粗略的、籠統(tǒng)的、模糊的,帶有很大的不精確性。這種思維方式對(duì)國(guó)人產(chǎn)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從目標(biāo)上,中國(guó)人希望達(dá)到和諧;從認(rèn)知過(guò)程來(lái)看,中國(guó)人看問(wèn)題從整體去把握;從行為表現(xiàn)上看,中國(guó)人處理問(wèn)題采取折中方法。”[5]而追求整體性和直覺(jué)性妨礙了邏輯推理的發(fā)展,這制約了中國(guó)近代科學(xué)的發(fā)展,世界上很多發(fā)明創(chuàng)造起源于中國(guó),但大部分發(fā)明創(chuàng)造來(lái)源于勞動(dòng)人民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缺乏系統(tǒng)的科學(xué)的實(shí)驗(yàn)論證和理論支撐,這是中國(guó)近代科學(xué)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近代以來(lái)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唯物辯證法轉(zhuǎn)向
自從中國(guó)進(jìn)入近代以后,社會(huì)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動(dòng),中國(guó)人民面臨著深重的民族危機(jī)和對(duì)民族獨(dú)立、人民解放的強(qiáng)烈渴望,同時(shí)又受到西方文化和思維方式的挑戰(zhàn)。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guó)古代傳統(tǒng)思維方式開(kāi)始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先進(jìn)的知識(shí)分子在西方的堅(jiān)船利炮下,逐漸認(rèn)識(shí)到國(guó)家的富強(qiáng)不能僅靠學(xué)習(xí)西方武器技術(shù),而是要掌握思維的方法,變革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從學(xué)習(xí)西方武器技術(shù)到學(xué)習(xí)西方制度再到學(xué)習(xí)西方文化,這個(gè)歷程是中國(guó)人逐漸覺(jué)醒的過(guò)程。特別是19 世紀(jì)90 年代甲午中日戰(zhàn)爭(zhēng)以后,以嚴(yán)復(fù)為代表的先進(jìn)知識(shí)分子從甲午戰(zhàn)爭(zhēng)的慘敗中認(rèn)識(shí)到了學(xué)術(shù)問(wèn)題的重要性,開(kāi)始思考求取真理的思理、方法論問(wèn)題。他們借鑒西方的近代思維方式,以期改變中國(guó)古代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在這樣的情況下引進(jìn)了近代科學(xué)實(shí)證方法和分析歸納的邏輯思維,同時(shí)批判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模糊籠統(tǒng)性。
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需要完善,但并不意味著一無(wú)是處,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全盤(pán)否定的觀念顯然是片面的。蔡元培曾說(shuō):“專治科學(xué),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機(jī)械的作用了。”[6]從“五四運(yùn)動(dòng)”開(kāi)始,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開(kāi)始了解接受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也開(kāi)展了對(duì)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的實(shí)踐,這才真正開(kāi)啟了向現(xiàn)代唯物辯證思維方式的轉(zhuǎn)變。毛澤東同志曾說(shuō):“中國(guó)的先進(jìn)知識(shí)分子為什么歡迎馬克思主義呢?除了政治的、經(jīng)濟(jì)的原因以外,還有思想文化上的考慮。一是看到了單靠西學(xué)的力量還不足以戰(zhàn)勝中國(guó)的封建舊學(xué),不足以改變中國(guó)人思維方式的缺點(diǎn),只能上陣打幾個(gè)回合,就敗下陣來(lái)。”[7]唯物辯證思維方式解決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和西方分析思維方式之間非黑即白的矛盾,實(shí)現(xiàn)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真正變革。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側(cè)重于矛盾雙方的和諧統(tǒng)一,西方分析思維側(cè)重于矛盾雙方的對(duì)立和分歧,而毛澤東同志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dǎo)下完善了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的矛盾論,強(qiáng)調(diào)矛盾既對(duì)立又統(tǒng)一,對(duì)立是統(tǒng)一的前提,統(tǒng)一是對(duì)立面的統(tǒng)一。毛澤東同志在此基礎(chǔ)上強(qiáng)調(diào)的調(diào)查研究的方法、對(duì)近代中國(guó)社會(huì)主要矛盾的分析、對(duì)全面抗戰(zhàn)三個(gè)階段的劃分就是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直覺(jué)性和整體性思維革命性變革的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促進(jìn)了中西思維的融合,但是一個(gè)民族在漫長(zhǎng)的歷史長(zhǎng)河中形成的思維是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的轉(zhuǎn)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今天,我們?nèi)匀皇苤袊?guó)傳統(tǒng)直覺(jué)性、整體性思維的影響,這也是我們今天要強(qiáng)調(diào)精準(zhǔn)思維的原因之一。
(三)新時(shí)代全面深化改革對(duì)“精準(zhǔn)”的召喚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時(shí)代改革進(jìn)入深水區(qū)的新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lái),中央根據(jù)新的形勢(shì)制定了一系列推進(jìn)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求要精準(zhǔn)定位,把握國(guó)內(nèi)外大勢(shì);其次要在精準(zhǔn)定位的基礎(chǔ)上精準(zhǔn)施策,確保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效。
“一個(gè)變,兩個(gè)沒(méi)有變”是對(duì)于我國(guó)歷史方位的精準(zhǔn)研判。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中明確提出,新時(shí)代我國(guó)社會(huì)主要矛盾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但中國(guó)是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這一國(guó)際地位沒(méi)有變,中國(guó)正處于并將長(zhǎng)期處于社會(huì)主義初級(jí)階段的基本國(guó)情也沒(méi)有變。只有在這樣的精準(zhǔn)定位之下,才能把握中國(guó)發(fā)展的方向。40 多年的改革開(kāi)放促進(jìn)了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的飛速發(fā)展,2010 年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升,政治、文化、社會(huì)、生態(tài)層面的建設(shè)愈加完善,但與此同時(shí)我們更應(yīng)該看到改革中出現(xiàn)的問(wèn)題,需求下滑、產(chǎn)能過(guò)剩、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不均衡、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平衡等成為我們現(xiàn)代化建設(shè)面臨的挑戰(zhàn)。這就需要“全面”和“深化”雙管齊下,“全面”是總體謀劃,是戰(zhàn)略,而“深化”是戰(zhàn)術(shù),意味著精準(zhǔn),要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以精準(zhǔn)思維聚焦問(wèn)題,精準(zhǔn)發(fā)力。在2019 年召開(kāi)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huì)第八次會(huì)議上,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前,我國(guó)改革發(fā)展形勢(shì)正處于深刻變化之中,外部不確定不穩(wěn)定因素增多,改革發(fā)展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wèn)題。我們要保持戰(zhàn)略定力,堅(jiān)持問(wèn)題導(dǎo)向,因勢(shì)利導(dǎo)、統(tǒng)籌謀劃、精準(zhǔn)施策,在防范化解重大矛盾和突出問(wèn)題上出實(shí)招硬招,推動(dòng)改革更好服務(wù)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大局。”[8]精準(zhǔn)推進(jìn)改革措施是確保全面深化改革落地開(kāi)花的保證。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2019 年黨和國(guó)家機(jī)構(gòu)改革總結(jié)會(huì)議上指出:“形勢(shì)在變、任務(wù)在變、工作要求也在變,必須準(zhǔn)確識(shí)變、科學(xué)應(yīng)變、主動(dòng)求變”[9],國(guó)內(nèi)外形勢(shì)在不斷地變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也要隨勢(shì)而變,面對(duì)變化,精準(zhǔn)識(shí)別、精準(zhǔn)駕馭是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必然要求。
二、理論維度:精準(zhǔn)思維的哲學(xué)基礎(chǔ)
精準(zhǔn)思維有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哲學(xué)基礎(chǔ)。矛盾規(guī)律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根本規(guī)律,是推動(dòng)事物發(fā)展的根本力量,要發(fā)揮精準(zhǔn)思維對(duì)實(shí)踐活動(dòng)的指導(dǎo)作用,首先就要把握事物發(fā)展的矛盾規(guī)律。在把握矛盾規(guī)律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分析事物的“質(zhì)”“量”“度”,以量變促成質(zhì)變。建立在矛盾規(guī)律和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基礎(chǔ)上的精準(zhǔn)思維的實(shí)質(zhì)就是實(shí)事求是。
(一)把握矛盾規(guī)律是理解事物發(fā)展變化的前提
矛盾規(guī)律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根本規(guī)律。矛盾是每個(gè)事物所具有的質(zhì)的規(guī)定性,要理解事物的發(fā)展變化、正確處理問(wèn)題,就要把握矛盾規(guī)律,而運(yùn)用精準(zhǔn)思維的第一步就是把握事物的矛盾規(guī)律。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聯(lián)結(jié)。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處處有矛盾、時(shí)時(shí)有矛盾,矛盾存在于一切過(guò)程中,存在于事物的每一個(gè)發(fā)展階段中。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提到:“矛盾的普遍性已經(jīng)被很多人所承認(rèn),因此,關(guān)于這個(gè)問(wèn)題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說(shuō)明白;而關(guān)于矛盾的特殊性的問(wèn)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10]事物之所以是此物而不是彼物、是這個(gè)階段而不是那個(gè)階段,是這個(gè)方面而不是那個(gè)方面,就在于決定其本身特質(zhì)的矛盾,如果只認(rèn)識(shí)到矛盾的普遍性,不研究特殊性,就不能認(rèn)識(shí)事物的本質(zhì)。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我們認(rèn)識(shí)事物從特殊開(kāi)始,然后才歸納為一般。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穩(wěn)固不變的。當(dāng)事物在某一發(fā)展階段出現(xiàn)多種矛盾時(shí)必然有一種矛盾起著主導(dǎo)作用,處于主要地位,這就是主要矛盾,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都包括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質(zhì)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可以相互轉(zhuǎn)化的,這種轉(zhuǎn)化由矛盾雙方斗爭(zhēng)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lái)決定。
矛盾規(guī)律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給我們的啟示就是要具體問(wèn)題具體分析。在運(yùn)用馬克思主義立場(chǎng)、觀點(diǎn)和方法看待和解決問(wèn)題的過(guò)程中,分析是極其重要的一環(huán)。而精準(zhǔn)思維便是一種分析的思維,僅僅掌握矛盾規(guī)律并不能實(shí)現(xiàn)“精準(zhǔn)”,只有在把握矛盾規(guī)律的基礎(chǔ)上繼續(xù)深入挖掘形成矛盾的量的變化,才能把握好矛盾雙方斗爭(zhēng)力量的強(qiáng)弱,使事物朝著有利的方向發(fā)展。
(二)“質(zhì)”“量”“度”相統(tǒng)一是精準(zhǔn)思維的哲學(xué)基礎(chǔ)
精準(zhǔn)思維不應(yīng)該僅僅限于把握事物的矛盾規(guī)律,更要進(jìn)一步區(qū)分事物的“質(zhì)”“量”“度”,才能做到精準(zhǔn)聚焦。每個(gè)事物都有根本矛盾所決定的質(zhì)的規(guī)定性。“質(zhì)”就是指一個(gè)事物之所以成為自身而區(qū)別于其他事物的規(guī)定性,質(zhì)和事物本身存在著統(tǒng)一性,沒(méi)有不依附于事物的質(zhì),也沒(méi)有不存在質(zhì)的事物。事物的屬性是多方面的,我們應(yīng)該通過(guò)人和事物的關(guān)系來(lái)判斷事物的質(zhì)。“量”是事物存在和發(fā)展的規(guī)模、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數(shù)量表示的規(guī)定性,量與質(zhì)不同的是:質(zhì)的變化會(huì)改變事物的屬性,量在一定范圍內(nèi)的增減不會(huì)影響事物的屬性,這個(gè)范圍就是“度”。在度的范圍內(nèi),質(zhì)規(guī)定了量的變化范圍,量的變化最終也會(huì)突破度,形成新的質(zhì)。
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在實(shí)踐中要掌握適度原則,“為了保持我們所需要的特定的質(zhì),應(yīng)當(dāng)有意識(shí)地把事物控制在度的范圍內(nèi);為了改變我們所不需要的特定的質(zhì),應(yīng)當(dāng)創(chuàng)造條件,有意識(shí)地促進(jìn)量的變化,并使其向度的邊緣不斷推移,使該物轉(zhuǎn)化為他物。”[11]在精準(zhǔn)扶貧工作中,我們對(duì)貧困人口的質(zhì)的分析就是“貧困”,精準(zhǔn)扶貧的目的就是要去除“貧困”這個(gè)質(zhì),所以我們需要推動(dòng)量變,使量變突破度的范圍,形成新的“質(zhì)”——脫貧。這個(gè)過(guò)程就是深入貧困地區(qū)、貧困人口內(nèi)部進(jìn)行精準(zhǔn)分析、精準(zhǔn)聚焦的過(guò)程。
(三)實(shí)事求是是精準(zhǔn)思維的精神實(shí)質(zhì)
實(shí)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毛澤東思想對(duì)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所作出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xiàn)之一。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xué)習(xí)》中提到:“實(shí)事求是:‘實(shí)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nèi)部聯(lián)系,即規(guī)律性,‘求’就是我們?nèi)パ芯俊!盵12]這四個(gè)字就是說(shuō)我們要研究事物內(nèi)部的聯(lián)系,把握規(guī)律,從而認(rèn)識(shí)事物。精準(zhǔn)思維就是要深入探索事物的內(nèi)部聯(lián)系,其精神實(shí)質(zhì)就是實(shí)事求是。
實(shí)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guó)化的重要?jiǎng)?chuàng)造,是馬克思主義的實(shí)踐觀和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今天我們所說(shuō)的痕跡主義、形象工程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其重視形式大于重視內(nèi)容,追求“差不多”“過(guò)得去”,不對(duì)事物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加以研究,這實(shí)質(zhì)上是與馬克思主義實(shí)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相違背的,在這樣的錯(cuò)誤思想影響下必然是缺乏精準(zhǔn)思維的。
2012 年時(shí)任中央黨校校長(zhǎng)的習(xí)近平同志發(fā)表了《堅(jiān)持實(shí)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講話,指出:“堅(jiān)持實(shí)事求是,最基礎(chǔ)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實(shí)事’,就是了解實(shí)際、掌握實(shí)情。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不斷對(duì)實(shí)際情況作深入系統(tǒng)而不是粗枝大葉的調(diào)查研究,使思想、行動(dòng)、決策符合客觀實(shí)際。”[13]堅(jiān)持實(shí)事求是,關(guān)鍵在于“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深入系統(tǒng)而不是粗枝大葉”就是要深入事物的每個(gè)發(fā)展階段的細(xì)枝末節(jié),就是要精準(zhǔn)。
三、實(shí)踐維度:注重實(shí)操,對(duì)癥下藥
樹(shù)立并運(yùn)用精準(zhǔn)思維,首先,要強(qiáng)化擔(dān)當(dāng)務(wù)實(shí)的意識(shí),實(shí)事求是,一切從實(shí)際出發(fā);其次,還要掌握分析-綜合的方法,對(duì)癥下藥,實(shí)現(xiàn)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擔(dān)當(dāng)務(wù)實(shí),精準(zhǔn)發(fā)力
精準(zhǔn)思維是一種務(wù)實(shí)的工作方式,關(guān)鍵在于落實(shí)。2018 年5 月2 日,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北京大學(xué)師生座談會(huì)上指出:“每一項(xiàng)事業(yè),不論大小,都是靠腳踏實(shí)地、一點(diǎn)一滴干出來(lái)的。‘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這是永恒的道理。做人做事,最怕的就是只說(shuō)不做,眼高手低。不論學(xué)習(xí)還是工作,都要面向?qū)嶋H、深入實(shí)踐,實(shí)踐出真知;都要嚴(yán)謹(jǐn)務(wù)實(shí),一分耕耘一分收獲,苦干實(shí)干。”[14]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曾在多個(gè)場(chǎng)合多次提到“實(shí)干”,精準(zhǔn)思維對(duì)實(shí)施主體的本質(zhì)要求就是擔(dān)當(dāng)實(shí)干,其對(duì)立面就是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和功利主義。要樹(shù)立精準(zhǔn)思維、運(yùn)用精準(zhǔn)思維首先就要在思想上認(rèn)識(shí)到實(shí)事求是、求真務(wù)實(shí)的重要性,去除形式主義等作風(fēng)問(wèn)題,真正深入事物內(nèi)部分析各方面的聯(lián)系和屬性,而不是只關(guān)注事物的表面現(xiàn)象,正確處理內(nèi)容和形式的關(guān)系。內(nèi)容和形式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的一對(duì)范疇,內(nèi)容決定形式,形式服從內(nèi)容,我們重視內(nèi)容并不是忽視形式,而是要在協(xié)調(diào)二者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以內(nèi)容為主,真正解決改革發(fā)展中遇到的實(shí)際問(wèn)題。這要求思路精準(zhǔn)、措施精準(zhǔn)、實(shí)施精準(zhǔn)、責(zé)任精準(zhǔn)、監(jiān)督精準(zhǔn),讓精準(zhǔn)覆蓋處理事務(wù)的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在每一個(gè)具體點(diǎn)上發(fā)力,避免大而化之的工作方式。
(二)精準(zhǔn)定位,對(duì)癥下藥
精準(zhǔn)定位事物發(fā)展中的問(wèn)題就要運(yùn)用分析-綜合的方法分析事物。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指導(dǎo)下的精準(zhǔn)分析不是片面的分析主義,而是分析-綜合相融合的認(rèn)識(shí)和實(shí)踐過(guò)程。我們了解一個(gè)事物,是從感性整體到理性分析再到理性整體的過(guò)程,是從感性一般到特殊再到理性一般的過(guò)程。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反對(duì)本本主義》一文中所說(shuō):“你對(duì)那個(gè)問(wèn)題的現(xiàn)實(shí)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méi)有調(diào)查,不知底里,對(duì)于那個(gè)問(wèn)題的發(fā)言便是瞎說(shuō)一頓。”[10]這里的調(diào)查就是對(duì)事物進(jìn)行精準(zhǔn)分析的一種方式。精準(zhǔn)扶貧是運(yùn)用精準(zhǔn)思維,進(jìn)行精準(zhǔn)定位的一項(xiàng)典型實(shí)踐,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有著豐富的基層工作經(jīng)驗(yàn),也一直走在深入調(diào)研的路上,在精準(zhǔn)扶貧工作中,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對(duì)于扶貧的對(duì)象、扶貧的主體、扶貧的具體方式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分析,并綜合各因素確定了精準(zhǔn)扶貧方針。關(guān)于“扶持誰(shuí)”的問(wèn)題,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指出,“要確保把真正的貧困人口弄清楚,把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致貧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戶施策、因人施策。”[15]關(guān)于“誰(shuí)來(lái)扶”的問(wèn)題,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指出:“要加快形成中央統(tǒng)籌、省(自治區(qū)、直轄市)負(fù)總責(zé)、市(地)縣抓落實(shí)的扶貧開(kāi)發(fā)工作機(jī)制,做到分工明確、責(zé)任清晰、任務(wù)到人、考核到位。”[15]在“怎么扶”的問(wèn)題上,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指出“要在精準(zhǔn)扶貧、精準(zhǔn)脫貧上下更大功夫,做到扶持對(duì)象精準(zhǔn)、項(xiàng)目安排精準(zhǔn)、資金使用精準(zhǔn)、措施到戶精準(zhǔn)、因村派人(第一書(shū)記)精準(zhǔn)、脫貧成效精準(zhǔn)。”[16]貧困人口致貧的原因有多種,“一刀切”式的扶貧并不能真正解決貧困問(wèn)題,只有深入基層,把致貧原因具體到地區(qū)乃至每一個(gè)貧困人口,才是針對(duì)性地解決貧困問(wèn)題的有效路徑。2020 年11 月23 日,全國(guó)832 個(gè)貧困縣全部摘帽,精準(zhǔn)扶貧取得了標(biāo)志性勝利。實(shí)踐證明干事創(chuàng)業(yè)需要運(yùn)用分析-綜合的研究方法,透過(guò)事物現(xiàn)象看本質(zhì),進(jìn)而制定計(jì)劃解決矛盾。
(三)精細(xì)化治理,推進(jìn)國(guó)家治理現(xiàn)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通過(guò)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wèn)題的決定》提出了“推進(jìn)國(guó)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huì)審議通過(guò)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制定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第十四個(gè)五年規(guī)劃和二〇三五年遠(yuǎn)景目標(biāo)的建議》,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huì)以后,我們進(jìn)入了全面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的新征程。鑒于粗放式治理的問(wèn)題和現(xiàn)代化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精細(xì)化治理不可避免地成為推進(jìn)國(guó)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重要手段。國(guó)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過(guò)程也是不斷滿足人民對(duì)美好生活需求的過(guò)程,這就要求精準(zhǔn)獲取個(gè)體信息,精準(zhǔn)識(shí)別人民需求,并精準(zhǔn)對(duì)接解決人民遇到的困難和問(wèn)題。
精細(xì)化治理要以滿足人民的多元需求為目標(biāo)導(dǎo)向,人民需求差異大,治理主體要精準(zhǔn)識(shí)別不同的需求,并根據(jù)人民需求建構(gòu)個(gè)性化的治理模式,以個(gè)性化、精準(zhǔn)化代替一般化、模糊化。精細(xì)化治理要以構(gòu)建多元治理主體為抓手,政府要把社會(huì)、公眾吸納進(jìn)治理主體之中,形成多元主體治理模式,政府、社會(huì)、公眾各歸其位,精準(zhǔn)定位三方職能,使人民的問(wèn)題和心聲得到及時(shí)的傳達(dá)、回應(yīng)和反饋。精細(xì)化治理要以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為手段,以大數(shù)據(jù)等互聯(lián)網(wǎng)工具對(duì)治理的主體、對(duì)象、內(nèi)容等進(jìn)一步細(xì)化。以精細(xì)化治理推進(jìn)國(guó)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滿足人民對(duì)美好生活的需求。
結(jié)語(yǔ)
從歷史維度來(lái)看,精準(zhǔn)思維是時(shí)代發(fā)展對(duì)超越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必然要求;從理論維度來(lái)看,精準(zhǔn)思維有著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辯證法的科學(xué)性;從實(shí)踐維度來(lái)看,精準(zhǔn)思維是從擔(dān)當(dāng)務(wù)實(shí)到國(guó)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現(xiàn)實(shí)需要。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我國(guó)發(fā)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進(jìn)入新時(shí)代,我國(guó)經(jīng)濟(jì)已由高速增長(zhǎng)階段轉(zhuǎn)向高質(zhì)量發(fā)展階段,粗放的發(fā)展方式難以為繼,精細(xì)化發(fā)展是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jí)必然面對(duì)的課題。當(dāng)前,我國(guó)面臨的國(guó)際國(guó)內(nèi)形勢(shì)愈加復(fù)雜,就國(guó)際來(lái)說(shuō),當(dāng)今世界正在經(jīng)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格局力量對(duì)比產(chǎn)生新的變化;就國(guó)內(nèi)來(lái)說(shuō),進(jìn)入新時(shí)代,我們比任何時(shí)期都要更加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以人民為中心的精準(zhǔn)的疫情防控手段顯示出了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在復(fù)雜的國(guó)內(nèi)外形勢(shì)下,黨面臨執(zhí)政新考驗(yàn),而我國(guó)發(fā)展的關(guān)鍵在于我們要辦好自己的事情,精準(zhǔn)思維是抓好機(jī)遇、應(yīng)對(duì)挑戰(zhàn)、實(shí)現(xiàn)新時(shí)代良性發(fā)展的必然需要。在接下來(lái)的“十四五”時(shí)期,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社會(huì)、生態(tài)建設(shè)和黨自身的建設(shè)都需要在前期成就的基礎(chǔ)上精準(zhǔn)識(shí)別問(wèn)題、聚焦各領(lǐng)域主要矛盾、有針對(duì)性地推動(dòng)發(fā)展質(zhì)的提高,我們更加需要摒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作風(fēng),能作為、敢擔(dān)當(dāng),實(shí)事求是,善于運(yùn)用精準(zhǔn)思維,掌握分析-綜合的辯證方法,為推動(dòng)新時(shí)代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事業(yè)而奮斗。
注釋:
①“李約瑟難題”:是由英國(guó)學(xué)者李約瑟提出,他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史》中正式提出此問(wèn)題,其主題是:“盡管中國(guó)古代對(duì)人類科技發(fā)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xiàn),但為什么科學(xué)和工業(yè)革命沒(méi)有在近代的中國(guó)發(fā)生?”1976年,美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
- 克拉瑪依學(xué)刊的其它文章
- 2019年毛澤東政治思想研究述評(píng)*
- “關(guān)于全面禁食野生動(dòng)物決定”的法律思考
——兼論《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的修改 - 商標(biāo)侵權(quán)損害賠償額之判定
——以《商標(biāo)法》第63 條為基點(diǎn) - 我國(guó)家事糾紛調(diào)解主體制度探究
- 網(wǎng)絡(luò)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下新時(shí)代高校班級(jí)管理創(chuàng)新研究*
——以“三個(gè)一二三”齊步走向成功模式為例 - 探頤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與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范式差異、耦合共性及融通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