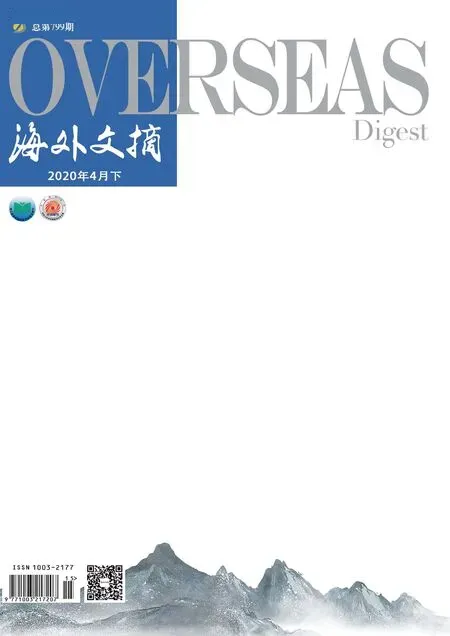東北方言主觀評價性構式“X 了X 了的”研究
鳳宇
(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四川綿陽 621010)
作者簡介:鳳宇(1995—),男,遼寧沈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方言學、少數民族文字學。
東北方言主觀評價性構式“X 了X 了的”表示說話的一方對其他人的行為、動作等進行主觀的判斷后所給出的評價。這種構式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暫時還沒發現,但是在東北方言中是大量存在的。王光全(1991)認為“X 了X 了的”構式是一種動詞的貶義描摹體,這種描摹體有嚴格統一的類意義即語法意義,可以看成是東北方言動詞的一個范疇[1]。筆者認為這類范疇不能僅僅理解為一種簡單的貶義臨摹體,從構式的角度來看,這類語法形式是一種典型的構式。
1 “X 了X 了的”中的構件成分及其特點
“X 了X 了的”構式由三部分構成:變項X 和常項了的。整個構式是“X 了”重復后加“的”,我們尤其要關注的其中一點就是構式中僅有的變項“X”的選擇及其特點,即哪些詞能夠進入構式之中,也就是進入到該位置的詞的語義特征。
要研究能夠進入到該構式的詞的特點及語義特征與整個構式的構式義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從“X 了X 了的”構式的構式義來看,“X 了X 了的”是一個具有高度主觀性并具有負向評價的構式。能夠進入“X了X 了的”構式中X 詞性一般為動詞性或形容詞性的,也有的兩種詞性兼有。只有單音節語素才能進入到此構式之中。語義上表現出個體對人或事物的行為動作等所做出的個人主觀評價,表示此時個人的心理活動或感覺。具有極強的個人主觀性色彩。有以下詞可進入該構式:
“騷了騷了的、拽了拽了的、鉗了鉗了的、瘸了瘸了的、拐了拐了的、翻了翻了的、晃了晃了的、穿了穿了的、扇了扇了的、嘚了嘚了的、唔了唔了的”等。
以上幾種詞無論是形容詞、動詞還是擬聲詞,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描述性,從上述例子中我們可以進一步明確東北方言“X 了X 了的”構式義為評價主體對客體的主觀評價性描述。上述的動詞,例如:“他走路穿了穿了的,太難看了。”是指一個人走路的時候腳后跟快速抬起來。
例:
(1)你一天別老唔了唔了的。
(2)你走路老穿了穿了的啥呀?
(3)他跑起來拐了拐了的。
(4)那個人說話的時候眼皮老翻了翻了的。
(5)她一天總騷了騷了的,不要臉。
例(1)中的“唔”是東北方言中表示人說話狀態的擬聲詞。例(2)(3)(4)中的“穿”“拐”“ 翻”都是表示人動作狀態的的動詞。這些表示人說話狀態和行為狀態的動詞屬于狀態動詞的下位小類,具有狀態詞的特性。狀態詞在“擬聲詞—形容詞—動詞”這一連串詞類中更靠近形容詞一端,在量上具有一定的游離性,受形容詞的影響而兼具了形容詞的一些共性,也能受高量級程度副詞“老、總”修飾, 與非定量形容一樣,具有量級特征。刁晏斌曾指出“不少動、形兼類詞最能體現性狀義”,在東北方言中具有“狀態”特征的詞是普遍存在的,在實際的語用過程中,整個構式的意義與能進入到構式的“X”的語素義有著密切的聯系,東北方言有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兼類詞普遍存在于各種詞性當中。兼類詞是詞的兼類現象,某個詞經常具備兩類或幾類詞的主要語法功能。即在甲場合(位次)里有甲類詞的功能,在乙場合里有乙類詞的功能,不是說在同一場合(位次)里有甲乙兩類詞的功能。兼類詞一定要讀音相同,詞義有聯系,而所以那些失去了聯系或者意義無關的詞不是兼類詞。進入到該構式的詞或語素均具有形容詞的特點。
綜合以上可看出,表各種狀態的詞也具有[+性狀]、[+評價]、[+主觀]的語義特征,因此能進入“X”中,這類狀態詞在音節結構上多為單音節,詞語感情色彩則褒義、貶義、中性義的詞都能進入“X”中。但是在實際的交流中無論是褒義還是中性的詞語,只要進入到構式“X 了X 了的”中后,整個構式就表現出貶義的意味。例如:(1)中你一天別老唔了唔了的,意思就是希望說話者說話更為清晰一些。(2)你走路老穿了穿了的啥呀?就是說話者不希望看到腳后跟先抬起來的情況,表現出對該行為動作的不喜歡或者說厭惡,側面體現出深層的[+貶義]的語義特征。
根據以上的例子,我們可總結出能夠進入“X 了X 了的”構式中的“X”在詞項類型上多數為表示性狀的形容詞,少數為表動作行為狀態的兼類詞;在語義特征上,具備[+主觀]、[+性狀]、[+評價]等基本語義特征,當“X”進入到構式之中后,無論該詞是中性還是褒義、貶義,整個構式的構式義在口語表達中均為[+貶義]。
2 “X 了X 了的”構式的壓制
構式壓制:“壓制”(coercion) 現象是源于計算語言學的一個術語,泛指語言形式和所表達的語義功能之間的一種不匹配現象,有的學者也將其稱為“糅合”。壓制就是為了使詞項與構式相配合構成新的構式義,將原有的與構式不匹配的部分刪去,增加與構式義相一致且匹配的意義的一種“修補機制”[2]。當某個詞語被用于某個構式中,兩者的語義或用法發生沖突時,處于上位的構式會迫使進入到該構式的詞發生改變,使詞項的語義和用法與該構式保持一致。
例如:他走路總穿了穿了的。
“穿”在“X 了X 了的”構式的壓制下,其動作義受到了抑制,呈現出一種經常性習慣性的動作狀態,狀態義通過“X 了X 了的”構式得到了凸顯。
例句中的“穿”原為及物動詞,例如“穿鞋”,不具有動作狀態義。進入“X 了X 了的”后,因為語義和用法上的不兼容,“穿”受到了構式的壓制,產生了新義,義為“穿鞋的走路時后腳跟先抬起來的動作行為狀態”。及物動詞在構式的壓制下呈現出較強的行為狀態義,具有經常性習慣性的意味。
當說話者選取該構式用于評價的時候,構式會自動排斥進入到該構式的詞的其他詞義或詞性,只保留一種描述性的詞義,也就是說當詞進入到“X 了X 了的”這個構式中,與整個構式表現出的行為狀態義不匹配,那么處于弱勢的詞項就會被迫改變自身的詞法類別,增加新的語義特征。原本不具有述謂性和狀態性的“穿”“翻”“唔”等詞,進入到“X 了X 了的”構式中就具有了以上兩種特性。以上原本就屬于形容詞的“騷、拽、鉗、瘸”等詞的語法特征來看,“X 了X 了的”構式功能相當于一個含義復雜豐富的狀態形容詞:不論內部結構,都要帶詞尾“的”。“X 了X 了的”構式突出客體的動作行為特征,強調了動作行為狀態性和非事件性。
3 “X 了X 了的”構式表達負向評價及隱喻認知
自然語言中的斷言,常常是說話人對事件中的人物帶有一定的認識、態度乃至評價。這個斷言有時是積極的、肯定的,可稱之為正向評價;有時則是消極的、否定性的,可稱之為負向評價。“X 了X 了的”表示說話者對前者動作行為的負向評價。那么該構式的構式義是如何產生的?接下來將對該構式的構式義的形成及負向評價的理據進行討論。
“X 了X 了的”的評價義源于描寫句式。“X 了X了的”表示主觀評價的語義是由描寫句,也就是形容詞性謂語句中分析出來的。與“X 了X 了的”構式最基本的句式是單形謂語句(主+形)。形容詞性詞語充當謂語的句子叫形容詞性謂語句,主要用來描寫人的性質、特征等。該構式承載了其他部分所要傳遞的信息。對于交流中的信息人腦不能及時的給予反映,不能從句子構成的構成成分和內部關系等簡單推斷出來,需要人腦對已知信息進行二次處理[3]。這樣就不符合交流交際中的“經濟原則”,說話者所要表達的意思在理解上就出現了偏差,這就需要人們在長時間的交流當中需要一個表達相應意義的固定句式,使之成為一個固定的表達主觀評價的標記性構式,這類固定句式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人們在長時間的生產生活中選擇并逐漸沉淀保存下來的。
一種構式在形成后必定會有相應的構式義產生,從認知語言學角度看,其構式義是在隱喻認知推動下獲得的。隱喻不僅是語言現象,更是一種思維方式。隱喻作為人的一種思維方式,是通過人類的認知和推理將一個概念域投射到另一個概念域的結果。在“X了X 了的”構式中,該構式的主觀評價性就是就是認知投射的結果。程度域處于更抽象、模糊的概念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