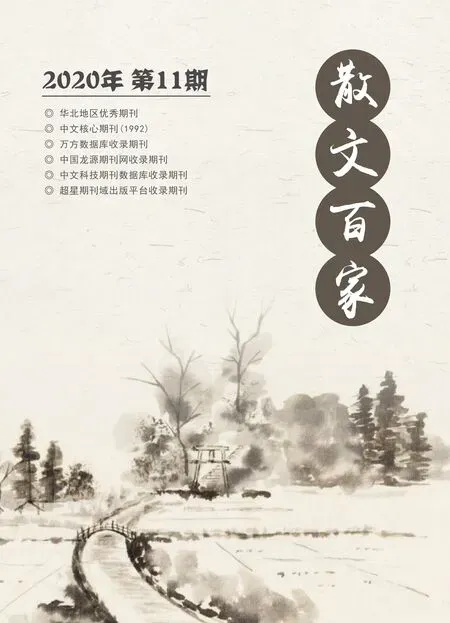文化“變異”中的吶喊
——《吃碗茶》的互文性解讀
彭思宇
四川工商學院
雷霆超于1961年出版的小說《吃碗茶》是美國亞裔文學作家與評論家公認的一部劃時代的作品,如今已成為美國亞裔文學。小說以主人公賓來和李美愛的婚姻生活為主線,圍繞著賓來因拈花惹草導致性功能喪失、美愛因受無業游民阿桑花言巧語蠱惑與其發生不正當關系、賓來之父王華基怒割阿桑耳朵等事件展開,真實反映了由美國政府的排華政策造成的畸形百年的華人“單身漢”社會。文中以互文手法展現了一系列中國文化在唐人街的反映、“變異”,而這些文化“變異”背后所蘊藏的社會意義是值得我們深入挖掘的。
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對于《吃碗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國內學者大都從人物、社會背景、文化三個方面對小說進行研究。在人物分析方面,學者們分別從文化身份塑造、女性解讀分析、精神分析、父親形象幾個方面進行了一定的研究。吳冰早期評析了《吃碗茶》中的紐約華人社會,并對男女主人公進行了一定的分析,認為賓來是中國傳統思想與美國新思想的結合體;而美愛則是“作者的敗筆”,并不能作為結束畸形華人“單身漢”社會的代表。[1]丁夏林則通過斯圖加特· 霍爾的文化身份理論,對主人公的文化身份重塑進行了探究,認為主人公賓來和李美愛從小說開頭到結尾完成了從“金山客”到美國人的身份轉變。[2]另外,有不少學者從小說的社會背景出發來探析小說中的“單身漢”、“父權制”社會。蒲若茜聚焦于小說中的唐人街“父權制”社會,分析了中國封建的“父權家長制”在美國主流社會擠壓下產生了扭曲和蛻變以及 其面臨的反抗等問題。[3]對于小說中體現的文化元素學者們也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薛玉鳳結合《吃碗茶》、《女勇士》和《中國人》三部作品,從“兩性關系”角度對華裔美國文學中的“分裂家庭”進行了解讀,最后提出華裔的相關研究不應忽視了華人移民的 “寡婦”妻子們,應給予他們更多關注。[4]
國外有關《吃碗茶》的研究相對較少,其中Ling Jinqi從歷史特征的角度來解讀《吃碗茶》中的性別協商問題,通過探究小說是如何反映唐人街“單身漢”社會以及其中的的種族、性別問題,最后道出小說實際以含蓄的方式為當時唐人街的勞動婦女發聲,以求更多的學者給予他們關注。[5]Geoffrey Kain從小說主人公賓來的性無能折射出整個“單身漢”社會的無能與墮落,探究這群被放逐的“單身漢”在美國所遭遇的文化孤立。[6]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吃碗茶》的研究已相對成熟,但是對于小說中出現的文化“變異”現象,雖已有翟卉婷對小說中的儒家文化的“傳承和變異”進行了一定的分析,[7]但是對于小說中“夫子”形象以及“尋夫記”這兩個具有代表性的“變異”現象尚未有任何涉及。本文試以小說中“夫子”形象、“尋夫記”等互文現象為例,分析小說中的文化“變異”現象,旨在探究這種文化“變異”背后的社會文化意義,為該小說的社會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
互文性是由法國符號學家、女性主義批評家克里斯蒂娃在其《符號學》一書中提出的,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語拼湊而成 ,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造。”[8]所以,這個“文本”可以是一種文化現象,社會觀念,人物形象等。小說中“夫子”形象、《千里尋夫》就是人物形象、文化故事“文本”,它們帶著其原有的文化背景被投入到一個新的文化背景(小說背景)中,就產生出了新的意義,即發生了“變異”。
“夫子”形象的顛覆
在中國的傳統思想教育中,教師的地位和積極作用是被肯定的,唐代的韓愈就曾對教師作用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由于教師地位的重要性,對師德就十分強調。漢代楊雄在《法言·學行》中指出教師要為人師表,做人楷模:“師者,人之模范也。”這些都說明了教師,即“夫子”這個形象的正面性。但是《吃碗茶》中的錢源(Yin Yuen),這個曾經的教師卻從言語、行為、思想上完全顛覆了“夫子”的“模范”形象。小說中對他的描寫多次涉及到中國的習語:“肥水不流外人田”;“男女授受不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9]這些對中國習語的借用事實上是對于錢源的一種諷刺。曾今的中國“夫子”到了美國唐人街后,生活混亂,工作之余的娛樂就是嫖妓,甚至還將賓來(Ben Loy)第一次帶入縱欲的世界。而作為賓來的好友,他卻對其妻子美愛想入非非,多次借機接近,占美愛便宜。其行徑皆與中國傳統的“夫子”的形象相差甚遠。而錢源常以“孔夫子”、“諸葛亮”這些中國歷史上德高望重的人物來與自己比較,更是讓人不免感覺滑稽可笑,產生了一種反諷的效果。
作者雷霆超在這里所塑造的顛覆傳統形象的“夫子”,通過對“俗語”的借用,向讀者展示了一個變異,思想墮落的“假夫子”形象。以“孔夫子”為代表的教師形象,到了紐約唐人街就完全被顛覆,這不禁引人思索探究,究其原因:
不難發現,錢源并不是這本小說里唯一的生活墮落的嫖客,阿桑、王華基等生活在唐人街社會里的“單身漢”,過的都是一種畸形的性生活。薛玉鳳曾說“排華法阻止華人與妻子到美國與丈夫團圓,禁止白人女子與華人結婚,使他們被迫過著單身生活,是對華人男子另一種意義上的閹割。”[9]不得不說錢源對“夫子”形象的顛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他處在這種被流放的“單身漢”社會造成的。因此,此處“夫子”形象的“變異”實是對造成這種“單身漢”社會的排華政策的揭露。
“尋夫記”與“盼歸夫”
小說中并沒有詳細解說《千里尋夫》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它只是在大廚(Fat Man/Kitchen Master)與王華基的對話中被簡單提到的一場戲名。但是筆者認為這場戲被提到并非作者隨意的選擇,它的出現帶有一定目的性。“千里尋夫”,一提到這個故事,中國人都知道講的是孟姜女千里尋覓丈夫范喜良的凄美愛情故事,同時也是對于秦始皇強征平民修長城的控訴。《千里尋夫》的戲名帶著其自身的中國文化背景出現在這部小說中,即便是以如此輕描淡寫的方式出現,由于《吃碗茶》自身所設置的小說背景與文化語境,它的意義便不再是其原來的含義。此處,由它產生的意義與聯想在雷霆超的小說中便被賦予了另一層新的含義,這也正是《千里尋夫》在此所體現的互文性的作用。
首先,“孟姜女”在故事中艱辛千里尋夫,放在《吃碗茶》的小說背景下,讓人不禁想到了獨守家園的“金山婦”們。小說中對他們的凄涼生活也有一定的描寫,“在新會還有千千萬萬個像劉氏一樣的妻子,他們的丈夫出海遠去了那個美麗的國家,一去不復返。……明年,或許再下一年。盡職盡責的妻子就這樣等待著,期望著。”[9]這些金山客的妻子們都在盼望著丈夫的歸來,他們永遠都在期盼,而這一天卻永遠都是一個未知數。同時“孟姜女尋夫”的故事中,丈夫范喜良被抓修建長城的情節,也召喚讀者回憶起早期赴美的勞工們修建鐵路的艱苦生活,以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歷史。而這么一批為美國社會做出貢獻的華人勞工卻得不到美國的承認。1882《排華法案》的實施,更是將他們與主流社會隔離,被放逐于唐人街,形成了美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華人“單身漢”社會。“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唐人街‘種族孤島’上的華人‘單身漢’和他們遠在國內的妻子們過著一種人類有時以來最為特殊的婚姻生活。在長達百年的這種不正常生活中,男女雙方都是當時美國排華政策的犧牲品,而受害最大的當屬他們‘守寡’在家的妻子們。”[4]
因此,通過對此處互文現象的分析,可知“孟姜女千里尋夫”這個中國流傳已久的民間故事在此起到了一種刺激功能,引導讀者去深思小說背景下的相關情節,進而帶領讀者去揭露《排華法案》對于華人“單身漢”以及他們的妻子的迫害。其中“千里尋夫”的故事結合小說背景在這里也發生了“變異”,而這種“變異”背后所要表現的社會文化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
結語
中國傳統文化下“夫子”形象、“尋夫記”在小說《吃碗茶》的背景下意義紛紛發生了“變異”:受人尊崇的“夫子”形象被徹底顛覆;《千里尋夫》變成了“金山婦”遙盼夫歸。本文通過對以上互文性的分析,解讀在新的文本語境下“夫子”形象以及“尋夫記”這些“變異”現象背后的成因,進而挖掘作者通過 互文性構建所表現的深刻含義:控訴美國排華政策造成的畸形“單身漢”社會,并揭露了在其影響下華人思想、文化所受到的荼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