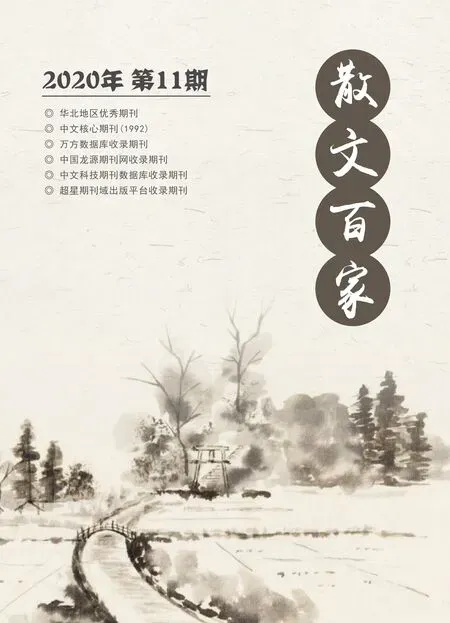《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怡芬姑母的病態心理解析
王 瓊
襄陽汽車職業技術學院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是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西西的成名作,也是其早期短篇小說之一。小說主要講述了女主人公在咖啡廳等待男友到男友捧著鮮花到來這段時間里的內心活動。全文采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手法,整篇文章將“我”的心理獨白完全展現在讀者眼前,真實地描繪了80年代香港底層生活的艱辛。文章中一共出現了三類人物:第一類是“我”和怡芬姑母,特殊的職業性質使我們成為最接近死亡的人;第二類是遠離死亡的人,這些人因為對死亡的原始恐懼疏遠我和姑母,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即將接受考驗的夏;第三類是已經死去的人,即我的工作對象。本文將針對第一類人物中怡芬姑母的病態心理進行解析。
一、從“我”的內心獨白解析怡芬姑母的病態心理
首先說一說“我”,“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女子呢?為什么她不適宜和任何人戀愛?她和夏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從整個文本的語言來分析作者似乎一直在絮絮叨叨,文章表達以長段、長句為主,全文語調緩慢低沉。從作者的敘述我們可以得知“我”的職業是一名儀容化妝師,我和怡芬姑母從事的是同一種職業,是姑母把我帶入這個行業的。顯然這是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群。或許這種職業收入不菲,但由于其特殊的職業性質和人類的原始心理恐懼,從事這類職業的人并不容易為普通人群所接受。但是“我”對自己的事業執著又充滿傲骨,同時也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與尊重。面對自己的婚姻與戀愛“我”始終持悲觀態度。
既然“我”渴望和普通人一樣擁有再簡單不過的生活,那么為什么不選擇改行呢?更何況“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兒,有著和其他女孩兒一樣的憧憬:向往美好生活、向往愛情、向往有人呵護。怡芬姑母究竟出于什么樣的心態才會把“我”帶入這個行業?其實,怡芬姑母是把“我”當成了自己的繼承和延續。如果把怡芬姑母看做不為世俗偏見而畏懼轉身的人,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未免把姑母的形象過分拔高了。姑母也是人,是一個及其普通的人,她也有七情六欲,也會向往陽光下的美好生活。愛人在知道她所從事的職業后失魂落魄的逃離了,怡芬經歷了失戀的打擊從此變得沉默寡言。愛人在死亡面前的膽怯表現出了普通人的庸俗與不堪,是不值得譴責的,可怡芬姑母卻對此耿耿于懷。她為什么不選擇改行并且還要將可以預知的痛苦帶給自己唯一的親侄女兒呢?姑母自以為勇敢、自以為執著,卻固執地將自己的孤獨帶給他人,錯誤的把“我”當做母親的再現,忽略了“我”對恐懼的感受,這本身就是一種病態心理的具體表現。怡芬姑母是可憐、可恨又可悲的。
二、從人物性格分析解析怡芬姑母的病態心理
怡芬姑母因為自身的工作性質被男友拋棄,她因此變得沉默寡言并且對身邊所有的人都有了戒備心理。她從此自我封閉、不再輕易相信任何人,把躺在自己面前的工作對象當作朋友,當作自己的傾訴對象。試想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會遭遇各種挫折,難道因為一次戀愛失敗就永遠不再接觸異性了嗎?甚至把這種拒絕由異性之間的愛延伸到朋友之間的友情,把人世間的一切美好都拒之于千里之外,這是缺乏健康人格的一種表現。
仔細分析文本我們不難發現,文章從始至終所描述的害怕接觸這個“特殊職業”的人都是“我”和怡芬姑母身邊的親人和朋友,遠離我們的也是這些親人和朋友,就連“我”也是“被勇敢”的。怡芬姑母帶我入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為喜愛化妝、喜歡這個職業,更不是因為自身具有奉獻精神,而是狹隘的利用這個職業的特殊性來測試朋友的真誠度和勇敢度,這種測試建立在對他人缺乏信任的基礎之上。怡芬姑母把心目中的愛人和朋友置于一種理想化境界,怡芬姑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愛人和朋友,而是一種具有決絕和貞烈品質的載體,這樣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是很難找到的。因此在怡芬姑母性格的主要成份是沉溺與固執,表現在生活中就是一種病態行為。
三、從擇業觀念解析怡芬姑母的病態心理
“我”是怡芬姑母帶大的,因此怡芬姑母“理所當然”地對“我”未來的命運做出了安排。關于怡芬姑母做出這種安排的出發點文中是這樣敘述的:“從今以后,你將不愁衣食了”,“你不必像別的女子那般,要靠別的人來養活你了”;而“我”的想法則是:“怡芬姑母這樣說,我其實是不明白她的意思的。我不知道為什么跟著她不必靠別人來養活。難道世界上就沒有別的職業可以令我也不愁衣食、不靠別人來養活么”?這說明我從內心深處并不太樂意接受這個職業。但是因為我和怡芬姑母相依為命,二人的性格呈現重疊狀態。我逐漸被姑母同化,具體表現就是脫離現實生活的理想化擇人標準。
從以上兩段獨白我們不難看出,怡芬姑母的擇業觀美其名曰是一種進步觀念——即女性能夠自食其力固然是好事,但未必只能受限于這狹小的空間。即使文化程度低,也未必只能從事這一種職業,還可以有更多其他的選擇。只要是靠勞動吃飯,工作是不分貴賤的。作為一個女人,最自然的想法應該是從事一些常人能夠接受的職業。試想怡芬姑母和主人公若是母女關系,她還會讓“我”去從事這樣不被世人理解的職業嗎?明知會有職業尷尬存在,明明能夠預測未來命運,卻偏偏還要把侄女推向這個不易被常人所接受的行列并剝奪了她享受美好生活的權利,這種做法讓常人難以理解。這難道不是病態心理的第三種表現嗎?
四、從設置開放式結局的角度解析怡芬姑母的病態心理
中國人歷來喜歡大團圓的結局,因此無論電影、電視劇還是文學文本多數結局都是皆大歡喜。但西西的這篇作品并沒有明確寫出結局,而是留給讀者多元化的想象空間,這說明女主人公對夏還有一絲期待,且“夏”這個名字也是有獨特寓意的,他是女主人公灰色人生中一抹獨特的陽光。女主人公根據怡芬姑母的愛情悲劇對自己的戀愛做出悲劇判定,但是她的內心還有另一種聲音在呼喚,那就是假設了一個類似自己父母愛情故事的喜劇結局。這說明“我”并不能接受怡芬姑母強加給我的勇敢、脫俗,“我”對愛有自己的渴望、期待和表達,我”對結局的美好設想是合情合理的。
這樣的結局設置允許讀者作出多元化解讀,從另一個側面則影射出怡芬姑母的病態心理,她以偏概全,用自己的遭遇覆蓋他人的命運。夏是“我”心目中的陽光地帶,作者表達的主體傾向是期待夏能夠接受“我”和“我”的職業。姑母病態心理驅使下強加給“我”的孤獨無法阻擋“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文中的“我”代表的并不只是我自己,而是這個社會上所有處于邊緣位置的女性群體的代表;“我”的呼聲是整個社會中女性弱勢群體的呼聲。
命運給予每個人的機會都是平等的,如果你對命運妥協,那么命運將會如死水一樣平靜。怡芬姑母的選擇看似是在和命運抗爭,但最終還是可以將其歸為妥協,并且將這種妥協殃及他人。因此這是她病態心理表現的第四個層面。
五、結語
文本中的怡芬姑母是一種介質,她把過去的我和現在的我連接在一起。對過去的“我”的回憶實質描述的是現在的“我”的處境。我的本質是一個樸素、本真的女子,但是怡芬姑母試圖用她的病態性格對我進行同化。過去的我是怡芬姑母的化身,擇業觀、性格等各方面都深受姑母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能抑制我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畢竟怡芬姑母的心理是病態的。對這種病態心理的掌握,有助于讀者正確把握文本的豐富性、復雜性,文本本身也因為這種“表里不一”的矛盾而顯得更有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