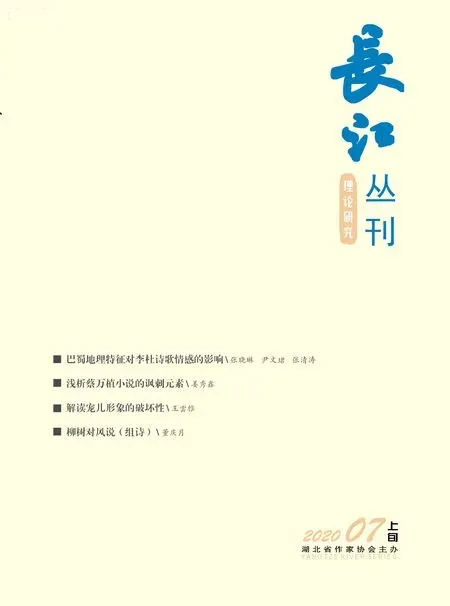具身學習意涵中的教學變革
■許雙成/遵義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
身體現象學與具身認知理論揭示了身體的認知主體地位,也就闡明了學習的具身性。“具身學習是個體最大限度地利用內部心理資源和外部環境條件,以達到心智、身體、環境之間動態平衡的過程。”[1]具身學習概念的提出,內蘊了教學的變革:教學是“情景嵌入”的——在教學主體與教學情境的互動中建構知識與個體的意義關聯;教學是“價值負載”的——教學并不追求外在的、工具化的知識,而是強調個體與他者的精神共契。由此,教學回歸豐富的意義世界,啟迪個體智慧,促進個體成長。
一、具身學習內蘊的教學理論更新
教學理念是人們對教學的基本看法和持有的觀念。傳統教學理念中“工具理性”的張揚和“離身知識”的充斥,導致了教學意義的迷失以及教學中身體被遮蔽后的知識與智慧的疏離。傳統教學理念的知識觀以“知識可教”為隱喻,追求知識的確定性,回避知識的不確定性,將靜態的、客觀的、顯性的知識奉為圭臬,對動態的、隱形的、緘默的知識棄若敝履。傳統教學理念的教學觀以“心智活動”為隱喻,教學是一種既定心智的抽象表征活動,是觀念傳遞和心智培育。其學習觀以“計算機”為隱喻,學習類似于計算機的輸入、加工、輸出過程,內部的心理活動是不可預知的。學生觀以“身體載體”隱喻,否認學生身體參與了認知活動,強調學習僅僅是大腦中的思維活動,與身體無關。教學禁錮身體,規訓身體。教師觀以“知識權威”隱喻,教師是知識的化身,其在教學中的權威性不容置疑。傳統教學理念中,身體和經驗是被遺忘的,身體是缺場的,經驗是缺位的。傳統教學理念中的身體虛無思想,不利于教學活動的展開。傳統教學理念固著于文本的傳遞,學生很難在教學中獲得切身體驗,更難于獲得教學中的精彩觀念和幸福生活,師生在教學共在系統中基于具體教學情境的心智、身體、環境的實時互動的知識建構和意義涌現被遮蔽,教學異化為知識傳遞活動。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后現代主義與消費文化的雙重推動,具身思想開始出現。身體哲學、身體美學、身體人類學等一系列交叉學科相繼出現,哲學、心理學、認識神經科學、計算機科學等對身體的研究被引入教育學之中,具身學習的概念形成了。具身學習思想是身體現象學、具身認知理論在教育研究中的折射,體現了學習中身體的重要性,要求改變以往把教學視為觀念傳遞、心智培育;把學習視為離身性的精神訓練的觀點,強調從身體活動入手,強調從身體經驗入手,融合身心一體,促進身體在教學中的成長。
祛除傳統教學的身體偏見,需要確立具身教學理念。確立具身教學理念,首先要樹立“培育整全生命的教學目標。”人是生命的存在,身體是生命存在的根本。身體之于人的生命具有根基性和本原性的意義。教學中的學生是“一種完整性的生命存在”,而非單純的思維存在。由此,教學對學生發展的關注,就不只是知識獲得、能力發展,更要協調身體知覺的敏銳性,發展身體感官能力,使學生的身體和思維自然地開釋。教學對學生發展的關注,不僅要關注學生所處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還要關注學生在特定社會歷史文化環境中的身體經驗,使其融入生活,生成智慧。其次是重建身體與知識的教育關聯。“基始的教育實踐是身體力行的。”[2]這一時期,教學與人們的生產、生活融為一體,教學具有“根身性”特征。隨著社會的等級分化以及學校教育的出現,身體與知識的教育關聯發生斷裂。孔子鄙視“為稼”“為圃”,實際上是這一問題的本質反映。教學被視為一種離身性的教育訓練活動。傳統教學認為,知識是對客觀世界的鏡式反映,是對客觀世界的靜態表征。教學內容承載的是一套統一的、靜態的、完全中立的、價值無涉的概念體系和符號系統。后現代主義強調,知識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任何知識都不是靜態的、完全中立的、價值無涉的;任何知識都處于一定的時間、空間、理論范式、價值體系等文化因素之中,是動態的、多元的、價值依歸的。教學一心專注知識傳遞,是偏離教學本義的。教學中的身體,既是起點,也是歸宿;既是目的,也是方法。教學不只是靜坐讀書,冥想致知,更應豐富、激活、建構、生成、引領學生的切身體驗,使之得以利用與改造,裨以生成個人知識,通達生活智慧。再次,鼓勵教師具身教學的行動研究,才能促成教師具身教學理念的覺醒。教師具身教學理念的形成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教師對具身認知理論的認同和接受。認知理論強烈地影響教師對教學的理解以及對學生學習的指導。傳統認知理論以“計算——表征”為根本特征,以此指導教學,教學活動日趨技術化、工具化、程式化,不利于教學中“人的培養”。變革傳統的認知理念,祛除教學的身體偏見,強調“身體知覺是認知的源泉及其發生的場域,”[3]強調學習是學習者以身體為媒介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的復雜活動中不斷自我更新的過程,突出身體在學習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強調身體整體地參與了學習活動,強調身體全面地、多維度地參與了學習活動,以此設計學習和教學。第二階段,具身教學的情境驅動。具身教學是發生在特定情境并具有良好教學效果的教學模式。專家型教師是具身教學的先行者。他們最先接受具身認知理論,并以此為基礎,設計、示范典型的教學案例,將其應用于教學實踐。這既是具身教學的切實證據,也是具身教學的很好范例。新手教師是具身教學的學習者。他們觀摩具身教學案例,反思具身教學與傳統教學的差異,將自身沉浸于具身教學的情境之中,親身感受的活躍的互動情景與良好的教學效果,激發了他們實施具身教學的熱情,鼓舞他們投身于具身教學實踐。第三階段,教師對具身教學生活史的回溯。教師在實施具身教學過程中,親身體驗了具身教學的熱烈氛圍與良好效果,內心生發的強烈感動,促使他們回顧具身教學歷程,不斷發現其中的問題并總結經驗,不斷強化具身教學的行動自覺。
二、具身學習意涵中的教學方式變革
教學理念的變革引發了教學方式的變革。教學方式即師生在教學活動中的行為方式。
針對傳統教學中“身體的偏移”,教學方式應實現從“我有身體”向“我是身體”的轉變。“我有身體”是傳統教學的普遍觀念。傳統教學則是這一觀念的代表性的教學方式。在傳統教學中,“我”和“身體”都是的實體。“我”是教學意識主體,“身體”是教學物質基礎。傳統教學的首要特征,是對身體的規訓。為了使學生專心學習,教學對身體的管束細密、嚴苛:從發型到服飾,從日常作息到言行舉止,身體無時無刻不處在監督之下。教學異化為常規化、形式化、連貫性、系統性的操作。身體被肢解為碎片,存在于一系列的數據、知識、方法、技術、規章之中。傳統教學的第二個特征是對身體的改造。傳統教學對身體改造的后果,身體成為知識的對象,成為“制度化”的身體。針對身體的管理經驗日益豐富的同時,身體經驗卻日趨貧乏。由于失去了與身體感性而豐富的聯結,知識成為浮萍。換句話說,由于教學中身體缺場,經驗缺位,知識缺乏具體定在,淪為學生頭腦中的空中樓閣。傳統教學的危機引發了教學方式的轉型——教學從“我有身體”向“我是身體”轉變。以“我是身體”指導教學和以“我有身體”指導教學,呈現出來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教學方式。“我是身體”強調教學中“我”與“身體”是統一的;“我有身體”強調教學中“我”與“身體”是對立的。教學中的身體是一個整體,是靈肉交織的統一體,不是二元對立的。作為主體和作為整體呈現在教學中的身體,不是空間中并列器官的組合,也不只是提供傳統意義上的感覺材料和意識聯想,也不只是傳統意義上心靈或思想的“刺激感受器”或“動作效應器”。教學中的身體是認知的源泉及其發生的場域。基于“我是身體”規劃、設計教學活動,知識扎根于身體,身體因知識而靈動、出彩。
教學方式的變革內涵了教學性質的轉變。美國課程論專家派納認為,課程教學實際上是教育經驗的傳遞。教育經驗總是具身存在于學習者的情感與智力的互動與參與中,并通過學習者具體而鮮活的生活過程習得。“生活經驗是非常執拗的,它總是與我們的身體相遇并進入我們的身體。”[4]由此,派納揭示了課程教學的具身性特征。由課程教學的具身性特征引出了教學的生成性、實質性、情境性特征,即教學具有具身性、生成性、情境性、實質性四重屬性。“兒童的邏輯與數學觀念,首先是作為外來活動展示出來,繼而才內化,并具有概念的性質。”[5]兒童的認識活動并非憑空生成,它建立在身體感知運動的基礎上的。進一步來說,兒童的認知經驗,需要通過身體參與來共情與理解,需要通過身體來感知和體驗。教學必須要建立在兒童經驗的基礎上,教學一開始就具有身體性質。除此之外,教學的生成性體現了教學對過程的要求;教學的實質性是教學適切性的體現,即教學實施必須具備適切的條件;教學的情境性體現了教學對環境的要求。將教學的諸多特征整合在一個框架內,強調具身教學的故事性建構。這包括兩個維度:橫向維度——教學的具身性要求把教學的身體還給學生,解放學生的身體,釋放身體活動;教學的情境性體現為教學環境(空間)的回歸,即教學把空間還給學生,把教學文本轉換為學生能夠參與其中的文化情境;教學的實質性體現為把教學內容(文本)還給學生,讓學生自主學習,通過自主探究,把教學中的人與人、人與文本、人與事物聯系起來,通過親身經歷,達成自己的認識;教學的生成性要求把教學的過程(時間)還給學生,讓學生自由掌控自己的學習。縱向維度——教學設計必須以學生的經驗為基礎;教學實施必須關注學生情感;教學最終達成預期目的——整全的人的發展。
教學方式的變革內蘊了教學主體的回歸——傳統教學中虛化的教學主體復歸為具身學習中的“身體主體”。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認為,信息技術消解了少數人壟斷知識的可能性,為個體開辟了一條非功利的、非封閉、非強制的知識通道。以此觀照傳統教學模式,教師是“無所不知”的,是“傳道、授業、解惑者”;學生是“一無所知”的,是知識填充的容器。師生在知識權利上的不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信息時代的到來,傳統教學模式中的師生不平等的知識權力結構土崩瓦解。教師的“知識權威”身份被消解,學生成為了學的真正主體。教師是學生學習的組織者、管理者、指導者、咨詢者、促進者,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學習是身體參與、獲得知識的行為。身體參與是具身學習的根本要義。由此,學生由傳統教學中抽象的“意識主體”歸化為現實教學中的“身體主體”。
教學方式的轉變內蘊了師生關系的轉變。從身體出發,重新審視教學中的師生關系,有助于打破教學對學生的控制和規訓,使教學由灌輸走向對話。在身心二元對立的背景下,教學中的師生關系是主、客體的對立關系,即如馬丁·布伯所說的“我——他”關系。“我”是主體,是教育者;“他”是客體,是受教育者。在教學中,“我”與“他”之間是一種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我”通過對“他”的控制、規范和約束,向“他”灌輸知識,“他”是“我”灌輸的對象,“他”是“我”塑造的對象,“他”也是“我”塑造的目的。超越師生關系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僵硬框架,追尋師生在教學中的生命靈動,需要轉換身體視角,即身體不是純粹的肉體,而是靈肉交織的。身體富于理性,蘊含知覺。“我”在身體知覺中見證了“他者”的存在,“他者”也在身體中見證了“我”的存在。“我”和“他者”擁有相同的身體,是我們彼此理解的基礎。“他者”被“我”的身體知覺構成,“我”也被“他者”的身體知覺建構。“我”與“他者”在身體知覺的可逆的建構中相互浸染著彼此的世界,實現彼此的理解。以這一原理審視教學中的師生關系,師生在教學場域中的際遇首先是身體的相遇。在教學中,教師首先看到的是學生的身體;學生首先看到的也是教師的身體。師生首先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鮮活個體。學生和教師的身體是平等的,蘊含于身體之中的知覺也是平等的,平等是對話和交流的基礎。唯一不同的是,是教師和學生的身體曾經的際遇不同。教學即教師以自己對世界的切身體驗召喚、激發學生對世界的切身體驗,以此在世界中實現對學生身體的建構和完型。師生在教學場域的際遇,是基于同質身體的交流與對話,而非控制與規訓。由此,教學是啟發的、對話的,而非灌輸的、規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