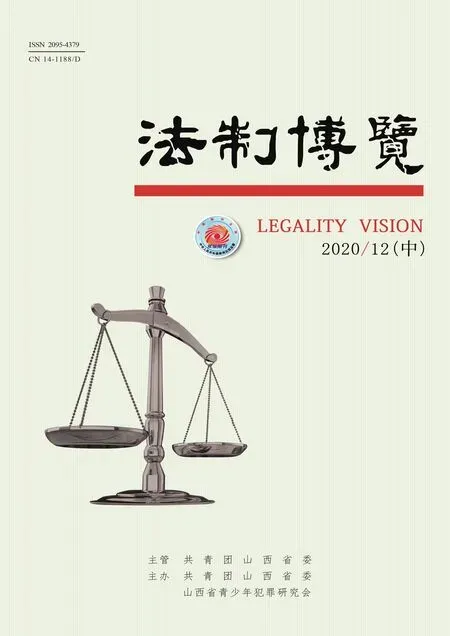民法典引入婚姻家庭法的理論分析
楊中原
中共六盤水市委黨校,貴州 六盤水 530000
在當前的民法草案中,隨著婚姻家庭法被納入民法典的獨立一篇,使得婚姻家庭法重新回歸民法典,這一改變不僅僅昭示了我國民法編纂體系的完整,更為重要的是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中相對獨立性的特點還將促使民法合流快速實現法典化的目標。民法典體系日益趨于完善也使得婚姻家庭法法律內容的豐富性得到一定的拓展,其立法價值也將得到充分發揮。面對學術界對婚姻家庭法地位的不同意見看法,需要通過對婚姻家庭法的獨立性特點展開理論分析和研究,在保障民法典完整性的同時,使婚姻法具有其相對獨立性的效果能夠得到展現。
一、民法典引入婚姻家庭法的意義
(一)調整對象的倫理屬性
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內容在于處理調整對象的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在自然關系方面,主要包括調整對象的兩性關系和血緣關系,通過分析調整對象的自然關系可以更好地掌握調整對象的關系背景與平等調整對象間的倫理屬性。而在社會關系方面,這種關系的存在只體現在人為對象上,不同時期下社會關系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男女和種族之間的不平等使得婚姻家庭法在執行過程中必須根據當前的社會倫理關系才能做出相對規范化、合理化的判決,在公民人倫關系確定后,婚姻家庭關系才能被進一步確立。婚姻家庭法對調整對象的親屬倫理關系確定有著重要意義,既要從基本倫理道德出發,考慮到夫妻、親子之間的關系使婚姻關系符合倫理、人文的要求;又要考慮婚姻關系對于社會秩序也有一定的影響。這需要從法律和道德層面來約束社會公民不正當、錯誤的婚姻行為,在對婚姻家庭關系進行調整時往往還需要借助一定的法律手段來進行強制性調整。總的來說,在民法典中引入婚姻家庭法使婚姻家庭法更具執行力,法律手段的介入也將會使婚姻家庭法具有更強的約束力作用,這對于社會秩序的穩定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1]
(二)穩固公法屬性
倫理關系是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屬性組成,如果僅是依賴于婚姻家庭法的制度條約來規范社會公民的倫理關系則會出現一定的局限性,無法對公民產生足夠的約束力,但通過法律法規的強制手段來管理倫理關系則顯得過于嚴苛,無法體現出家庭自治和保護家庭隱私,難以全面顧及家庭中每位成員的個人權益。而隨著婚姻家庭法的日益健全和在民法典中引入婚姻家庭法,使得公民獲得了更多的權益保護,如個人財產劃定、婚姻登記、離婚登記等,在婚姻家庭法執行過程中既體現了法律的嚴格,也充分考慮了公民意愿,公民有了更多的婚姻自由權,民法典對婚姻家庭法的引入將使公法屬性更為穩固。另外,婚姻家庭法的公法屬性還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婚姻家庭法將承擔社會發展、養老、教育等職能,使婚姻雙方更加明確自身的權益與職責,從而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
(三)健全完善民法體系
在傳統的民法體系中,婚姻家庭法被包含其中,這是由于我國傳統的民法體系的理論架構受到古羅馬親屬法的影響,能夠為封建時期的社會關系和婚姻制度提供完備的法律支持,在隨后的民法體系健全、完善過程中也是按照這一理論體系進行拓展、延伸。到了近代,民法典改制使得婚姻家庭法脫離民法體系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但婚姻家庭法的建法體系仍與民法具有一致性,相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體系,婚姻家庭法并不屬于私法范疇,而是遵照民法典內容作為民法典的特殊組成發揮其能效作用。[2]
二、民法典引入婚姻家庭法的理論分析
(一)從婚姻家庭法調整對象來看
我國婚姻家庭法的調整對象為兩個平等主體,因此在婚姻家庭法中對調整對象特定范圍內的親屬關系進行規定,進而明確了親屬與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關系。另外,由于婚姻家庭法是在我國法律制度體系之下建立的,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具有普遍適用性,在調整主體的私人利益關系上需要借助民法典私益內容才能配合其有效運轉。由于婚姻家庭法調整對象與民法基本一致,這說明在調整對象層面上婚姻家庭法歸位于民法,是民法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在面對特定的社會矛盾問題時,婚姻家庭法也應保持其獨立性,尤其是在處理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問題時,要根據《民法通則》第2條對公民、法人、公民與法人之間的關系要求出發,使調整對象的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得到準確的區分,并能在地位平等的角度上使對象接受民法調整,并受到民法保護。此外,在民法中還對家庭婚姻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作了進一步規范,將有關婚姻、收養、監護的協議內容進行了統一,因此無論是從婚姻家庭法的調整對象還是在民法典中的地位來看,婚姻法的引入將是促使民法結構體系趨于完善的重要決策。
(二)從婚姻家庭法立法發展趨勢來看
我國婚姻家庭法框架結構并不完全是按照現代法律體系建立的,婚姻家庭法的框架結構是按照古代立法和國外諸法融合的形式構建的,這使得婚姻家庭法在中國不同時期的形態結構有所差異,在早期封建社會時期婚姻家庭立法更多的是以“禮”為核心來建立,只是依靠約定俗成或當時社會的倫理關系來處理家庭矛盾或婚姻問題,沒有單獨成型的法律制度來規范家庭婚姻關系。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封建制度下成文法律法規的制定和統一,家庭婚姻關系問題開始有了規范化的處理方式,但在處理家庭婚姻關系上卻是采取禮、法并用的方式,家庭婚姻關系缺乏相對獨立的、健全的法律制度。到了近代中國,1911年編訂的《大清民法草案》實現了對家庭婚姻關系立法由封建近親關系到現代規范法律體系的過渡,該草案是以日本明治維新中所編訂的民法為藍本建立的,其中將家庭婚姻親屬關系納入了民法,婚姻家庭法初次成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1930年南京民國政府針對民法典中家庭婚姻親屬關系獨立成篇,使得家庭法與民法典的融合更加深入。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重新建立了新的法律制度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法典框架與西方各國的民法有著本質區別,民法典內容是以國家制度為核心進行架構,在當時采取了蘇聯并行立法模式將婚姻家庭法從民法典中剝離出來,單獨成立專門的法律部門進行管理,這一模式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新嘗試。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婚姻家庭法回歸民法典的問題備受專家和社會大眾的關注,考慮到民法的完整性和婚姻法的獨立性,學術界普遍接受把婚姻家庭法作為民法特殊的獨立的組成部分,促使婚姻家庭法的回歸勢在必行。[3]
(三)從婚姻家庭法的訴訟程序來看
在民事訴訟法中對于民事案件的起訴、審判、執行流程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在處理民事案件時必須嚴格按照訴訟流程進行。在我國,婚姻糾紛案件的屬性包含于民事案件之中,因此婚姻糾紛案件的處理流程也應按照民事案件訴訟程序執行,正是因為實體法與程序法關系的存在,使得民法內容對于婚姻家庭法具有普遍適用性,所以為婚姻家庭法應作為民事實體法而被納入民法典提供了有利的支持。[4]
三、總結
綜上所述,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中的再次回歸既是法律體系建立健全的重要途徑,又是法治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從調整對象、婚姻家庭法發展歷程及訴訟程序來看,婚姻家庭法始終離不開民法體系,民法與婚姻家庭法相輔相成,才能有效地維系社會穩定秩序,因此將婚姻家庭法納入民法典是科學合理的,可以促進社會主義法學的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