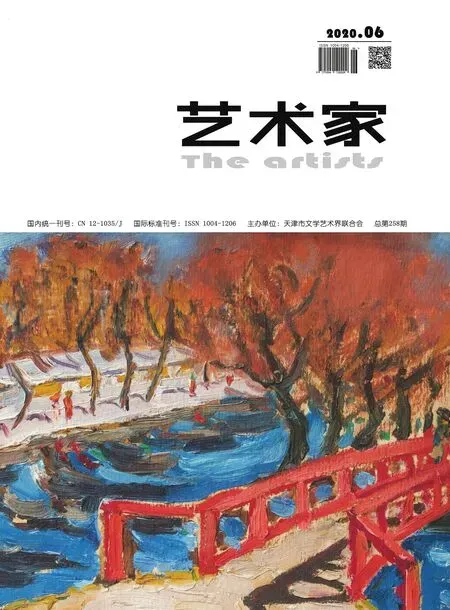煙波浩渺 萬物皆有靈
——評舞劇《銀孩子》
□王 慧 廣西藝術學院
舞劇《銀孩子》是根據原創小說改編的,由廣西藝術學院本科2013級學生出演,編導黃磊,舞美設計王動,服裝設計陳天。在白色縹緲的煙霧中,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在低聲吟唱中緩慢地舞動,哀哀婉婉的浮動逐漸將羊弟與秋姐的命運刻畫出來。這部由梅帥元先生的早期小說《銀孩子》改編的舞劇已然得到了大家的賞識。編導對于舞劇中人物的心理刻畫,使觀者對生命的輪回及人性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一、中西融合之特點
舞劇的整體結構為臨世——神諭1——亂山——迷霧——蒼風——神諭2——熔漿——塵雨——銀火——神諭3——重生,概述了銀孩子從降臨到成長,最后死亡又重生的人生過程。從動作方面來看,既運用了西方從呼吸出發引導動作的方式,又融入了中國傳統的動作與情景,從而創造出一種現代舞的中國風格。
首先,舞劇運用了西方現代舞的技術體系,在舞蹈動作上從呼吸出發,由呼吸帶動身體收縮及舒展。扮演秋姐和羊弟的兩位舞者除運用技法上的套路外,還將肢體語言與情感相互交融。從舞劇一開始,舞者就隨著彌山大霧和悠遠依稀的銅鈴聲,從舞臺兩側向中心臺緩慢舞動,整個身體彎曲在中度空間舞動,運用現代舞中的地心引力將整個身體的重力都放在地面,從而襯托出舞臺環境與人物的關系,同時迷霧又營造出現實與虛幻的模糊意境。在舞蹈語匯的選擇上,其運用大量的身體語言把主體“銀孩子”塑造得更加神秘;在舞段“亂山”中,群舞斜線波瀾起伏,時而站起,時而緩慢地下去,表現了羊弟的成長過程;最后,圍成一個圓包圍住他,所有群舞演員都趴伏在地,只有男演員自己昂首挺胸,表明羊弟已經長大成人。
其次,編導更是在舞劇中加入了大量的中國元素——靖西巫儀式,以“魔婆”儀式制造出了魔幻色彩。例如,在“神諭1”中,男演員頭戴紅色紗巾,女演員手拿紅扇,再現了壯族巫儀式中的活動內容;“神諭2”更加具體地刻畫了這一儀式活動,這次是男演員手拿紅扇而舞,多次重復雙手向上攤開雙腿開胯蹲起的動作,以此來表現男子那種充滿張力的氣魄,從而突出人物的血氣方剛與桀驁不馴;群舞中出現的雙膝跪地卷腰起來又低頭跪拜動作,表現了當地人們對“銀孩子”的祭祀。舞劇《銀孩子》這種中西元素的巧妙結合,創造了一種獨具中國風格的現代舞。
二、心理空間之特性
舞劇《銀孩子》中的舞臺空間,豐富了對心理結構的刻畫。在舞段“銀火”中,呈現出了兩個不同的虛擬空間——羊弟在一個空間,而秋姐在另一個空間,這兩個虛擬空間相互獨立,這樣能更加立體、多層面地表現他們內心的情感活動。開始一位手持銀色長旗的男演員從上場口直沖較為明亮的臺前1區位置,銀色的長旗代表礦山,男演員邁著矯健的步伐揮舞著,大幅度的舞動表明羊弟在礦洞里不畏艱苦、努力奮斗,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期待能夠早日與秋姐相見。同時,舞臺3區的女演員共同構造出了舞臺空間,女演員始終在燈光暗淡的臺口,這里代表監獄,面對男演員雙手向上延伸又吐氣松懈下來,仿佛在洗刷著自己的罪孽。由此,在舞臺空間中形成了兩種情景,隨之呈現出人們不同的心理狀態,極大地豐富了舞劇的心理結構。此外,舞蹈快要結束時群舞包成一個圓,這個圓具有抽象含義,它是一種悲劇的象征,是無法解脫的一種命運枷鎖,羊弟眼看著大火封死了出口,這時神祇的出現仿佛在召喚你就是“銀孩子”的化身。
三、生命哲學之悟性
舞劇《銀孩子》是通過小說改編而成的,以故事情節發展為脈絡,將人物性格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塑造了一個充滿虛幻的人性世界,通過對羊弟與秋姐之間的情感把握,讓觀眾看到了羊弟成年后的情感轉變,從原先情感束縛中的解放,到后來與命運抗爭的無力感,最終沒有擺脫命運的枷鎖。最后一幕當死亡降臨時其復雜的心理變化,使觀眾產生對人性的思考。秋姐這一角色,過早地懂得了世俗追求,她沒有抵制物欲的誘惑,而選擇了現實的一面,她是羊弟心中一直向往著的愛情,這引發了觀眾的感想。人們會對在大火中死去的羊弟感到悲哀,也會在最后神祇的出現時表明他好像就是銀孩子的化身而感到敬畏,無論是什么,我們都會在這部舞劇所啟示的充沛情感中收獲自己的一份獨特的領悟。而通過這個舞劇的情節脈絡我們可以看到,由于礦山被過度開發,以及不斷商業化地發展,人們受到了大自然的懲罰,最后羊弟化身為銀孩子,綿長的哼唱,縹緲在世人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