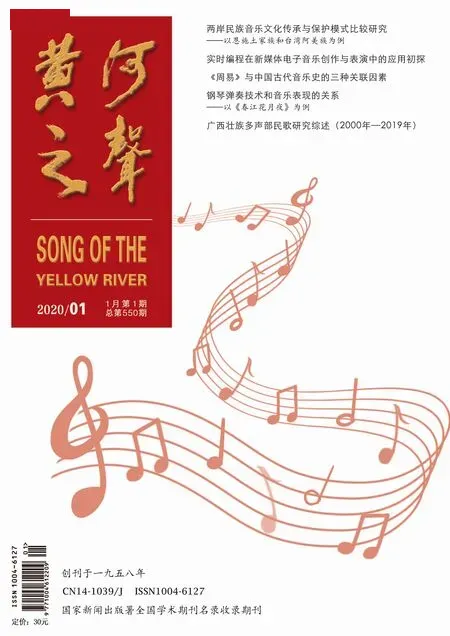兩岸民族音樂(lè)文化傳承與保護(hù)模式比較研究
——以恩施土家族和臺(tái)灣阿美族為例
賀晶嫻/ 周莉 [中國(guó)地質(zhì)大學(xué)(武漢)]
概 述
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原住民作為臺(tái)灣本土的族群,其音樂(lè)文化源遠(yuǎn)流長(zhǎng)。由于族群歷史、部落傳統(tǒng)以及當(dāng)代生活方式的不同,呈現(xiàn)出獨(dú)特的音樂(lè)表達(dá)方式和特點(diǎn)。阿美族作為原住民中人口最多的族群,他們沒(méi)有自己的文字,音樂(lè)是他們最為珍貴的財(cái)富。依據(jù)巴奈·母路對(duì)阿美族音樂(lè)功能性的劃分,阿美族音樂(lè)可分為祭儀性與非祭儀性音樂(lè)(生活歌曲、工作歌曲、童謠)兩類。祭儀性的音樂(lè)包括巫師治病歌、乞雨歌、豐年祭男女合舞歌、成年祭儀式之歌等;非祭儀性音樂(lè)包括除草歌、歡樂(lè)歌、工作歌等,歌曲的意義通過(guò)標(biāo)題一目了然。[1]
而大陸地區(qū)的土家族主要居住在湘西、鄂西兩個(gè)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我國(guó)人口數(shù)排名第七的少數(shù)民族。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全國(guó)土家族人數(shù)最多的地區(qū),約占總?cè)丝诘?4.9%。土家族人民善歌善舞,其民族音樂(lè)種類豐富多彩,以漢族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的種類劃分依據(jù)為參考標(biāo)準(zhǔn),本地區(qū)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的種類在一級(jí)分類層面上,同樣也可以包括民間歌曲、民間歌舞音樂(lè)、曲藝音樂(lè)、戲劇音樂(lè)及民間器樂(lè)五個(gè)部分。[2]
一、對(duì)比研究
(一)音樂(lè)傳承人傳承
對(duì)于沒(méi)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來(lái)說(shuō),表演者的演藝技能的傳承可能局限在家庭或者社群,具有首屬群體內(nèi)部的口頭傳承性質(zhì);也可能是在戲班乃至寺院、道觀等,具有次屬群體中師徒傳承的性質(zhì)。[3]在此中音樂(lè)傳承人作為“活”的音樂(lè),聲口相傳直接參與了民族音樂(lè)的傳承過(guò)程,這使音樂(lè)傳承人傳承在民族音樂(lè)的傳承與保護(hù)中顯得尤為的重要。
恩施目前有4位國(guó)家級(jí)、18位省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傳傳承人,根據(jù)《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代表性傳承人認(rèn)定與管理暫行辦法》規(guī)定,各級(jí)文化行政部門應(yīng)對(duì)確有困難開(kāi)展傳習(xí)活動(dòng)的國(guó)家級(jí)非遺代表性項(xiàng)目的傳承人予以一定的支持。而傳承人們?cè)谙硎車?guó)家支持政策的同時(shí),也要承擔(dān)相關(guān)的義務(wù),義務(wù)包括提供完整的技藝要領(lǐng)、報(bào)備項(xiàng)目傳承計(jì)劃和目標(biāo)、開(kāi)展技藝傳承工作、參與文化交流展示和定期匯報(bào)項(xiàng)目傳承情況。
而臺(tái)灣地區(qū)則是甄選對(duì)于重要的民族藝術(shù)具有卓越技藝者為藝師,簡(jiǎn)稱重要民族藝術(shù)藝師,審查合格的藝師頒發(fā)證書,并可以擔(dān)任民族藝術(shù)訓(xùn)練機(jī)構(gòu)教職或各級(jí)學(xué)校的藝能教師,同時(shí)在從事重要民族藝術(shù)研究工作時(shí),可以申請(qǐng)補(bǔ)助經(jīng)費(fèi)。而藝師們必須要參與的傳藝工作則包括收徒、任教和展演。
由以上可以看出,我國(guó)大陸地區(qū)和臺(tái)灣地區(qū)都出臺(tái)了相關(guān)的政策來(lái)認(rèn)定民族音樂(lè)傳承人,相比之下大陸地區(qū)的政策更加的完善,且具有系統(tǒng)性,已擁有一整套非遺傳承人認(rèn)定與管理體系。被認(rèn)定的民族音樂(lè)傳承人大陸地區(qū)稱之為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而臺(tái)灣地區(qū)則叫做藝師,二者都經(jīng)過(guò)相關(guān)組織判定甄選,在享有一定福利資助的同時(shí),也有義務(wù)需要完成帶徒傳藝和參與展演競(jìng)賽。不同的是臺(tái)灣地區(qū)被認(rèn)定的藝師還需要根據(jù)各地的需求,前往大中小學(xué)任教傳授技藝。
(二)民族節(jié)日傳承
傳統(tǒng)節(jié)日音樂(lè)是傳統(tǒng)節(jié)日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二者相互依存,民族節(jié)日音樂(lè)與民族節(jié)日的主題、功能、作用契合,更有只能在特定的節(jié)日中演唱、平日被禁唱的歌曲,民族節(jié)日音樂(lè)和節(jié)日融為一體,成為一種節(jié)日的符號(hào)。
祭儀節(jié)日是阿美族重要的部落性活動(dòng),族人們都會(huì)參與進(jìn)祭儀活動(dòng)中,通過(guò)傳統(tǒng)節(jié)日將一些在節(jié)日中特定演唱的民族音樂(lè)在部落中傳承下去。略有遺憾的是,受到政治環(huán)境、生活環(huán)境等大環(huán)境的影響,很多節(jié)慶、祭儀活動(dòng)已不復(fù)存在。同時(shí)阿美族祭儀音樂(lè)的嚴(yán)肅特殊性,有些歌曲只能特定的人進(jìn)行演唱,無(wú)法進(jìn)行大范圍的傳播,同時(shí)參與祭祀團(tuán)體的成員人數(shù)日趨減少,參與祭儀的族人年齡偏大,缺少年輕的族人們參與,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族音樂(lè)的傳承與發(fā)展。
而恩施土家族主要的節(jié)日類型分三種:祭祀節(jié)日、農(nóng)耕節(jié)日和功利節(jié)日。土家族的民族節(jié)日是土家族人的歷史沉淀和生活積累,體現(xiàn)了土家族文化不斷轉(zhuǎn)變和發(fā)展的流動(dòng)狀態(tài)。“女兒會(huì)”是恩施州土家族具有代表性的區(qū)域性民族傳統(tǒng)節(jié)日之一,每年到了這一天,恩施都會(huì)舉行“女兒會(huì)”節(jié)慶民俗活動(dòng),這已經(jīng)成了恩施市的一項(xiàng)旅游項(xiàng)目,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來(lái)參與。
由以上可以看出,臺(tái)灣阿美族和恩施土家族都有各自的民族節(jié)日,由于生活環(huán)境和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部分節(jié)慶祭儀活動(dòng)漸漸流逝在歷史的長(zhǎng)河中,僅剩下一部分節(jié)慶活動(dòng)。阿美族的節(jié)慶活動(dòng)主要為一些部落性的祭儀活動(dòng),主要針對(duì)部落族群內(nèi)部,并且由于阿美族部落主要分布在立霧溪以南的東臺(tái)縱谷和東海岸平原遠(yuǎn)離都市,而族群內(nèi)的年輕族人們大多離開(kāi)部落到城市里打拼,很難有時(shí)間趕回部落參與祭儀活動(dòng),所以目前的祭儀活動(dòng)的參與者主要為常年留在部落中的中老年族人。恩施土家族主要的節(jié)慶活動(dòng)為土家女兒會(huì),與阿美族不同的是,土家女兒會(huì)的參與者除了面向土家族人外,還面向所有慕名而來(lái)的恩施當(dāng)?shù)仄渌褡迦撕陀慰停诠?jié)慶音樂(lè)的演唱上和阿美族由族人或特定人士演唱不同,所有前來(lái)參與節(jié)慶活動(dòng)的人,都可以參與到節(jié)慶音樂(lè)的演唱當(dāng)中,與土家族人一起歡慶節(jié)日。
(三)音樂(lè)競(jìng)賽及展演傳承
民族音樂(lè)屬于民間文化活動(dòng)形態(tài),其文化藝術(shù)活動(dòng)的主體存在于民間,通過(guò)音樂(lè)競(jìng)賽和展演活動(dòng)可以發(fā)現(xiàn)、挖掘年輕一代優(yōu)秀的音樂(lè)傳承人,使民族音樂(lè)得到“活”的傳承;競(jìng)賽及展演通過(guò)評(píng)比打分的形式,調(diào)動(dòng)群眾學(xué)習(xí)民族音樂(lè)的積極性,擴(kuò)大民族音樂(lè)的影響范圍,提高群眾對(duì)民族音樂(lè)的掌握程度;音樂(lè)競(jìng)賽和展演活動(dòng)建立了固定的競(jìng)賽展演制度,使民族音樂(lè)的評(píng)判更加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化。
多麗絲·萊辛以細(xì)膩的筆觸描寫了殖民地背景下瑪麗的心理和現(xiàn)實(shí)的困境。“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間的較量構(gòu)成了瑪麗的心理困境,也正是因?yàn)楝旣惖男睦砝Ь常⒍爽旣惖谋瘎 6旣惖默F(xiàn)實(shí)困境則是迪克的經(jīng)營(yíng)不善導(dǎo)致瑪麗整日只能在炎熱的鐵皮屋里度過(guò),甚至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維持。
臺(tái)灣地區(qū)每年都會(huì)定期開(kāi)展“大專院校原住民族傳統(tǒng)樂(lè)舞競(jìng)賽”、“大專青年原住民族樂(lè)舞交流演出”和“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母語(yǔ)歌謠暨歌舞劇競(jìng)賽活動(dòng)”等相關(guān)音樂(lè)競(jìng)賽及展演活動(dòng),主要由原住民族人參與,逐漸吸引其他民族人民,借由參與過(guò)程,使原住民族人更加認(rèn)同自身文化,同時(shí)也讓非原住民族人推廣原住民族樂(lè)舞,讓原住民族樂(lè)舞已向其他族群擴(kuò)散發(fā)展。
在音樂(lè)競(jìng)賽及展演方面,恩施州則主要舉辦了龍船調(diào)藝術(shù)節(jié)以及利川市山民歌傳唱大賽。2009年舉辦了第一屆龍船調(diào)藝術(shù)節(jié),將歌曲與舞蹈結(jié)合,舉辦了全國(guó)土家族苗族歌舞發(fā)展論壇,開(kāi)展了土苗族歌舞比賽;2018年第二屆龍船調(diào)藝術(shù)節(jié)則是與湖北省第九屆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運(yùn)動(dòng)會(huì)聯(lián)合舉辦,將音樂(lè)與體育相結(jié)合,其中肉連響將首次納入湖北省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xiàng)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廣、宣傳土家族傳統(tǒng)音樂(lè)的作用。
由上可以看出,臺(tái)灣地區(qū)每年定期舉辦原住民樂(lè)舞競(jìng)賽展演,主要面向原住民逐漸輻射向其他民族人民,同時(shí)在表演展示已有樂(lè)舞節(jié)目的基礎(chǔ)上,重視民族樂(lè)舞的創(chuàng)編。而恩施地區(qū)根據(jù)當(dāng)?shù)孛褡鍢?lè)舞的特色,將音樂(lè)與舞蹈、體育競(jìng)賽相融合,同時(shí)注重恩施傳統(tǒng)音樂(lè)的全民化傳播,將恩施土家族傳統(tǒng)音樂(lè)在恩施州各縣市進(jìn)行傳唱,重點(diǎn)打造“龍船調(diào)”品牌。
(四)旅游傳承
隨著國(guó)家經(jīng)濟(jì)文化的快速發(fā)展,相關(guān)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政策的出臺(tái),為了適應(yīng)民族地區(qū)文化旅游業(yè)的發(fā)展,民族藝術(shù)文化與日益發(fā)展的旅游業(yè)緊密的聯(lián)系在了一起。在民族音樂(lè)文化方面,少數(shù)民族挖掘發(fā)現(xiàn)民族音樂(lè)的內(nèi)涵和閃光點(diǎn),使之成為各地重要的旅游資源,挖掘了保護(hù)和傳承民族音樂(lè)文化的新方式,也為當(dāng)?shù)芈糜螛I(yè)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機(jī)遇和可能。
旅游傳承是恩施土家族音樂(lè)的一個(gè)重要傳承方式,在恩施旅游發(fā)展步入快車道的進(jìn)程中,恩施民歌以其獨(dú)特的魅力征服游客,在恩施重點(diǎn)旅游景區(qū)大峽谷、土司城、騰龍洞以及土家女兒城中都有民族傳統(tǒng)藝術(shù)文化和民俗活動(dòng)的蹤影,利川騰龍洞景區(qū)的激光秀和極具土家族民族特色的大型劇目《夷水利川》的演出收入已成為騰龍洞景區(qū)收入的主要來(lái)源,恩施大峽谷中的《龍船調(diào)》吸收了恩施地區(qū)土家族民族音樂(lè)元素和表現(xiàn)形式,汲取土家文化,同時(shí)結(jié)合恩施大峽谷景點(diǎn)特色,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景區(qū)觀看。[4]
臺(tái)灣地區(qū)打造了多個(gè)原住民文化園區(qū),例如臺(tái)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qū)、九族文化村和阿美族民俗中心,每個(gè)文化園區(qū)都會(huì)有專業(yè)的民族歌舞劇團(tuán)進(jìn)行民族歌舞展演,也會(huì)安排相關(guān)的民族樂(lè)器和民族技藝的體驗(yàn)活動(dòng),同時(shí)開(kāi)發(fā)民族傳統(tǒng)節(jié)日,面向游客開(kāi)展節(jié)慶活動(dòng),歡迎游客一同參與節(jié)慶活動(dòng)。除了文化園區(qū),在國(guó)際發(fā)展生態(tài)旅游的大熱潮下,臺(tái)灣也出現(xiàn)了部落生態(tài)旅游,以臺(tái)東阿美族刺桐部落為例,刺桐部落的目前的生態(tài)旅游規(guī)劃為阿美族傳統(tǒng)歌謠及舞蹈表演、傳統(tǒng)手工藝及生活體驗(yàn)等,以體驗(yàn)部落生活與生產(chǎn)為主要目的。[5]
由以上可以看出,恩施將民族音樂(lè)融入進(jìn)已有的自然景區(qū)中,重點(diǎn)打造恩施土家族“龍船調(diào)”品牌,用成功的大型劇目吸引海內(nèi)外游客,并以此來(lái)推廣恩施民族音樂(lè)藝術(shù)。臺(tái)灣則是建造新的文化園區(qū),將各原住民部落民族藝術(shù)文化整合在一起,同時(shí)推廣原住民部落生態(tài)旅游。
(五)藝術(shù)教育傳承
1.教育政策
恩施州在幼兒乃至初高中階段,對(duì)民族音樂(lè)教育沒(méi)有頒布相對(duì)應(yīng)的硬性政策文件,對(duì)擁有民族音樂(lè)技能的學(xué)生也沒(méi)有相關(guān)的加分優(yōu)錄政策,只有全國(guó)統(tǒng)一的少數(shù)民族考生身份加分的高考加分政策,并不涉及到少數(shù)民族技藝部分。臺(tái)灣“教育部”于1993年修訂了國(guó)民小學(xué)鄉(xiāng)土教學(xué)活動(dòng)課程標(biāo)準(zhǔn),“鄉(xiāng)土語(yǔ)言教學(xué)”正式被列入中小學(xué)選修課程,1999年出臺(tái)了“原住民族教育法”,明確規(guī)定了“各級(jí)各類學(xué)校實(shí)施原住民民族語(yǔ)言、文化及藝能有關(guān)之教學(xué)”,2000年正式頒布《國(guó)民中小學(xué)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要求國(guó)小學(xué)生在選修課程上必須就閩南語(yǔ)、客家語(yǔ)、原住民語(yǔ)等三種鄉(xiāng)土語(yǔ)言選一種進(jìn)行研究。[6]2001年出臺(tái)了《原住民語(yǔ)言能力認(rèn)證辦法》,開(kāi)始實(shí)行族語(yǔ)能力認(rèn)證考試,將族語(yǔ)認(rèn)證考試的成績(jī)作為原住民族高考加分的依據(jù)。
恩施州中小學(xué)沒(méi)有編寫并使用專門的民族音樂(lè)教材,目前使用的都是全國(guó)統(tǒng)一的音樂(lè)教材。臺(tái)灣地區(qū)于1998年增設(shè)的鄉(xiāng)土教學(xué)活動(dòng)以及“九年一貫”新課程規(guī)定,授權(quán)各縣市可以根據(jù)各地的特色和發(fā)展需要,自行編寫合宜的鄉(xiāng)土教材,內(nèi)容依照各縣市的文化、資源、環(huán)境等特色,與當(dāng)?shù)厣罹o密相關(guān),其中包含了阿美族歷史、語(yǔ)言、藝術(shù)文化等原住民教育知識(shí)。
3.教育課程
恩施州利川市將肉連響融入進(jìn)中小學(xué)乃至大學(xué)的課間操和運(yùn)動(dòng)會(huì)中,將傳統(tǒng)民族藝術(shù)與學(xué)校教育融合,力求民族藝術(shù)的普及化,但是除此之外中小學(xué)并無(wú)開(kāi)設(shè)相關(guān)土家族音樂(lè)課程,只有各地文化館、非遺傳承中心會(huì)在周末及寒暑假期間開(kāi)設(shè)相關(guān)的課程以及講座。除了普及化的民族藝術(shù)文化教育,大陸地區(qū)還舉辦了“全國(guó)民委少數(shù)民族藝術(shù)人才培訓(xùn)班”,旨在培養(yǎng)頂尖的少數(shù)民族藝術(shù)創(chuàng)作人才。而位于恩施市的湖北民族學(xué)院下設(shè)有民族研究院和藝術(shù)學(xué)院,音樂(lè)專業(yè)則是主要培養(yǎng)以學(xué)習(xí)西方音樂(lè)理論為主的音樂(lè)文化人才。臺(tái)灣地區(qū)中小學(xué)為了配合“九年一貫”的教學(xué)改革,開(kāi)始推行“校本課程”和開(kāi)展暑期學(xué)校——第三學(xué)期教育等一系列課程。除了中小學(xué)的校本課程,臺(tái)灣地區(qū)也注重各層次學(xué)生的民族音樂(lè)的教育傳承,其中原住民部落幼兒托育班和原住民部落大學(xué),分別為幼兒和社會(huì)各年齡層次的人士開(kāi)設(shè)包括原住民族音樂(lè)在內(nèi)的原住民族技能培訓(xùn)。同時(shí)隨著臺(tái)灣地區(qū)主流教育體制下推動(dòng)開(kāi)展原住民特色教育,目前各高中職級(jí)大專院校廣泛開(kāi)設(shè)“原住民藝能專班”、“原住民專班”和“原住民民族學(xué)院”。1999年3月“教育部”公布“高級(jí)中等學(xué)校設(shè)置原住民藝能專班試行要點(diǎn)”政策,該政策推動(dòng)臺(tái)灣各大專院校增設(shè)了原住民專班。
4.教育師資
恩施州各縣市大中小學(xué)教師大多為非土家族籍的教師,并且都是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的西方音樂(lè)理論培養(yǎng)出來(lái)的音樂(lè)教師,2015-2018年期間,恩施州各縣市公開(kāi)招聘音樂(lè)舞蹈方向教師34名,招聘要求多為學(xué)歷及研究成果,專業(yè)方向需求也集中在西洋音樂(lè)表演及理論,沒(méi)有招聘崗位需求為土家族音樂(lè)方向。臺(tái)灣“民原會(huì)”于2010年6月發(fā)布了“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雇用支援教師”的公告,要求設(shè)有原住民族資源教室的學(xué)校必須甄選常駐民族教師一名,其中民族教師必須具備原住民身份,母語(yǔ)認(rèn)證資格及高中學(xué)歷。而各“原住民藝能專班”、“原住民專班”和“原住民民族學(xué)院”也都是有專任的原住民族教師。
5.小結(jié)
由以上可以看出,大陸地區(qū)在政策上沒(méi)有對(duì)少數(shù)民族作太多傾斜,沒(méi)有將學(xué)習(xí)和傳承民族音樂(lè)文化列入官方文件中,硬性要求學(xué)生學(xué)習(xí)和傳承民族音樂(lè)文化,也沒(méi)有編寫出版系統(tǒng)的民族音樂(lè)教材,供中小學(xué)生學(xué)習(xí)。在中小學(xué)的基礎(chǔ)教育上將民族音樂(lè)舞蹈與課間操、運(yùn)動(dòng)會(huì)相融合,用新的方式進(jìn)行民族音樂(lè)舞蹈的傳承與推廣。而在高層次的民族藝術(shù)文化人才的培養(yǎng)中,主要的學(xué)習(xí)內(nèi)容以少數(shù)民族歷史以及藝術(shù)文化理論為主,較少涉及到藝術(shù)實(shí)踐領(lǐng)域,師資力量也主要集中在西洋音樂(lè)表演及理論方向。
而臺(tái)灣地區(qū)從1993年起陸續(xù)頒布了多項(xiàng)政策,要求各種小學(xué)學(xué)習(xí)民族技藝,并把原住民音樂(lè)文化中的靈魂——民族語(yǔ)言作為學(xué)習(xí)與傳承的重點(diǎn),同時(shí)雖也沒(méi)有編寫統(tǒng)一系統(tǒng)的民族音樂(lè)教材,但各地區(qū)中小學(xué)根據(jù)當(dāng)?shù)氐奶厣鞍l(fā)展需要,也編寫了適合當(dāng)?shù)氐摹班l(xiāng)土教材”。臺(tái)灣地區(qū)重視民族音樂(lè)的根本——原住民族族語(yǔ)的學(xué)習(xí)與傳承,各大中小院校聘請(qǐng)專業(yè)的原住民教育人才開(kāi)設(shè)“校本課程”、“原住民藝能專班”、“原住民專班”和“原住民民族學(xué)院”等這樣極具特色的原住民族教育課程,開(kāi)設(shè)“接地氣”的原住民課程。
二、對(duì)比
在音樂(lè)傳承人傳承上,對(duì)比體制,我國(guó)大陸地區(qū)非遺傳承人傳承機(jī)制與系統(tǒng)更為完善,完善的體制系統(tǒng)便于民族藝術(shù)傳承人的管理,也能促進(jìn)民族藝術(shù)的傳承與保護(hù)。對(duì)比傳承人義務(wù)內(nèi)容,臺(tái)灣藝師任教義務(wù),讓專業(yè)的民族藝術(shù)教師進(jìn)學(xué)校,協(xié)助學(xué)校的普通音樂(lè)教師學(xué)習(xí)發(fā)展民族藝術(shù)文化的技藝,能夠有效地推動(dòng)民族教育課程。
在民族節(jié)日傳承上,由于阿美族民族祭儀活動(dòng)的文化特性和政治環(huán)境等因素的影響,其民族節(jié)日的參與者多為族群內(nèi)部的中老年族人,部分祭儀音樂(lè)的演唱也因其族群內(nèi)嚴(yán)格的階級(jí)制度只能由特定的人來(lái)演唱,這使得一部分的祭儀音樂(lè)傳承困難,最終只能失傳。而恩施土家族的民族節(jié)日大多面向大眾,邀請(qǐng)所有前來(lái)參與節(jié)慶活動(dòng)的人都參與到節(jié)慶音樂(lè)的演唱當(dāng)中,打破了民族與民族間的邊界,擴(kuò)大了土家族音樂(lè)的傳唱度。
在音樂(lè)競(jìng)賽及展演傳承上,臺(tái)灣地區(qū)舉辦的民族音樂(lè)競(jìng)賽更具有連續(xù)性,每年定期舉辦,推動(dòng)各培養(yǎng)單位有針對(duì)性的組織練習(xí),以面向原住民族人為主,漸漸擴(kuò)大到其他各民族,同時(shí)也組織舉辦原住民族音樂(lè)創(chuàng)作比賽,重視民族樂(lè)舞的新創(chuàng)。而恩施地區(qū)舉辦的民族音樂(lè)競(jìng)賽不具有連續(xù)性,參賽人員面向各族人民,主要通過(guò)比賽來(lái)進(jìn)行土家族民歌的推廣與宣傳,更注重民歌的傳唱度。
在旅游傳承上,恩施州將民族音樂(lè)文化與已有的自然景區(qū)相融合,結(jié)合現(xiàn)代科技手段,打造富有土家族民族特色的藝術(shù)作品。通過(guò)大型的劇目演出,將民族文化轉(zhuǎn)化成經(jīng)濟(jì)價(jià)值,使民族音樂(lè)文化與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相結(jié)合,重點(diǎn)打造恩施州旅游品牌。臺(tái)灣地區(qū)則是新建文化園,整合各原住民族文化資源,將原住民樂(lè)舞表演作為園區(qū)的一部分展示于其中,同時(shí)推動(dòng)部落發(fā)展生態(tài)旅游,旅游的重點(diǎn)集中在原始部落生活和樂(lè)舞文化的體驗(yàn)。
在藝術(shù)教育傳承上,目前大陸地區(qū)還主要培養(yǎng)的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上的,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西方藝術(shù)理論教育的人才。相比大陸地區(qū),臺(tái)灣地區(qū)更加重視民族傳統(tǒng)技藝的藝術(shù)實(shí)踐,重點(diǎn)培養(yǎng)各層次的以本民族的音樂(lè)文化身份為其音樂(lè)文化身份的原住民族樂(lè)舞藝術(shù)人員和理論人才。
結(jié) 語(yǔ)
由于歷史發(fā)展、文化變遷、政治環(huán)境、族際關(guān)系、教育體系等原因的影響,大陸地區(qū)和臺(tái)灣地區(qū)民族音樂(lè)文化傳承與保護(hù)模式也有所不同。以本文所選的案例,大陸地區(qū)更注重民族音樂(lè)的普及度和其帶來(lái)的經(jīng)濟(jì)效益,在人才的培養(yǎng)上主要培養(yǎng)的是民族藝術(shù)文化大類下的理論人才;臺(tái)灣地區(qū)更注重民族音樂(lè)的本土化和原生態(tài),注重民族技藝實(shí)踐,培養(yǎng)以本民族的音樂(lè)文化身份為其音樂(lè)文化身份的原住民族樂(lè)舞藝術(shù)人員和理論人才。兩種模式各有千秋,沒(méi)有優(yōu)劣之分,可以相互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