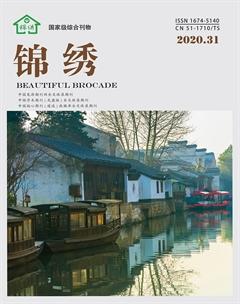“物哀”文化視角下日本人的身份建構
摘要:物哀文化作為日本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對日本人的身份建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采用定性分析,對物哀視角下日本人的身份建構進行研究,在“物哀”文化的影響下,日本人構建其“弱者”,“友人”與“無畏者”的身份。
關鍵詞:物哀;無常感;身份建構
“物哀”最早是出現在日本江戶時代學者本居宣長的《源氏物語玉的小節》一書中,追溯“哀”因素的起源,首先可以從地理環境來看。日本只是太平洋上的小島,地理位置上相對獨立,加上日本南北分別處在熱帶和寒帶之中,氣候差異大,這種自然條件使得日本所有的大城市幾乎都集中在日本列島太平洋沿岸,于是生活在那里的日本人將自己稱為“里日本”,居民們都帶著一種深深的自卑感。加上日本災害頻繁,夏有臺風,冬有雪害,最讓日本人感到不安的是火山眾多,地震頻發,在這樣的環境里,日本人習慣性地將人生看作蟀蟒一般,輕如草芥、短暫易逝。因此,無論是對于自然還是人生,對外物還是自身,他們都抱有一種悲憫之心,哀切之感。
“物哀”因素一直深深滲透于日本文化及日本民族性格的各個角落,結合Tajfel &Tunner的社會身份理論來看,日本人的“物哀”文化與日本人的自我身份建構是有必然聯系的。而提到日本的“物哀”文化,就不得不提到“無常感”這個詞。日本人的“物哀”即會對自然和人生產生一種無常感。這種“無常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日本人對自我的認知,從而影響其身份的構建。本文主要結合Tajfel &Tunner的社會身份理論,以定性分析來對日本人構建的身份進行剖析和理解。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日本是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這種地理環境給日本人帶來了不可把控的恐懼,對自然的敬畏,形成日本人的“物哀”文化。而在這種文化氛圍下,日本人產生了這樣的自我認知:人在自然的面前是渺小的,不可相提并論的;面對自然這個強而有力的對手,人是不堪一擊的弱者。由于物哀文化的影響,面對強有力的自然,日本人給自己建構了“弱者”這一身份。這一“弱者”身份,在日本人處理很多問題時都有所反映。尤其是在日本如今談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事件的時候,對于日本所犯下的罪行總會輕輕帶過甚至不提,而會著重強調日本受到的原子彈爆炸帶來的無窮傷害,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有學者認為這是戰后美國和日本政府對日本民眾引導的結果。而筆者認為究其根本,一個民族的文化對民眾的影響才是深入骨髓的。日本人在“物哀”文化下構建的弱者身份也是一直伴隨著日本人的。在二戰中的失敗,原子彈的爆炸,日本人的弱者身份在此時就會起作用,讓其自然的將自己歸為弱者,因為是弱者,自然而然就是受到傷害的一方,加上政府的引導,民眾就更確信自己是受害者。一直到現在,日本人的這種弱者身份也是一直存在的。
再者,面對自然的弱小,會讓日本人覺得自己不如別人,所以大多數日本人一生都在小心翼翼的反省自己,不要犯錯,不要給別人添麻煩,不要有情緒和行為上的起伏波動。他們的這種反省和對個人行為的約束事實是對自己弱者身份的行為反應。
前面說到日本文化及其國民性中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那就是經常出現各種極端的矛盾統一,反映到其身份建構中也是如此。日本人面對強大自然,建構了自己的弱者身份,而與此同時,在這種“物哀”文化的影響下,日本人一方面感嘆于自己的弱小,另一方面也會敬畏自然的強大,所以日本人對神秘的大自然又是充滿崇敬與向往的,在與自然的相處中,日本人又構建了自己與自然友人身份。在自然保護方面,日本是環保大國(張釗《簡析日本環境保護現狀》),日本人對自己與自然的友人身份很堅信的。這種“友人身份”不僅表現在日本人對待自然環境的方式上,也會反映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上,在這方面日本人表現出來的都是很恭謙的,待人彬彬有禮的。
本尼迪克在《菊與刀》中有這樣的論述“日本的心理機制有一條公認的原則,即意志應該超越身體。”所以對一個日本人來說,無論他的一生是如何的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當他垂垂老去,不再有工作能力之時,還是會被無情地稱為“大號垃圾”,因為他的意志已經無法控制身體。在很多日本人的觀念中,喪失了對社會做出貢獻的能力,就喪失了存活的意義,這也是日本老年人自殺率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人無時無刻不在感懷哀傷,因為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唱嘆著時光飛逝、青春易老,感嘆著時刻臨近的死亡。一朵花的盛開是它凋謝的開始,一個生命的誕生是它結束的預言。日本人對待犧牲的態度是肯定的。他們不把“犧牲”當作是一種失去、一件壞事,而將它當作是一件好事。他們認為犧牲會從精神上提高自己,他們會因此而得到“回報”。但是不論他們怎樣強調“犧牲”帶來的好處,都不意味著他們為此采取的極端行為不是真正嚴重的折磨,不會給他們的身體帶來傷害。日本人認為最大的犧牲莫過于自我毀滅,于是他們將死渲染得正大清明,無比崇高,并不懼死亡。正是有這種“物哀”文化的基底,日本才構建起其面對死亡無畏者的身份。
本文以定性分析法對“物哀”文化視角下日本人的身份建構進行了討論,發現日本人的身份建構是具有矛盾和統一性的,在“物哀”文化的影響下,日本人構建其“弱者”,“友人”與“無畏者”的身份,這些身份對其日常行為也具有很大影響,“弱者”身份使日本人時刻提醒反省自己,不給別人帶來麻煩;“友人”身份讓日本人保持恭謙的態度對待自然和和周圍的人與事物;“無畏者”的身份則讓日本人擁有面對死亡不同的勇氣與對待死亡無畏態度。不過本文僅僅是進行了定性分析,后續可以考慮與語料庫結合進行更詳細的分析。
參考文獻
[1]陳建平.王加林:互文性與身份建構話語策略[J].中國外語. 2014年第2期. 32-38.
[2]翁麗霞:試論日本文化的源與流.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52-55.
[3]涂有明:社會身份理論概述.延邊黨校學報.2009年.第24卷第5期.68-69.
[4]劉然:淺析日本文化中的“哀”因素.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作者簡介:李瑩萌,女,1993年6月,漢族,湖北宜城人,助教,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碩士,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