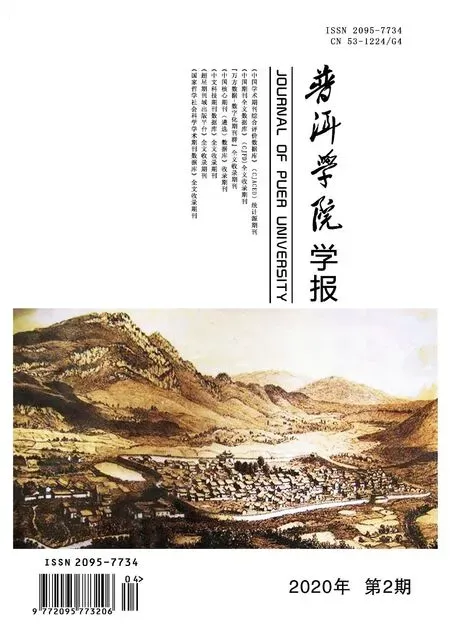《史記》中語言藝術研究
申前程
山西旅游職業學院,山西 太原 030031
司馬遷的《史記》語言風格多變,多以“悲壯”“雄奇”著稱。縱觀《史記》發現司馬遷語言亦有辛辣戲謔、詼諧揶揄之處,且絕非偶涉戲筆,幽默戲謔的語言特征與“悲壯”“雄奇”的語言風格形成對比,構筑了《史記》獨特的語言風景線。根據《史記》創作語言特征、特點及風格,可將《史記》劃分為敘述語言與人物語言兩類,且由于《史記》的體裁限制使敘述語言所占比例較大。人物語言也在整部《史記》中發揮著不小的作用,可以突出角色性格,呈現作品主題,展現不同時期的政治、文化、經濟特色。
一、《史記》的直敘與婉敘特征
在《史記》語言藝術范疇內可將敘述語言劃分為直敘與婉敘兩種,直敘能夠對記敘事件、人物并給予明確的闡釋,而婉敘對所敘述的事件、人物給予委婉的暗示。雖然婉敘比直敘隱晦、間接,卻能夠將事件與人物的整體畫面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使讀者結合自身的經歷感受歷史人物的性格、思想及道德觀念。而在《史記》諸篇中,直筆和曲筆、直敘和婉敘相映成趣、相互呼應又相互融合,于是讀者在誦讀《史記》時便能由宏觀到微觀、由表層到深層地洞察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明確歷史發展規律。
首先,微詞顯意。在《屈原列傳》中司馬遷稱贊《離騷》“其行廉、其志潔、其辭微、其文約”,文雖小,而境極廣,舉類窄,卻見義深。而在語言風格與手法上,司馬遷沿襲了《離騷》的創作傳統,通過微婉詞匯寄托精神旨意。譬如攝漢王手附耳語封韓信為王,卻又誣害韓信變心。司馬遷能夠通過對張良柔弱外表的描述,揭示其殘忍奸詐、深于城府的性格特征。如在《留侯世家》中,作者通過細節描寫,將張良憎惡輕蔑的心理動態委婉地展現出來,若不深讀將很難體味得到。
其次,意在言外。隱匿本意,豐富內涵。在這種筆法作用下,讀者是很難靠字面含義推理出作者本意的。譬如在《衛將軍列傳》中,作者重點介紹了名將衛青,開篇寫道:“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司馬遷并未露一字,卻將衛青憑借裙帶關系得寵的事實表達出來。
再次,旁敲側擊。旁敲側擊主要指通過寫人物周邊的人及事點明二者的關系,使人物的形象躍然紙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司馬遷深諳此道,故借社會關系、社交群體的層次關系,將歷史人物的階級、地位及特點呈現出來。譬如在《平津侯列傳》中,司馬遷寫公孫侯“外寬內深,為人意忌”。而在刻畫漢武帝陰險狡詐時,司馬遷并沒有直接描述漢武帝的內心陰險,而是從偶遇孫弘的事件中進行呈現。
最后,借物言志。司馬遷很少將自身的見解及想法直接寫出來,而是通過人物之口來表現。在特殊的語境中,司馬遷以褒代貶、以貶代褒,正話反說、詞正意反,通過詞匯的靈活運用營造出辛辣諷刺的語言風格。譬如在《蕭相世家》中,司馬遷寫道:“辣布、海印皆誅滅,何之爛勛爾。”表面上司馬遷是在夸贊蕭何功勛赫赫,但潛臺詞卻說蕭何世故奸滑。
二、《史記》的語言形式
首先,《史記》在傳記記敘中通常采用交替、插入、連貫等表達形式。其中連貫指根據歷史人物的生平經歷、事件的起因經過來記敘。常用的連詞主要有“于是”“久之”“及”“頃之”等。譬如“然則何由?”與“請入圖之”。又如“居有間,將得罪于嬴政,亡之燕”。而插入主要指在事件與人物敘述的過程中插入另一事件、另一人物或另一評議。若在事件敘述中插入事件“發展后期”的敘述文字,則稱之為倒敘,在事件或人物敘述中插入其它事件或人物,則稱之為插敘。在敘述人物和事件時補充事件發展階段的細節信息,則稱之為補敘。比如在《武安侯》列傳中,司馬遷在敘述竇嬰經歷與家世中,插敘了梁孝王的信息,隨后又直接回到敘述主線上。美國語言學家康樂特在相關著作中指出,“插敘、閃回”嚴重隔斷了事件的敘述流程,影響了作品的流暢度,然而在信息呈現與主題理解上,卻擁有難以替代的作用。所以,《史記》較少應用“插入”手法,有其特殊的道理。
其次,在連貫層面。連貫主要指根據時間順序、空間順序及邏輯順序記敘事件和人物。該筆法占比最高,也是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常用手法。然而在語言表現與主旨呈現上,連貫與其他古代文學作品并無差異,故此,不再累述。在“交替”層面,“交替”主要指敘述、抒情、評議、說明的相互交替,使事件、人物的敘述,更顯緊湊、連貫,更具有層次性、邏輯性、紋理性。譬如在《衛將軍列傳》中,司馬遷寫道“其明年,匈奴入定襄、北平,殺漢千馀人。”此處,司馬遷便將評議與敘述相融合、使兩者根據特定的邏輯順序,呈現在讀者面前,使讀者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創作主旨。
其三,在連貫、插入、交替等語言表達形式上,司馬遷注重關聯詞的應用,從而使敘事有頭有尾。連貫自然。與此同時,也使“交替”“插入”意斷形聯,視角轉換更加靈活自然。然而司馬遷在使用關聯詞的同時,也采用形異意近的“變通”詞,譬如用“于”代替“乃”,用“初”代替“其先”。用“當是時”代替“當是之時”等。又譬如“其先,楚地皆降漢”與“初,劉溫嘗息大澤……”等。在句式層面,司馬遷善用春秋筆法,即“一字含褒貶”,一詞窺“全身”,微言大義者也。在句式結構中,司馬遷所用字詞較短,較少、語言精悍,能夠在極短的文字中呈現出所有的思想內涵及歷史文化。
三、《史記》的語言風格
首先,似褒實貶,反語譏諷。反話正說是司馬遷應用婉敘筆法的重要方式,能夠對所要批判的人物進行嘲諷,使人物的歷史形象更加鮮明。如對陰奉陽違之徒傅靳,司馬遷在《傅靳列傳》中是這樣寫道的:“舟不見貶、操心堅正,篤厚君子,此傷心者然。”司馬遷對傅靳極為不滿但不直言揭示,而是先表其“操心堅正”再用“篤厚君子”來暗諷,語言辛辣詼諧,但表面卻嚴肅克己,貌似正經的“人物評述”。可見,正話反說是司馬遷詼諧文風的重要特征,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過司馬遷:“司馬遷的諷與刺,大過于傳統的文章,曲折中蘊有直白,褒貶中蘊含深意”。
其次,歸其荒謬而達曲諷。作者通常能夠抓住人物的荒謬細節引申發展,將其荒謬之處烘托得鮮明徹底,進而達到幽默詼諧的語言效果。譬如在《滑稽列傳》里,優孟為勸楚莊王埋葬寶馬,便用了“以大夫之禮埋之,淡,以君子禮葬之,優!”的荒謬說詞。這充分地凸顯楚莊王的昏庸與荒謬,提升了文章的詼諧氛圍。
再次,風趁典永,引用謠診。司馬遷的《史記》汲取了形成于民間的民歌、俗語、諺語,使得整體風格幽默繽紛、風趣雋永。譬如“生女無怒、生男無喜”,便是用了風趣委婉的語言諷刺了隋朝的外戚干政現象。“黃金百斤,何如季布一諾”則是用俏皮輕松的民謠,突出“承諾”的“不易”與“榮耀”,繼而使文章平添幾絲風趣。并且在俗語、諺語、民歌的應用下,整部作品的風格更加多樣、形式更加多變,不僅“高大上”并且“接地氣”。
最后,修辭手法的應用。在《項羽本紀》中“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巧妙地應用了排比、比喻等修辭手法,將平庸的對話語言生動地展示出來,并使角色語言與敘事語言形成對比,增強角色的感染力,使語言更富有性格特征。而根據古代語言的應用特征及表現手法,短句與長句、動詞與形容詞的有效應用,能夠鮮明地表現出角色的性格特征及特點,使人物的內心情感躍然紙上。
四、結語
司馬遷的《史記》擁有較強的審美價值、文學價值及歷史價值,能將中華歷史文化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通過紀傳體的形式提升作品的通俗性與文學性。通過分析《史記》的語言特征、語言形式及語言風格,明確《史記》在語言應用層面的成功之處,確定了《史記》語言藝術的睿智之處,進而在分析語言藝術的過程中,人們感受到司馬遷豐富的文學素養、深厚的文化底蘊及精湛的史書撰寫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