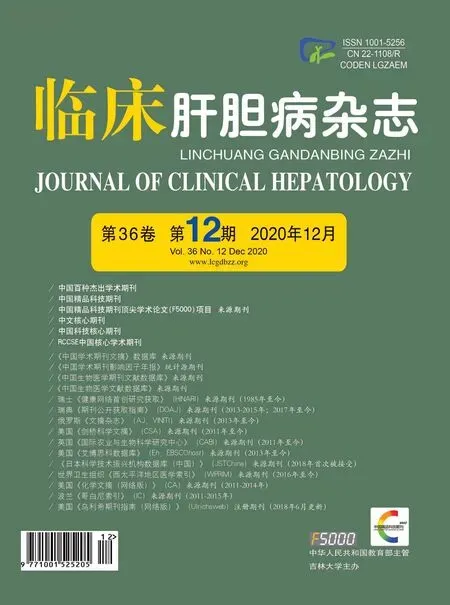酒精性肝病發病機制研究現狀
吳 亞, 李艷茹, 楊寄鐲, 殷建忠,2, 馮月梅
1 昆明醫科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昆明 650500; 2 保山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 云南 保山 678000
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是慢性肝損傷的主要病因之一,該病的發展經歷了多個進行性階段。最初表現為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長期大量飲酒病情會逐步進展為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肝纖維化、肝硬化,最終有可能發展為肝癌而死亡。2010年,全球約有8萬人死于酒精性肝癌,其中50%發生在中國[1]。2000年我國ALD患病率為2.27%,隨著我國嗜酒人群的不斷擴大,2015年上升至8.74%[2]。酒精引起的輕度肝損傷可以通過長期戒酒來逆轉,但當病情進展至ALD終末期時,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法是肝移植,但該方法存在供體缺乏、免疫排斥以及手術費用昂貴等缺點。因此,ALD已經成為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目前ALD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本文將從氧化應激導致的肝損傷、腸源性內毒素血癥、遺傳變異等方面簡要介紹近幾年國內外對ALD發病機制研究的相關進展。
1 氧化應激
在生物系統內,自由基包括氧自由基和氮自由基兩類,其中氧自由基和次氯酸、臭氧等非自由基被稱為活性氧(ROS)。ROS能夠氧化生物膜和組織中的幾乎所有分子,引起DNA鏈斷裂,造成損傷。但在正常生理情況下,人體內存在膽紅素、泛醌、谷胱甘肽還原酶/氧化酶等一系列酶促和非酶促的抗氧化物質。這些抗氧化物質的存在使ROS在生物體內不會損害機體(圖1)[3]。但在長期酗酒的情況下,ROS生成增加,抗氧化劑的水平或活性會下降[4]。當ROS生成量超過抗氧化系統清除ROS的限度時,ROS在體內水平上升,引起氧化應激。肝臟中實質細胞和非實質細胞都可能參與ROS的生成,但主要以肝細胞為主[5]。肝細胞內ROS主要通過3個途徑產生:線粒體呼吸鏈、細胞色素P450 2E1、NAD(P)H氧化酶[6]。乙醇被乙醇脫氫酶氧化為乙醛時會產生ROS和NADH。NADH會干擾線粒體的電子傳遞系統,促進ROS的生成[7]。乙醛會引起線粒體損傷,這也可能導致氧的單電子還原為超氧化物。另外,在微粒體內氧化乙醇的過程中,細胞色素P450利用NADPH還原O2時也會產生ROS[8]。酒精還會引起肝細胞中NAD(P)H氧化酶的活化,導致超氧物的生成增加[9]。此外,有研究[10]發現酒精依賴者肝臟中鐵濃度增加,而鐵可以催化反應較少的氧化劑如超氧化物轉化為更強的氧化劑如羥自由基。
酒精引起ROS增加并氧化脂質、蛋白質和DNA已經在各種系統、細胞和物種中得到證實。1966年Di Luzio[11]首次觀察到長期飲酒會引起脂質過氧化現象,這是在多不飽和脂肪酸中去除電子后脂質自由基形成的反應。細胞脂質過氧化產生的親電性物質會修飾細胞內蛋白質,導致蛋白質功能喪失并破壞細胞內環境的穩定。ROS對蛋白質的攻擊主要是通過二硫鍵形成和谷胱甘肽化、亞硝基化、羰基化等途徑來調節蛋白質的活性。此外,ROS增加會導致線粒體羰基水平增加,從而進一步導致氧化蛋白的積累[12]。ROS對細胞核和線粒體DNA造成的氧化損傷均會導致編碼蛋白質的變化,這可能造成編碼蛋白質的功能失調或完全失活。
2 腸道微生物
腸道是體內最大的微生物庫。人類的胃腸道腔包括病毒、酵母、真菌、細菌等數以萬億計的微生物,它們攜帶著300多萬個獨特的基因[13]。在正常的生理條件下,腸道菌群的組成和數量處于穩定狀態。酒精攝入后穩定狀態會被破壞,這種情況稱為菌群失調。在酒精喂養3周的小鼠體內表現為革蘭陽性菌減少,革蘭陰性菌和疣微菌門的豐度增加[14]。而Bj?rkhaug等[15]研究指出,長期過量飲酒者腸道中變形菌門、梭菌門、厚壁菌門增加。酗酒者和肝硬化患者體內存在富含變形菌門和厚壁菌門的細菌群落,其過度生長的程度與肝損傷的嚴重程度相關[16]。酒精不僅會導致菌群失調,還會影響腸道屏障。腸道屏障是由腸黏膜上皮細胞通過緊密連接、黏附連接和橋粒形成的可選擇性滲透的物理屏障,而且由于黏液的存在,腸道屏障還具有免疫特性。酒精及其代謝物通過影響黏液層和緊密連接蛋白的表達,對腸屏障完整性產生直接的損害作用,進而增加腸道通透性。此外,酗酒后的一些微生物代謝物如丁酸鹽、乙酸鹽和丙酸鹽發生改變后也會影響腸道屏障的完整性[17]。腸通透性增加有助于具有活性的致病菌、革蘭陰性菌產物脂多糖(LPS)和腸內具有促炎癥作用的代謝物進入血液循環。當這些致病抗原通過門靜脈到達肝臟時,它們能夠激活炎癥反應。其中LPS、革蘭陽性菌組成部分肽聚糖和β-葡聚糖分別與Toll樣受體4/CD14復合物、Toll樣受體2和C型凝集素樣受體結合,通過NF-κB和IL-6/STAT3信號通路介導Kupffer細胞和外周血單個核細胞的活化[18-20]。活化的單個核細胞和Kupffer細胞會釋放大量促炎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在肝細胞已經受損的情況下,這些細胞因子會進一步加重肝臟炎癥和氧化應激,導致肝損傷惡化,同時促進肝星狀細胞的激活,參與肝纖維化過程。
3 遺傳變異
有報道[21]稱,95%以上的慢性酗酒者患有酒精性脂肪肝,然而,只有大約30%的患者發展為更嚴重階段,其潛在的保護機制尚不清楚。不同人群攝入不同數量的酒精或個體間基因的表達差異可能導致疾病進展的不同。有研究[22]發現,ADH1B*3等位基因在非洲裔人群中幾乎是唯一的,該等位基因具有更快速的乙醇消除能力,可以保護接觸酒精的胎兒,并可能使飲用相同數量酒精的青少年患ALD的可能性降低。ALDH2*2等位基因引起雙硫侖樣反應,在亞洲人群中普遍存在。可能由于該反應,攜帶這種顯性等位基因的個體更不易患ALD[23]。美國的一項研究[24]發現,PNPLA3基因的單核苷酸rs738409多態性與ALD的發生密切相關。此外,單核苷酸rs738409多態性與漢族男性ALD的發生也密切相關[25]。在晚期肝病患者中,PNPLA3 I148M變異會導致ALD發展為肝癌的風險增加[26]。
4 自噬在ALD中的作用
自噬是一個進化保守的細胞內分解代謝過程,對細胞的發育、分化、穩態和生存至關重要。乙醇對自噬的影響很復雜,急性和慢性酒精暴露可能對肝臟自噬具有不同的調節作用。急性酒精暴露激活自噬,對肝細胞起到保護作用。Ding等[27]研究發現,原代培養的肝細胞和肝細胞系經乙醇處理(20~80 md/L,持續6~24 h)后,自噬小體和自噬通量增加,提示急性酒精暴露下細胞自噬被激活。但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自噬如何防止酒精引起肝損傷,可能涉及受損線粒體和脂質的選擇性降解。線粒體在酒精代謝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極易受到損傷。
線粒體自噬是自噬的一種特殊形式,即通過自噬選擇性去除受損的線粒體。在酒精性肝損傷和脂肪變性的過程中線粒體自噬對肝細胞起到保護作用。受損線粒體被去除后可以維持健康的線粒體,從而減少氧化應激,保持呼吸鏈功能和線粒體能量生成,進而防止細胞死亡。線粒體自噬還通過維持具有β-氧化能力的線粒體來防止脂質在肝臟中積累(圖2)[28]。
脂滴的內容物被自噬體轉運至溶酶體,溶酶體利用酸性脂肪酶降解脂質的過程被稱為脂噬。在體內和體外均觀察到酒精誘導的GFP-LC3陽性自噬體特異性包裹脂滴。在ALD動物模型中,使用雷帕霉素激活自噬降低了甘油三酯水平,而氯喹抑制自噬使肝臟甘油三酯水平升高[29-30]。Mallory小體(Mallory-Denk bodies,MDBs)是肝細胞內的胞質透明包涵體,其主要成分包括角蛋白8、角蛋白18、泛素和p62。乙醇和脂質代謝釋放的ROS會影響許多細胞內蛋白,形成MDBs,這可能對肝臟結構和功能造成潛在的損害。雖然MDBs的形成機制不完全清楚,但是有證據[31]表明,自噬參與了MDBs的消除。
隨著飲酒時間的延長,酒精可能抑制自噬。有研究[32]發現,用乙醇喂養小鼠10 d后,肝臟內自噬小泡增加,自噬通量下降。Chao等[33]研究也發現了自噬通量受損的情況,他們認為這是自噬不足,即慢性乙醇損害肝臟轉錄因子EB,使溶酶體數量下降,最終導致自噬小體積累。慢性暴露時雖然酒精能誘導自噬,但由于溶酶體損害,自噬活性最終也會受到損害。有研究[34-35]報道,慢性乙醇暴露可能通過滅活RAB7和降低動力蛋白2活性來抑制肝細胞的脂噬;也可能通過抑制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的活性來抑制自噬。自噬抑制會阻止過多的脂滴、受損線粒體和有毒蛋白聚集物的清除,這些物質可在各種肝臟疾病的發展過程中產生,從而導致脂肪變性、損傷、脂肪性肝炎、纖維化和腫瘤的發生。
5 microRNA(miRNA)
miRNA在肝臟中含量豐富,參與調節多種與肝損傷相關的過程,如炎癥、凋亡、肝細胞再生等,miRNA的異常表達可能是許多肝臟疾病的關鍵致病因素。有研究[36]發現在酒精暴露下miRNA-21、miRNA-34a、miRNA-155、miRNA-320和miRNA-200a的表達上調,而miRNA-122、miRNA-181a、miRNA-199a的表達下調。
miRNA-155缺乏可減輕慢性酒精誘導的脂肪變性、肝損傷和氧化應激。Bala等[37]發現慢性酒精喂養的野生型小鼠中炎性單核細胞的數量和巨噬細胞的比例增加,而miRNA-155敲除小鼠的炎性單核細胞數量下降,但未發現巨噬細胞比例增加。進一步研究發現,酒精喂養導致野生型小鼠肝臟被中性粒細胞浸潤,而酒精喂養后的miRNA-155敲除小鼠中性粒細胞浸潤被阻止。
miRNA-122占成熟肝細胞中所有miRNAs的70%,在其他細胞和組織中幾乎沒有表達。肝特異性缺失miRNA-122的小鼠在出生時表現為脂肪變性,然后逐漸進展為纖維化和肝癌。在酒精性肝硬化患者和酒精喂養小鼠的肝臟中發現miRNA-122的表達顯著降低[38]。在肝細胞中,miRNA-122直接或間接地調控參與脂質合成、輸出以及膽固醇穩態的復雜基因網絡。肝細胞miRNA-122過表達可減輕酒精引起的血清ALT和肝臟甘油三酯水平升高。此外,用pri-miRNA-122處理酒精喂養的小鼠,會使小鼠的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和IL-1β的水平下降[38]。
Li等[39]發現,與健康對照組相比,酗酒者血清miRNA-223水平升高。在慢性酒精喂養加急性酒精灌胃的小鼠模型中發現,血清和中心粒細胞中miRNA-223水平均升高。此外,miRNA-223基因缺失引起肝臟IL-6的表達上調并加重乙醇誘導的肝損傷、中性粒細胞浸潤和ROS。Wang等[40]則發現在人類酗酒者中血清miRNA-223水平升高,而中性粒細胞miRNA-223水平下降。這些差異背后的確切機制尚不清楚,但可能是由于接觸酒精的時間不同。酗酒模型小鼠中性粒細胞miRNA-223的增加可能反映了適應性反應,而人類酗酒者可能由于長期接觸酒精而損害了適應性反應。
在小鼠和AML-12細胞中均發現酒精上調miRNA-200a的表達。miRNA-200a的過表達改變了包括BAX、BCL-2在內的標志性凋亡蛋白的蛋白水平,而miRNA-200a抑制劑則產生了相反的效果。此外,miRNA-200a的高表達增加了AML-12細胞的凋亡率,相反,miRNA-200a抑制劑轉染的AML-12細胞凋亡率降低[41]。總之,這些發現表明miRNA-200a可調節ALD肝細胞的凋亡。
6 其他
酒精進入人體后主要在肝臟中代謝并產生大量乙醛,乙醛會上調甾醇調節元件結合轉錄因子1c促進脂肪酸的合成,同時乙醛抑制DNA結合能力和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α的轉錄活性來抑制脂肪酸氧化,最終導致脂肪酸在肝細胞內積累[42]。酒精性肝毒性和酒精代謝引起的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會導致線粒體依賴性細胞凋亡,加速ALD的進展。肝細胞內積累的ROS會抑制AKT磷酸化,從而抑制GSK3β/Wnt/β-Catenin信號通路的激活,下調G1期細胞周期蛋白D1,進而阻滯細胞周期并激活線粒體依賴性凋亡[43]。 ROS還能直接激活凋亡信號調節激酶1,活化NF-κB和JNK/P38從而誘導線粒體依賴性凋亡[44]。此外,性別和既有疾病是ALD進展的危險因素。有研究[45]發現女性酗酒者比男性酗酒者患ALD的風險更高,可能原因是女性體內總含水量和胃內酒精代謝能力較男性低。
ALD病因明確,但其發病機制十分復雜,多種因素可能參與ALD的發生發展。雖然對ALD發病機制的認識有了長足的進展,但是還有很多問題有待明確及進一步研究,比如哪些基因的變異使人群更易受到酒精的損傷、酒精損害自噬的機制、各種miRNAs如何參與調控ALD的發生發展、MDBs通過什么途徑造成肝損傷等。對ALD發病機制的進一步研究將有助于做好ALD的防治工作。
作者貢獻聲明:吳亞是綜述的主要撰寫人,完成相關文獻資料的收集、分析及初稿的寫作;李艷茹、楊寄鐲參與文獻資料的分析、整理;馮月梅負責指導論文寫作及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