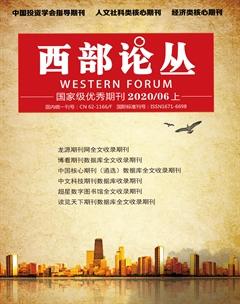從“文本”到“觀念”:中國古代傳播觀念史研究方法思考
摘 要:本文認為,華夏傳播研究領域提出的“釋義系統(tǒng)”研究方法強調了在中國古代傳播觀念史研究中文本的重要性,并暗示了一種重要的,理解“文本”與“觀念”之關系的進路。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在如何從“文本”走向“觀念”上應當充分釋放想象力,并介紹了西方“語境主義觀念史”的“言語行動”面向在這一問題上的貢獻。
關鍵詞:中國古代傳播觀念史;華夏傳播;文本;傳播;觀念史
一、對華夏傳播“釋義系統(tǒng)”研究方法的思考
近年來,如何進行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的問題已經引發(fā)了傳播學學者們的不少討論。而在如何利用傳統(tǒng)歷史資源來進行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的路徑上,“華夏傳播研究”以利用歷史與傳統(tǒng)資源為特色,形成了其獨特的研究風格。其中,一些學者將目光投向了對中國古代傳播觀念的研究。本文希望在該領域既有方法的基礎上展開進一步的探索。
在“華夏傳播研究”領域中進行的中國古代傳播觀念研究是以“華夏傳播研究”本身的一套宗旨和學術追求為內核展開的。“華夏傳播研究”,總的來說,是以歷史和傳統(tǒng)思想為起點的本土化傳播研究類型,其旨在從歷史和傳統(tǒng)思想中發(fā)展出中華傳播學理論,實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這種“轉化”主張將歷史觀念轉化為“釋義系統(tǒng)”,從而“用過去的事物來理解現(xiàn)在的事物”。
從這一思路出發(fā),邵、姚兩位學者撰寫了《傳播理論的胚胎——華夏傳播十大觀念》一文,總結出了“陰 - 陽”、“言 - 行”等十對傳播觀念,作為解讀中國人“賴以行動的‘釋義系統(tǒng)”。所謂“釋義系統(tǒng)”大致有兩個含義,一方面,它涉及利用“一種‘隱喻的方式,即用現(xiàn)在的事物理解現(xiàn)在的事物”,這種“理解”側重于詮釋;另一方面,二位學者強調“釋義系統(tǒng)”在“指導人們行為與行動”方面的作用。總的來說,它是由過去的觀念編織而成的“意義之網”。
以二位學者對在論及“陰 - 陽”這對觀念時對《易經》這一歷史文本的使用為例,他們認為《易經》可以用來詮釋“人類傳播是相互聯(lián)系的”這一觀念,同時也強調《易經》的智慧在人際交往方面的啟示和引導作用。他們對《易經》本文的使用與他們對“釋義系統(tǒng)”的闡述是可以互相參證的。
“釋義系統(tǒng)”的提出為我們如何進入中國古代傳播觀念史的研究指出了十分有用的方向,這主要體現(xiàn)在,它體現(xiàn)了“文本”作為核心研究材料的重要性,并強調了文本的“隱喻”和“意義”這兩種影響人們文化實踐的重要方式,這對于我們研究傳播觀念是如何影響歷史上人們的傳播實踐這一問題來說,是十分具有啟示意義的。
沿著這一思路,我們會發(fā)現(xiàn),當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傳播觀念史時,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可避免地碰上“我們應當如何遭遇文本”的問題。這一問題主要是由我們研究歷史時,文本材料在所有可用的材料中占主要比重的客觀事實導致的。但是如何處理這一問題,卻隱藏著我們如何對文本進行定位和解構的問題。是以如何遭遇文本的問題,反映的是我們在進行中國古代傳播觀念史研究時的種種預設,影響的是我們如何、在多大的、什么領域的學術地圖中去對中國古代傳播觀念問題展開想象。而這種想象力,對于如今的中國傳播觀念史研究來說,應當是非常需要的。
二、“語境主義”:從“文本”到“觀念”
筆者認為,對于中國古代傳播觀念史研究而言,將“如何處理文本”作為問題的一個關鍵是意識到“文本”和“觀念”之間的距離,即“觀念”并不就等于“文本”。從“釋義系統(tǒng)”出發(fā),從對文本內部的意義解釋出發(fā)去“析出”中國古代的傳播觀念當然是可行的而且是有必要的。但是對于“文本”和“觀念”之間的關系,畢竟還有更多樣的可能,因為,相較于“文本”而言,“觀念”事實上更具有一種“人的行動”的傾向和屬性,如果采取這個視角進行研究,那么,“文本”對“觀念”的影響可能要變得相對間接很多,與其說前者對后者是直接的映射關系,不如說,“文本”更像是具備某種“觀念”的人在采取行動時所采用的一種媒介。
將“文本”視為一種媒介,就是將它視為僅僅是歷史行動者部分思想行動的承載者、呈現(xiàn)者,認為它無法代替這些思想和行動本身。在這種分析框架里,占據更顯要位置的就不是“文本”本身,而是所謂的“文本行動”。事實上,這一觀點在西方的觀念史研究中已經得到了一定的闡述。
在“劍橋學派”提出的“語境主義觀念史”研究中,其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納就主張:“文本即行動(texts are acts),因此,與其他一切自發(fā)行動一樣,理解過程要求我們復原文本作者行動所體現(xiàn)的意圖。但這并非陳舊的解釋學試圖使我們相信的那種神秘兮兮的移情過程。因為行動就是文本:我們能夠解讀它所體現(xiàn)的主體間性意涵。(intersubjective meanings)……任何復雜文本,其中都包含了大量的以言行事行動。”
具體來說,這一方法的目標就是“將文本視為對特定話語的貢獻,進而發(fā)現(xiàn)它們是如何延續(xù)、挑戰(zhàn)或者顛覆那些話語本身的傳統(tǒng)語匯的。總體上說,這里的目標在于將我們所研究的文本還原到其當初賴以形成的具體的文化語境當中。”
而“為了理解一個文本,我們至少必須理解考察對象的意圖,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意欲的溝通行動(intended act of communication)。這樣,我們在研究這些文本時需要面對的問題在于:這些文本的作者身處特定的時代,面對特定的讀者群,他們通過自己的言論實際是要傳達什么。因此,在我看來,最好從一開始就對通常在特定時刻的特定言論的傳達對象予以說明。接下來第二步應當是考察特定言論與更為廣泛的語境(linguistic context)之間的關系,以揭示特定作者的意圖。”
這即是說,我們應當將重心從文本本身轉移到歷史行動者對文本的“使用”上來,按照斯金納的說法,即“我們不應該研究文本的意義(the meanings of the words),而是應該研究對它們的使用(use)”。概括而言,“劍橋學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重點考察歷史上的人們如何通過文本來實現(xiàn)他們的行動,因此,該學派的研究方法不強調對文本意義的主觀解讀,而主張考察文本形成時的文化語境,這包括作者所處的歷史時代、他通過他的言論實際想要傳達什么、他希望通過對文本的使用達到什么意圖,他向誰寫作等。
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回應,研究者將獲得對于特定文本在思想史上的特定地位的理解和把握,而不僅僅是對文本內容的主觀判斷。這固然有助于提升我們研究結果的“客觀性”,但更重要的是,這種“文化語境”展現(xiàn)出的是一條縱向的深沉的文化脈絡,它能勾畫出所研究的觀念背后的活生生的歷史文化圖景。對于中國古代傳播觀念史研究來說,能夠“以小見大”,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傳播觀念背后的連續(xù)的、縱深的文化脈絡,將是一件有利于我們形成對于中國古代傳播觀念整體認識,進而對“華夏傳播學”的發(fā)展也是意義深遠的事情。
參考文獻
[1] 邵培仁,姚錦云.為歷史辯護:華夏傳播研究的知識邏輯[J].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6(03):140-151.
[2] 邵培仁,姚錦云.傳播理論的胚胎:華夏傳播十大觀念[J].浙江學刊,2016(01):203-215.
[3] Quentin Skinner, Version of politics, vol. Ⅰ,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2002,pp.57-89.
[4] 同上
[5]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History of Ideas . 1969.
[6] 同上。
作者簡介,潘彥伶(1993-)性別:女,籍貫:湖北宜昌,學歷: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傳播觀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