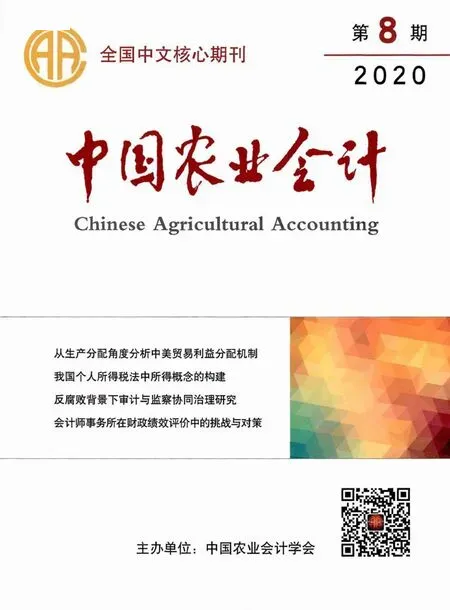我國個人所得稅法中所得概念的構建
屈鈺瀟
個人所得稅作為針對我國個人納稅人的直接稅種,其變革總是引起極大關注。自1984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或法律授權國務院及其他行政部門制定了多部《暫行條例》,其中一部分沿用至今。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國家征收個人所得稅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充,但我國未在法律層面對個人所得稅中“所得”的概念進行界定,同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對于“所得”內涵的激烈討論不同,我國的稅收法律似乎尚未加強對“所得”界定問題的重視。但是“所得”概念的模糊已經給個人所得稅的法律公信力和稅收制度的執行力帶來困擾。
一、“所得”概念授權立法帶來的困境
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前,我國行政部門在稅收立法中的地位一直無可動搖,并且截至2019年5月,全國人大頒布的八部稅收立法中有五部都不同程度上授權給國務院或者其他相關行政機關制定條文或者實施細則的權力,例如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實施條例》就是國務院根據新施行的《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個稅法”)制定的實施細則。
誠然,從社會效率和稅收法律制定的現實困境來看,稅收相關規定的全然法定必然導致稅收立法的嚴重漏洞,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和社會、市場管理機制運行。一直以來,國務院等相關行政機關在我國稅收立法的道路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奠基作用,本文認可行政機關制定相關實施細則的必要性和一定范圍內授權的合理性。所得認定規則體系的完善,不得不依賴于財稅部門體現在稅收規范性文件中的自由裁量權,期待后者秉持平等課稅的理念,彌補法律的不足。這是面對社會生活的高速發展與稅法的滯后沖突時,為實現稅法的普遍適用而不得已的次優選擇。
但是,根據我國已經出現了國務院等相關部門對法律進行實質上的任意擴張解釋而導致《個人所得稅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個稅實施條例”)之中的征稅范圍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從而引起國民對于稅收部門征管行為的合法、合理性的質疑。國務院及相關行政機關并不具有解釋法律的資格,但是目前實際存在國務院及相關行政機關通過制定相關實施條例的方式行解釋稅收法律之實的情形,且在稅收法律部門中該現象尤為普遍。
以2019年6月25日財政部官網發布的財政部、稅務總局公告2019年第74號《關于個人取得有關收入適用個人所得稅應稅所得項目的公告》(以下簡稱“74號公告”)為例,該公告將“個人為單位或他人提供擔保獲得報酬”等轉入“偶然所得”項目征收個人所得稅,將“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養老金收入”計入“工資、薪金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引起了國內納稅人和學界對其是否符合稅收法定原則、順應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的質疑。其中的一些條款更是通過解釋公民獲取所得的行為將納稅人收入納入個人所得稅類目的征稅范圍,明顯超出了國民預測可能性。
雖然根據個稅法相關內容“國務院根據本法制定實施條例”,即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國務院只能對稅收征收的執行規定制定條例,但是根據2019年個稅實施條例中第6條所述:“個人取得的所得,難以界定應納稅所得項目的,由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確定。”這實際上是國務院賦予自身隨意改變個稅課稅對象的權力。實踐中已經發生的法律適用問題顯示,該行政權力的擴張,不僅會影響到稅收法律的穩定性和公信力,降低公民對稅收預期的信賴,同時也不免影響到法律的中立性,產生法律部門利益化的風險。
二、刪去“其他所得”類目的影響
本文認為,我國對于“所得”的概念未被統一界定導致了上文的困境。實踐中,稅收征管機關掌握了將個人的所得歸類的重要過程,所以對于“所得”這一概念的界定就變得尤為重要。即當國民和稅收立法中對于“所得”的界定有著統一的認知和認同,法律的確定性和稅收立法在實施中的正當性才能得到保證。下文以“其他所得”類目的刪去為例,從稅收機關行為正當性的兩個角度闡述“所得”概念未被界定的影響。
從稅務機關職權不斷擴大、侵害納稅人權利的角度來說,2018年個稅法對原本“其他所得”項目下的十類收入重新分類。“其他所得”作為兜底性條款從稅收法律中刪去,使得國務院及相關行政部門不可避免地將進一步擴大對于稅收法律的類推解釋適用。并且我國在“所得”類目定義的缺失,致使雖然在社會樸實的認知中其存在大致的范圍,但是清晰的理論及法律條文上的界定尚未形成,導致實踐當中產生了稅務部門與國民認知之間的偏差。其中,在我國所得稅法中長期存在的其他所得類目就展示了這方面的問題。其他所得從1995年起陸續添加了十個項目。其中包括“企業在年會、座談會、慶典以及其他活動中向本單位以外的個人贈送禮品,對個人取得的禮品所得”、“個人為單位或他人提供擔保獲得報酬”等。
目前實行的個稅實施條例當中,2018年個稅法刪去“其他所得”的類目,意味著本包含于“其他所得”項目下的十類收入將重新分類。稅務總局將對個人所得的界定做出重大調整。“偶然所得”成為了國務院欲對個人收入實行普遍征收的新“口袋”。在之前相關文件中存在的對于“偶然所得”的界定中,其表述是“個人得獎、中獎、中彩及其他偶然性質的所得”。雖然定義當中存在“其他”這樣可以填塞概念的字眼,但是對于先前表述中“偶然”兩字重點在于該所得和勞動、經營、資產無關且具有“偶然”的特征。故該概念中包含的“其他偶然性質的所得”實際不應當包括74號公告中所歸類的內容,該公告的內容明顯超出了納稅人的期待可能性,有侵害納稅人權利的嫌疑。
從稅收機關行為獲取正當性的角度來看,所得稅法的深刻痛感決定了對于所得的定義應當更加明晰,否則政府頒布的任何分類行為而非決定稅收基礎規范的內容都會遭到詬病。雖然國務院及其授權機關已經不可以直接規定實際上的稅收法律,但是其具有可以頒布相關規章或者行政法規的能力,通過規制分類行為直接導致稅收法律對某一行為生效或者不生效,實際上是對稅收法律中的征收對象做出了改變或者擴大。例如,74號公告中將個人為他人提供擔保獲得的所得定義為偶然所得征稅的規定,就展露了行政機關對于所得概念定義的權力的擴張,損害了稅收機關行為正當性。
從上文不難看出,對于個人來說,該收入是否可以被判定為所得是至關重要的,只有該收入符合“所得”在我國稅收法律上的定義,才能將其進一步分類。所以,對個人所得稅中“所得”定義的厘清,必能為稅收法律的有效執行和國民的心理預期及確定性,甚至限制行政權力的過度擴張以及促進稅收法定的改革方向增添重大助力。
三、借鑒外國稅法實踐探尋我國稅改發展方向
在探討我國個人所得稅中對于“所得”的定義之前,本文欲根據其他國家中所存在的對于“所得”的內涵進行分析,闡述這些概念對于我國“所得”定義的借鑒意義。1799年英國開始征收個人所得稅,此后美國、韓國等國家紛紛開始征收個人所得稅,目前個人所得稅已經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重要財稅收入來源。但是由于對于所得基本概念的理解不同,不同國家的稅制設計存在很大差別。
其中對于所得的范圍的理解主要包括三種:一是增值類,屬于廣義的所得概念,來源于德國經濟學者Schanz的純資產增加說,該學說認為所得等于供消費用之財產的市場價值加上兩個時點間財產價值的變動。其中消費支出,不單指納稅人現實上為個人及其家庭所作之金錢給付而已,也包含自我提供勞務與使用自有財產(即因此而得到利益或滿足感,節省了本應負擔費用的支出),因此而節省下來的金錢給付在內,即學說上所稱之隱含所得、設算所得或自我消費所得,且對于該種所得的定義不論主觀意圖,也不論來源。二是源泉類,來源于德國經濟學者的源泉理論,認為所得應當是通過經營行為得到的,有固定來源和周期的現有資產孳息,其中屬財產本身的價值變動不屬于所得。三是市場所得理論,該理論是主要來自于法律人的角度的定義,該定義的核心為納稅人是否藉著利用稅法規定之營業基礎而取得盈余,而非關注納稅人主觀上是否有盈利的意圖。
其中德國1891年6月24日頒布的普魯士所得稅法中采用了源泉理論說,稅法中規定了四種所得的來源,但是后來發現雖然該稅法設計簡便易行,但無法對納稅人的收入廣泛征稅。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1920年3月29日頒布的德意志帝國所得稅法采用了純資產增加說,將所有可能使得納稅人財產增加的因素都考慮在內,但是該制度卻因規定的范圍過于廣泛而難以實行。于是德國自1925年起為了明確稅收立法的內容,根據實際之需要列舉了所得的種類,并在1934年以后兼采上述兩種不同之所得理論,其中雖然規定有“其他所得”類目,但仍然是列舉式地定義了“其他所得”的內容,并非開放式的示例。美國則一直采取純資產增加說,通過列舉方式列舉15種可能產生所得的來源,幾乎囊括納稅人的所有收入,并且規定毛所得并不限于規定的15種來源。但是美國的《國內收入法典》明確將一部分不屬于所得稅征收范圍的“非所得”排除在個人所得稅征收范圍之外,包括“根據人壽保險合同,因死亡、患有不治之癥或慢性病而獲得的收入”等。日本則跟隨美國步伐,于“二戰”后一改對于所得概念的源泉理論概念為凈資產增加說理論。
從我國稅法實踐來看,現階段明顯采取對個人收入廣泛征收的理論概念,采取的是凈資產增加說。臺灣學者柯格鐘也認為,我國所得稅法上所得之概念,應系采取與美國、日本相同之純資產增加說的所得理論為基礎。但是基于德國的實踐凈資產增加說具有局限性,以該說為基礎的稅收設計過于廣泛,難以實行,我國稅收執行的過程也的確體現這樣的困境,并且出現國家立法機關對相關行政機關的授權現象。所以根據德國目前兼采兩種所得理論的實踐,先是根據凈資產增加說將可能產生所得的來源和因素列舉,然后通過對“偶然所得”項目的正面列舉限制國家機關征收范圍,以達到提高法律確定性的作用。該實踐對于我國稅法領域所得的概念具有啟示作用,并且可以參照美國做法,對“非所得”進行列舉或者定義,以明確不包含于所得中的收入,對所得的定義進行明確。
四、對于我國稅收法律領域“所得”概念建構的建議
我國可參照德國做法,采取凈資產增加說的同時,考慮源泉理論學說,在執行全面征收的同時,減縮行政機關解釋“何為所得”問題的權力,以達到增加法律確定性的效果。同時,還有一些因素也應當加以重點關注。第一,我國的國情,“所得”定義應當落到公民的意料、預測范圍之內,而不能為實現全面征收的目的而盲目擴大其概念囊括的范圍。第二,正如俄國個人所得稅法改革所取得的成功為世界各國所關注,我國對“所得”的定義和解釋勢必受到境外所關注,在充分考慮中國實際情況的同時,也應當將西方現有學說和成功經驗納入到考量范圍,一方面是為充分考慮境外勢力對該定義的反響,另一方面是承接外國現有經驗,節省本國探尋的時間。第三,結合我國國家政策和稅收制度的改革方向,在實現全面征收的前提下,實現個人所得稅的調節作用,同時契合我國稅制改革、法制建設的目標,做到既維護稅收法律的執行效率,也保護法律的確定性和公信力。考慮到以上幾點因素,下面本文將提出對于我國個稅領域“所得”概念構建的幾點建議。
首先根據上文,我們可以先明確我國基本上采用凈資產增加說來理解所得,基于該理論個人所得稅的征稅對象應當是:供消費用之財產的市場價值加上兩個時點間財產價值的變動減去財產本身的價值波動。實際上,我國所列舉的“工資、薪金所得”等9項內容對比美國詳細到“事業養老金收入”以及“兼職收入”等15項具體的表述來看相對模糊。我國可以通過對于稅收制度中9項所得進行明確的法律解釋的方式來逐步歸納出我國稅法領域的所得范圍,正如我國現在所實施的個人所得稅的綜合征收制度改革,應當在凈資產增加說的理論支撐下,通過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法律解釋的方式逐步產生對該9項所得的基本解釋,將“所得”的范圍固定在法律解釋的文本中,而非由國務院通過行政法規和公告來變動。若是目前規定的就像類目不能囊括國家的稅收范圍,則應當適當考慮根據我國經濟和實際國情添加類目,而非將類目不能涵蓋的收入內容強行歸類。
其次,通過借鑒德國實踐的相關經驗,我國即便希望也必須在稅法的明文規定之中加入可供政府變通的規定,也應當對可以變通的范圍作出限制,而不能任由所得的概念不斷擴張。例如,假設“其他所得”這一類目仍然存在,也許放棄采用開放式示例的方式而采取列舉式的定義來限制該類目的具體范圍更為行之有效。當然將這一列舉通過立法的方式實現尚有風險,同樣地,是否可以通過法律解釋的途徑將此類定義相對可變通的類目的內涵加以明晰,達到限縮所得概念的目的。
再次,“所得”的適用對象領域必然可區分為肯定候選域、否定候選域和中立候選域三種。我國稅法尚未在否定候選域角度作出相關規定和解釋,導致納稅人的全部收入實際上都屬于肯定候選域和中立候選域之中,很容易導致對于所得的概念的認定毫無邊界。上文提到的美國《國內收入法典》中明確列舉了該國國內對于所得概念的否定候選域,我國與美國對于所得理解的理論基礎大致相同,都是基于凈資產增加說,可以參詳美國對于所得概念的負面列舉,對我國納稅人收入中應當排除的部分也作出列舉,以明晰不屬于個人所得稅法中所得概念的收入內容,例如排除已經在其他稅種征收范圍內的所得。
綜上所述,對于我國個人所得稅中“所得”概念的界定,從正面可以通過有權解釋法律的方式對現存法律進行解釋,并且進一步增加稅法中列舉的所得概念肯定域的類目,并對可能擴張的類目加以限制;從反面可以通過參詳美國相關法律規定,對已經由其他稅種征收的收入和認為不屬于納稅人所得的收入進行列舉,將其排除出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圍,以從反面列舉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圍和限制“所得”的概念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