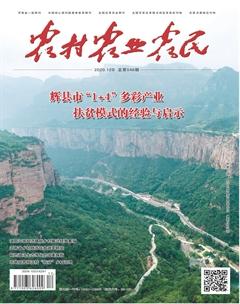積極引導勞動力回流 助力河南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李中建
摘 要:作為勞動力輸出大省的河南,要實現縣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的外流問題。農村勞動力回流,是一種理性的自主選擇,產業興旺、資本支持、創業環境優化,是吸引勞動力回流的主要因素。要加強激勵,創新舉措,改善農村創業環境,積極引導勞動力回流,在助力鄉村振興中實現河南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勞動力回流
縣域經濟是包含著廣大農村、涵蓋著農業、含育著農民在內的區域經濟板塊。2014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調研時對縣域治理提出以強縣富民為主線、以改革發展為動力、以城鄉貫通為途徑的“三起來”要求,深刻洞察了縣域治理的特點和規律,是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遵循。河南省委書記王國生在今年4月召開的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工作會議上,高度肯定了縣域經濟在河南經濟大局中的地位。作為全國重要的農業大省、人口大省、新興工業大省和交通大省的河南,長期以來,“三農”是實現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將這一愿景化為行動,就要深入考察農村勞動力的外流與回流問題。
一、農村勞動力外流引起的問題不容忽視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人口占比近80%,農業勞動生產率和邊際收益極低,隨著沿海開放和城市改革的興起,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沿海流動,成為農民獲得額外收入、擺脫貧困的理性選擇,地方執政者普遍將促進勞動力轉移視為發展縣域經濟、緩解人地矛盾、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在理論上,配第和克拉克揭示了產業結構演進的必然性,為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提供了理論基礎,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假說為農業勞動力轉移提供了有力支持。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河南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經商,務工收入成為農民擺脫貧窮、勤勞致富的重要來源。但隨著城鄉關系的不斷演變,大量農村勞動力持續外流引起的問題愈來愈突出。
首先,勞動力持續外流形成了新的“三農”問題。持續的農村勞動力外流造成的積累效應,已成為新的“三農”問題根源所在。突出表現在農村空心化嚴重,現代農業后繼乏人,農民的農業經營收入增長趨緩。“農二代”長期隨父母在城市,沒有農業生產實際經驗經歷,而且普遍對農業不感興趣,留守老人和婦女構成了我國農業生產主力軍。在持續的農村勞動力外流影響下,要建設一支有文化、會技術、懂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還缺乏足夠的對農業有興趣的人參與。農民農業經營收入增長緩慢,國家對農業進行了最好的政策支持,即使如此,由于農業經營成本不斷上升、經營規模普遍較小、科技含量不高等因素,農業經營的收入水平較低,農民農業經營收入增長緩慢,農民職業吸引力極低。
其次,外出務工人群的就業質量不高,收入增長潛力有限。目前,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身份仍然是農民工,他們在城市和二三產業的就業,往往處于勞動力市場分割中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崗位多具有臟、累、險等特征,勞動環境較差,勞動保護較弱,工作報酬水平較低,工作的存續時間極不穩定,極易成為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的主體,大多數文化程度較低且技能短缺,在就業單位沒有晉升機會和通道,使這一群體整體上收入處于邊緣地位,收入增長潛力極為有限。
最后,農村外流人口對城市、工業的貢獻趨于降低。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另一方面又面臨資本、技術、管理上的短缺,沿海地區率先發展中大量吸收廉價的勞動力,這一時期,農村人口外流對于緩解農村人地矛盾、促進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改善農民收入的作用非常明顯。但隨著經濟轉型升級,尤其是在制造業中,原來貢獻很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于提高競爭力的內在需要,更多為自動化生產、智能制造所替代時,產生了明顯的“機器排擠勞動力”現象,第二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作用大為降低。第三產業成為吸納勞動力的主要部門,但農村勞動力自身教育、技能等方面的局限,又使他們多集中在較為基礎的層次,收入低下、競爭激烈,在城市缺乏穩定的職業預期。無論是從工業化進程還是產業結構調整看,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的發展空間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從城鎮化視角看,隨著城市房價不斷攀升,農村勞動力很難通過自身努力在城市安家置業。農村外流人口日益成為城市待不下來、農村不愿意回的兩難“城漂”人群。
二、引導勞動力回流難在哪里
農村勞動力回流到農村,尤其是大量具有開闊見識、掌握一定技能的勞動力返鄉,才能給鄉村振興、現代農業農民增收注入活力,才能有效解決農村空心化、現代農業后繼乏人、農業收入增長緩慢等問題,解決農民工的長久歸宿問題。但從現實看,除非因為年老或疾病因素,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不愿意主動返回農村,其根源就在于農村的環境不佳,容納不了就業,更無法滿足其實現發家致富的創業夢想。
首先,難在鄉村缺少產業上。一些地方的農業以糧食為主,種糧效益相對較低,依靠傳統農業實現收入增長極為艱難;工商業不發達,無法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產業鏈條較短,缺少致富門路。如果沒有起步的鄉村產業,外出勞動力返鄉就會形成滯留、閑置。
其次,難在缺少資本投入上。鄉村產業來源于投資,河南的農民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承擔風險的能力和投資的積極性低。據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項,廣東為28995元,江蘇為22675元,浙江為21352元,山東為17775元,湖北為16391元,湖南為15395元,安徽為15416元,山西為12902元,河南為15164元。河南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遠低于廣東、江蘇、浙江和山東,在中部地區與安徽、湖南基本持平,高于山西,也略低于湖北。從融資渠道上看,農民的耕地很大程度上具有社會保障功能,抵押和流轉的意愿不高,抵押和流轉換來的資金較少;宅基地受限于受讓主體范圍的限制和位置,出售、出租的價格并不高;即使農民有信貸需求,也會因缺少有價值的抵押物、缺少有資質的擔保人而無法融資。鄉村資本短缺成為“三農”發展的一個普遍性約束。
最后,難在環境不佳上。經過最近幾年農村環境生態的修改,鄉村基礎設施嚴重滯后的情況有所改善,但鄉村的公共基礎設施的水平和質量仍遠遠落后于城市。更為重要的是,鄉村辦事難,創業更難,人情風、官本位在鄉村仍有較大的市場。
三、通過農村環境優化促進農村勞動力回流
在根本上,勞動力的外流與返鄉,是勞動者的理性選擇的結果,是勞動力綜合判斷農村的推力和城市、工業的拉力,是自主決策后的行動。要有效促進農村勞動力回流,為鄉村振興找到源頭活水,為河南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找準突破口,必須大力優化農村干事創業的環境。
首先,抓好關鍵的少數。村“兩委”擔負著鄉村經濟發展和社會事務的重任,是鄉村政治經濟秩序展開的執行者,也是鄉村振興的具體實施者,“兩委”的產生和議事程序、工作作風,直接決定了鄉村的制度環境。抓好村“兩委”班子建設,讓政治立場堅定、擁護黨的政策、作風正派、群眾威信好的村民進入村“兩委”。規范議程程序,透明鄉村財務、鄉村事務,使村“兩委”成為公平秩序的維護者、基礎設施建設的實施者、公共事務的承擔者。
其次,促進資本回流。利用鄉情這一紐帶,積極聯絡鄉村外出的企業家資源,為其在家鄉舉辦產業提供土地流轉、配套設施等便利,無論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還是維護其在鄉村中榮譽和地位的考慮,返鄉的企業家都會將較有前途的配套性環節放在自己的家鄉。
再次,做好對致富帶頭人的激勵。引導鄉風鄉俗,對鄉村致富帶頭人授予榮譽,吸納政治立場好、帶領群眾致富效果好的能人進入村“兩委”。
最后,促進新鄉賢培育。鄉村人才嚴重短缺,返鄉鄉賢可以發揮精英的個人才能,對提升鄉村發展和治理水平具有極好的促進作用,但也要防止這些精英“寡頭化”。充分梳理鄉村外出參軍、上學、經商、從政等人才資源,創造條件吸引其返鄉參與鄉村建設,形成一批有資源、有品行、社會形象好的新鄉賢力量,通過這些新鄉賢力量,帶動資本下鄉、項目下鄉、文化下鄉、技術下鄉等,大力改善鄉村面貌,以更優質的環境吸引鄉村勞動力回流。
參考文獻:
[1]宋亞平,《“縣域經濟”到底是什么?》,江漢論壇,2009年第5期:5-12.
[2]馮文海:《發展縣域經濟 實現富民強縣》,《求是》,2002年第23期:28-30.
[3]朱冬亮、洪利華:《“寡頭”還是“鄉賢”:返鄉精英村治參與與反思》,《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作者系鄭州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勞力流動與地方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