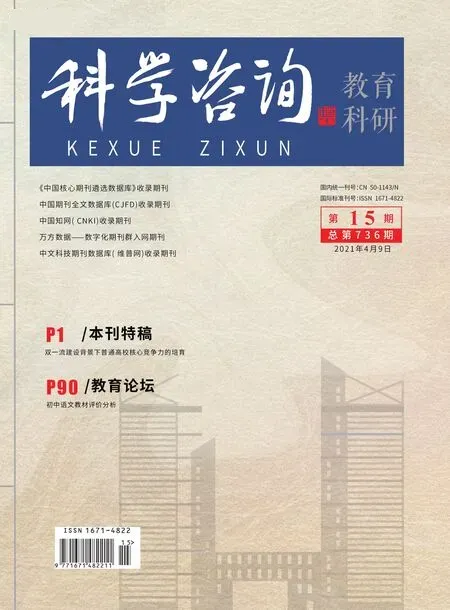新時期背景下高校體育教學中德育功能實現的路徑探究
沈 源
(南京理工大學 江蘇南京 210094)
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中談到“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皆寄于體,無體是無德智也。”[1]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體育這門學問和德育智育相互配合,而道德和知識都寄托在身上,沒有身體就沒有道德和知識。由此可以看出,德育與體育密不可分,沒有體育,德育就無從談起了。
一、我國古代至近現代體育中德育功能
學校教育作為培養社會人才和傳播文化的重要環節,也是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與我國悠久的中華文明相對應,我國在古代就產生了學校和教育制度,并分為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
(一)我國古代體育教學中的德育功能
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就已經出現了最早的學校教育,直到西周,我國古代學校教育制度已經初具規模,出現以“六藝”為核心的教育體系,其中“禮、樂、射、御”為我國古代學校體育的教育內容。與體育有關的“禮、樂、射、御”占到了“六藝”的一大半,并且“禮”教更是我國古代的核心教育內容,在“六藝”的教育體系中占據第一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體育在古代的教育體系中占到了相當重要的位置。“樂”教通過對學生進行樂舞的教育可以使學生的身心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以樂舞的形式熏陶人的性格以及內心世界,時人戒掉驕橫,蠻夷的思想以及各種惡習。在身體得到鍛煉的同時,身心也得到很大程度的發展。“射”即為“射藝”,學校設立這個課程的教育,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射箭是作為軍事和禮教的主要手段,但“射藝”又被尊稱為“射禮”, 按照“射禮”的等級,被分為“大射”“賓射”“燕射”與“鄉射”,這是因為射箭被定為等級分明的禮制活動和道德觀念培養的重要手段。“御”指的是古代祭祀駕車,出行駕車,戰車駕車的總稱,其中祭祀駕車和出行駕車十分注重禮節,尤其體現在古代的王宮貴族身上。“御”是一個有所作為的人必須掌握的技能和道德高低衡量的標準,這是一個古代學生“六藝”教育的必修課。
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他在德育上的思想是其修身養性和實現發展的核心理念,他提出仁愛、禮義、忠恕、明智和誠信的理念。這些理念不僅在思想方面引領著人們正確的實現為人處世之道,同時在實踐中也體現了道德的重要性。春秋末期,我國奴隸制禮崩樂壞,孔子為舊的禮樂制度中加入了新的教育思想,將他的德育理念與體育教育相融合,提出“寓教于樂”的教育原則和理念,在體育活動中培養學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心理品質為活動的主要目標。在繼承“六藝”教育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仁”與“禮”的教育理念,注重學生的德育教育,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始終重視將德育貫穿于體育的教育過程中。
(二)我國近現代體育教學中的德育功能
西方教育家斯賓塞在《教育論》中討論了有關智育、德育、體育的思想,提出要同時發展學生的道德、智慧、身體三方面的能力。《教育論》由四篇論文構成,分別是《什么知識最有價值》《智育》《德育》《體育》。斯賓塞在其中所提出的智育、德育、體育,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科學在教育中的地位,穩固智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并沒有討論到三者之間的關系。首先將斯賓塞帶入國人視線的是圣約翰書院學監顏永京,在1882 年,他以《肄業要覽》為題翻譯了《教育論》的第一篇《什么知識最有價值》。[2]他在文中將教育一次翻譯為肄業,書中也并未提及智育、教育、體育。嚴復則是將斯賓塞的思想帶入中國最重要的人物,他于1985 年發表了一篇《原強(修訂稿)》,文中他以《明民論》為題解釋了關于斯賓塞《教育論》中的幾篇文章,“斯賓塞爾全書而外,雜著無慮數十篇,而《明民論》《勸學篇》二者最著名。《明民論》者,言教人之術也。《勸學篇》者,勉人治群學之書也。”[3]斯賓塞在論述教育時,將對象默認為初等教育體系中的兒童,而嚴復卻將對象擴展為“民”,并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將國家的強盛衰弱與否和人民的德智體育的水平相聯系。1906 年嚴復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系》的文章中提到“是以講教育者,其事常分為三宗:曰體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三者并舉,顧主教育者,則必審所當之時勢而為之重輕”,在此時德育智育體育已經成了教育的流行用語。
在民國時期1912—1913 年間教育部頒布了“壬子學制”,在這種學制下的中小學“學校令”中規定中小學仍設體操一科,以兵操為主。在學校中既有體育課,也有課間操和課外體育活動,并逐漸組織了各種體育部和運動隊,所以把學校這種既有“以兵操為主”的體操課,又有以田徑、球類為主的課外活動的形式稱為“雙軌制體育”。 由此可以看出,早在20 世紀初,體育教育已經在中國開展起來,但將其與德育和智育的結合還停留在國民的層面,并未將其完全列入到教育的體系中來。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與完善,教育體系也隨之完善。通過社會生活的影響,德育、智育、體育三者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隨之發生變化,人們越來越覺得德育在人的成長發展歷程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素質教育就是指一種以提高受教育者諸方面素質為目標的教育模式,它重視人的思想道德素質、能力培養、個性發展、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通過教育引導,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作為指導思想。由此可以看出德育在教育體系中已經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了,毛澤東曾將體育列為教育之首,但在進行體育教育的同時,更要牢記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
二、高校體育教學中的德育功能實現的路徑
1998 年,Berkowⅰtz 提出道德教育是任何有計劃地提高道德功能。現當代大學生的德育教育還未完全結束,他們自身的道德習慣并未完全養成,需要不斷對其培養良好的道德習慣,使其具有穩定性。在大學校園內,不僅有規定的傳統體育技能課,更有各種各樣的體育文化活動,而道德教育則無時無刻地貫穿在這些體育課堂與活動中。由此可以看出,在高校的體育教學中,道德教育起到了引領和規范的作用,反之,體育教學以及文化活動等則是道德教育的踐行者。
(一)以關愛生命作為體育教學的起點
美國的倫理學家蒂洛認為,倫理體系的構建,首先就是生命,沒有生命就沒有倫理可言。[4]生命作為萬物的起源,沒有生命,道德就無從談起了。在我國古代,有“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之說,要求人們要珍惜父母給予你的肉體,不可輕易毀壞他。近幾年來,國內發生不少有關大學生輕易結束自己生命的事件,可見國內有關珍愛生命的觀念的灌輸仍然缺乏。在大學內可通過傳統的運動生理課來讓同學們了解自己的身體,再通過組織大量的體育活動、運動會、體育文化節等,從而潛移默化地將珍愛生命的觀念進行滲透,從而養成良好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二)將公平正義視為體育教育的前提條件
在當今世界,各個國家的激烈競爭更多地體現在經濟、國防和民族凝聚力上,想要國家在綜合實力上的增強,離不開學校教育這一陣地。體育教育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勢必要面臨各種競爭,不論是在體育教學的過程中,還是在運動訓練的過程中,都要注重培養學生公平競爭的意識,通過體育競賽活動來樹立學生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培養青少年良好的體育道德風尚。大小比賽及活動均嚴格按比賽規則,通過執法的裁判員公正、公平、公開、準確的裁判,堅決反對不正當襲取行為。當代大學生作為祖國的未來,既要學會拼勁努力取得勝利,也要學會體面地面對失敗。
(三)愛國主義是體育教育堅守的底線
當代奧林匹克運動是以國家作為代表隊參加,由此更是凸顯了體育運動中愛國主義精神的貫徹。通過我國由于綜合國力的提升,從而獲得奧運會舉辦權以及我國運動員在國際賽場上取得傲人的名次,都可以作為愛國精神的教育案例。通過名人事例來對高校學生進行愛國主義精神的教育,在體育課堂中加強愛國精神的灌輸,潛移默化地讓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激勵學生奮發向上的精神,增強愛國熱情和為祖國建功立業的使命感,更有利于學校良好校風,學風的形成,學校呈現穩步向上發展的態勢。
(四)與時俱進必將成為體育教育的不竭動力
隨著國內外形勢的不斷變化,人們的社會生活也時時刻刻發生著變化。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僅要重視知識與技能的提高,更要重視對學生綜合素質的教育,尤其是德育的教育,防止學生出現道德品質的缺失。要做好新時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從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現實的角度,深刻分析新形勢下對廣大干部群眾的思想活動發生作用的客觀環境及其基本特點,正確審視和解決影響群眾思想活動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5]德育的根本任務就是要根據新情況,發現新問題并解決它,從而來揭示規律性的新特點,探索新思路,尋求新方法、新途徑,并且要為新的實踐提供科學的理論支持和指導。根據大學生現階段所要遵循的教育規律,把握住學生成長所需要的主客觀條件,使德育教育能夠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