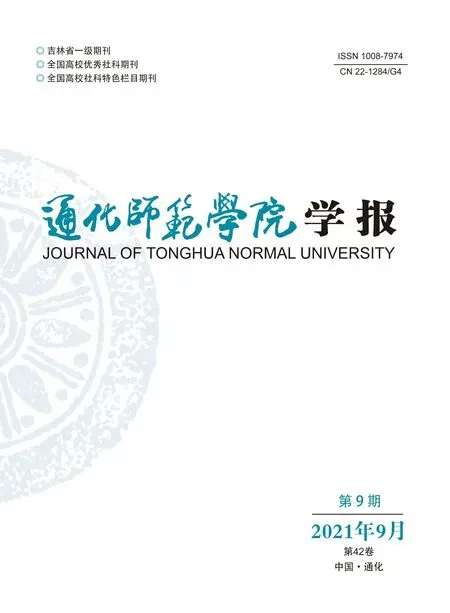扎根邊疆·學術戍邊
——高句麗歷史遺產守望者耿鐵華教授訪談錄
孫煒冉
耿鐵華,1947年5月生于吉林省扶余縣,1975年畢業于吉林師范大學(今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1978年考入徐喜辰教授門下,攻讀先秦史碩士學位,1981年畢業后留校任教。1982年調入集安博物館,開始從事好太王碑研究和高句麗歷史文化遺跡的考古發掘與保護工作。1998年調入通化師范學院高句麗研究所(院),擔任所長(院長)職務。從業40年來,耿鐵華教授專攻高句麗相關歷史研究,在國內外具有極高的學術影響。他著有《中國高句麗史》《高句麗史論稿》《高句麗考古研究》《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好太王碑新考》《高句麗史籍匯要》《中國學者高句麗研究文獻敘錄》《高句麗歷史與文化》《高句麗歷史與文化研究》《高句麗歸屬問題研究》等30多部著作;在國際、國內發表有關高句麗問題相關論文200多篇,學術論文曾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耿鐵華教授主持并完成國家和省級科研項目10余項。1993年國務院批準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他曾先后被國家、省、市及學校評為特等勞動模范和教學先進名師,被中宣部、國家教委授予“八十年代優秀大學畢業生”稱號。
2020年10月,在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邊疆研究所主辦的《中國邊疆學》(第十二輯)上刊發了《改革開放40年來高句麗研究現狀分析——以研究成果的數據統計和內容分析為中心》,根據中國知網(CNKI)1979年到2018年收錄的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研究的文章,對于作者隊伍和研究機構、文獻來源(核心刊物)、經典文獻等進行列表比較分析。其中關于核心作者的發文總量、CSSCI檢索數量、被引頻次、經典文獻及被引頻次等5項內容的比較列表中,耿鐵華教授均排在首位。鑒于耿鐵華教授對于高句麗問題研究的建樹及在國內外的學術影響力,使得這一成果統計與說明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基于耿鐵華教授在高句麗研究領域的巨大成就,我們專門對其進行了如下訪談。
問:耿老師,您對《中國邊疆學》2020年第12輯上發表的《改革開放40年來高句麗研究現狀分析》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去年秋天,有人從網上將這篇文章傳給了我。不過,到現在我也沒看到這本書。當然了,這篇文章是運用計量史學方法進行統計分析研究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研究狀況的。有方法說明、數量統計、列表比較和分析總結。發文數量主要依據中國知網(CNKI)中收錄的CSSCI期刊的數據,影響因子則根據知網上的引用數量列表比較。說來慚愧,我在個人相關項目數據的統計上都名列第一。從研究團隊的成果統計來看,通化師范學院在一級研究機構中排名第一。在研究刊物的論文發表來看,《通化師范學院學報》排名第二。對于我們這座長白山區的邊疆大學是一種肯定和鼓勵。當然,這只不過是一種計量學上的統計,其中還存在著一些難以說明的因素。而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不只體現在發表論文的數量上,還要看論文的內容、含量,特別是研究的深度、廣度及其影響等方面。
還有,中國知網在收錄高句麗問題研究的論文方面也存在著力所不及的遺漏或不足,CSSCI期刊及引用數量也存在著某些變化。論文的標準界定、人工選擇、數理統計中也還存在著某些不穩定因素,總的看來,《中國邊疆學》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影響性,其《改革開放40年來高句麗研究現狀分析》一文可以作為改革開放40年來高句麗研究狀況的一次總結,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問:您從事高句麗研究較早,至今已經幾十年了,研究成果恐怕不只是知網上收錄的那些吧?很多研究成果國內外影響很大,這些論著獲得了哪些獎項能不能介紹一下。
1982年,我來到了集安博物館從事高句麗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參加過多次考古調查與發掘,發表和整理了一批高句麗歷史與考古方面的資料和文章。1998年,我調入通化師范學院高句麗研究院(1995—2005年為高句麗研究所)。至今,從事高句麗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已有40年了。初步統計一下,發表各類論文230多篇,其中有高句麗歷史與考古論文(包括合作)200余篇,出版研究著作(包括合作與主編)36部。有10多部獲獎:《中國高句麗史》獲得吉林省長白山優秀圖書一等獎、中國圖書獎提名、吉林省社會科學著作二等獎、第一屆吉林省政府圖書出版一等獎;《高句麗古墓壁畫研究》獲吉林省社會科學著作類優秀成果一等獎;《集安高句麗碑》獲第三屆吉林省新聞出版獎圖書類精品獎;《高句麗壁畫研究》獲第四屆吉林省政府圖書出版精品獎。吉林省政府出版獎至2020年評了四次,我的三部著作獲得三次獎,第一次獲得一等獎,以后幾次不設等級,都是精品獎。
問:據我們所知,您的研究成果包括論文發表的數量、著作出版的數量及獲獎的等級和數量,在國內外高句麗研究領域都處在絕對的領先地位。能不能說一下您的研究都有哪些特點呢?
從成果的數量和獲獎情況看,在高句麗問題研究領域,目前我應該暫時處在領先地位,多年以后必定會有學者超越的,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嘛。至于我的研究特點,應該與我的學習和工作經歷密切相關。
第一,我系統地接受了大學歷史系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對于世界古代史、中國古代史的學習與研究,曾經得到國內知名學者專家的指導,如林志純、朱寰、徐喜辰、萬九河、陳連慶、吳楓、馮君實、李洵、趙德貴、詹子慶先生等。考古與古文字學課程則是由張忠培、孫曉野(常敘)兩位先生講授和指導的。張先生的《考古學概論》和《先秦考古》對于我在集安的高句麗考古調查與發掘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孫常敘先生的《兩周金文研究》為我后來的高句麗碑刻研究奠定了基礎。在集安博物館工作期間,正趕上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我有幸作為調查隊長跑遍了集安全境,還到通化、柳河、梅河口、白山、桓仁等地進行過調查,對于國內高句麗遺址、古城、山城、墓葬、碑刻的分布與保存現狀、研究情況有了深入的了解,極大地提高了我的高句麗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和研究能力。
第二,我是在改革開放后不久進入到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研究領域之內的。1984年第1期《文物》雜志發表了一組高句麗文物考古的報告和論文,在這一期發表的《集安出土高句麗陶器的初步研究》是我撰寫的第一篇高句麗研究論文,也是國內最早的有關高句麗陶器研究的論文。此外,我發表的《集安出土的高句麗瓦當及其年代》(《考古》1985年第7期)、《高句麗起源和建國問題探索》(《求是學刊》1986年第1期)、《高句麗漁獵經濟初探》(《博物館研究》1986年第3期)、《高句麗壁畫中的社會經濟》(《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高句麗民俗概述》(《求是學刊》1986年第5期)、《集安高句麗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9年第1期)、《高句麗釉陶的類型與分期》(《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3期)等文章,無論從研究時間、研究內容及其方法的創新上,都起到同類文章的首創視角和學術引領作用。
第三,我的高句麗研究內容相對來說是比較開闊的,涉及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的多個方面。高句麗歷史研究論文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宗教、傳說等諸多方面。考古研究論文有遺址調查、古城研究、墓葬研究、壁畫研究、碑刻研究、可移動文物研究等諸多方面。高句麗研究著作也包括歷史和考古兩個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歷史類著作有《中國高句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高句麗史論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高句麗研究史》(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年);考古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高句麗瓦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高句麗考古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高句麗壁畫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8年)、《集安高句麗碑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8年)、《好太王碑拓本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8年)、《高句麗瓦當藝術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20年)等。
問:據我們了解,您從事高句麗研究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您開始從事高句麗問題研究正好處在了改革開放的歷史節點,在這之前的一些老一輩研究者和之后新興的學者都與您有所交集,您是當代高句麗研究的親歷者,那么請您介紹一下當代高句麗研究的隊伍情況。
我是改革開放以后加入到高句麗研究隊伍中來的。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高句麗研究隊伍人數不多,成果也較少。主要是吉林省、遼寧省博物館和文物管理部門的保護、調查與研究。學術論文主要是集安和桓仁等地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報告,沒有高句麗歷史和考古的綜合研究論文,更沒有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的著作出版。參加調查發掘、編寫報告的有吉林省博物館的王承禮、李殿福、方起東,遼寧省的陳大為等。改革開放以后他們依然活躍在高句麗考古領域,從事相關調查、發掘與維修工作,同時開始發表綜合性研究論文,如李殿福的《集安高句麗墓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方起東的《集安高句麗墓壁畫中的舞樂》(《文物》1980年第7期)、陳大為的《桓仁高句麗積石墓的外形和內部結構》(《遼寧文物》1981年第2期)等。歷史學界的學者們也先后參與了高句麗問題研究,主要成果有:顧銘學的《〈魏志·高句麗傳〉考釋》(《學術研究叢刊》1981年第1、2期)、劉永智的《好太王“辛卯年”記事初探》(《學術研究叢刊》1981年第2期)、徐德源的《高句麗社會性質問題的綜合述評》(《遼寧大學學報》1982年第6期)、劉永智的《幽州刺史墓考略》(《歷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張博泉的《“別種”芻議》(《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等。
高句麗問題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由王健群著的《好太王碑研究》,1984年8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我從事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研究之后,與這些學者都有過不同層面的交往。老一輩的高句麗研究學者還有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健才、劉萱堂,黑龍江社會科學院的張碧波,延邊大學的樸真奭、姜孟山、劉子敏,吉林大學的魏存成,遼寧省博物館的王綿厚等。這些學者都是在高句麗研究領域中影響很大的,其中王承禮、李殿福、方起東、陳大為、李健才、劉萱堂等學者在改革開放以前就已經從事高句麗考古調查發掘和壁畫臨摹的工作。改革開放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多些。我和這幾位學者都有過多次接觸和不同程度交往,主要是他們先后多次到集安調查發掘或檢查指導及研究。尤其是方起東和李殿福兩位先生,每年都要到集安多次,有時會在集安停留居住十天至半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我都會和他們一起調查發掘、維修、撰寫論文、參加學術會議,尤其是在與中外高句麗學者交流的過程中,我學習到了不少東西,對于高句麗歷史與考古諸多方面的了解和認識也不斷深入和提高。
改革開放以后,進入到高句麗研究領域的有張博泉、顧銘學、劉永智、王健群、樸真奭、姜孟山、徐德源、張碧波、劉子敏、魏存成、王綿厚等學者,與他們的接觸和交往主要是陪同在集安考察研究或參加學術會議等,他們自改革開放以來這段時間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影響很大,我在同他們的交往中也有很多的收獲。一方面,在對待高句麗歷史文獻上,無論是正史中的《高句麗傳》《高麗傳》,還是王氏高麗首部正史《三國史記》等,基本意見是一致的,對于一些歷史與考古問題的看法也都相同或者相近,完全可以起到學習、交流和傳承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高句麗歷史的分期、社會性質,以及高句麗墓葬的類型與年代、壁畫墓的分期、古城遺址的年代、碑刻的隸定與考釋等方面大家存在著較大分歧,這些都是很正常的現象,既可以相互討論,也可以相互切磋,不斷提高。
目前,這些老一代的高句麗研究學者大都已經不在了,只有樸真奭(1926年生)、徐德源(1927年生)、張碧波(1930年生)、魏存成(1945年生)、王綿厚(1945年生)等健在。樸真奭先生在延吉,他于90歲時還參加了一次學術座談會,發表了論文,把自己的論文集《爭鳴集——樸真奭文集》贈送給我們參加會議的人。徐德源先生在沈陽,張碧波先生在哈爾濱,兩位老人都已經超過90歲了,不久前我們還通過電話,他們還關心著高句麗研究的現狀、研究隊伍的建設、年輕人的培養、學術會議的召開與考古調查發掘的新進展、新發現。魏存成先生在長春,王綿厚先生在沈陽,這二位年長我一歲多,都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參加到高句麗歷史與考古的研究隊伍中來的,雖然已經退休了,仍然承擔著國家的重點研究項目,每年都要在一起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交流、交往與見面的機會很多。2020年11月初,我和魏存成先生作為《東北古代方國屬國史研究叢書》的編委會成員,在長春南湖賓館出席了這套叢書的出版發行座談會,我倆的座位緊挨著,借機進行了一些交流,涉及高句麗項目的進展和相關著作的出版、論文的發表等問題。目前,我們三位也都已經年過古稀,是國內高句麗研究領域年齡較大的學者,擔負著承上啟下的重任。我們會努力學習和研究,不斷提高,把傳承工作做得更好。
問:你們這一代學者承擔著培養學生、建設隊伍、深入研究的重任,特別是參加田野調查和考古,一定非常辛苦,還有很多體會與收獲,能否介紹一下您參加過的調查與發掘。
我到集安博物館工作不久,就趕上了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很快就進入了狀態,使我對集安乃至通化地區的歷史文化、文物分布有了初步認識,也為我后來的工作與研究打下了基礎。40年來,我參加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不少,其中規模較大、對我影響比較深刻的有這么幾次。
第一次,是1983年至1984年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與文物志編寫工作。1983年春季,為了搞好文物普查和編志工作,吉林省文化局在德惠縣舉辦了文物干部培訓班,我和通化地區的幾位同志參加了培訓,聽了張忠培、林沄、李殿福、方起東、劉萱堂等老師的專題講座,明確了普查工作的各項準備和時間安排。4月中旬,組成了兩個普查隊,我帶隊負責集安老嶺嶺后幾個鄉鎮(當時還稱“公社”)的文物普查,傅佳欣負責集安老嶺嶺前幾個鄉鎮的文物普查。經過兩個多月的工作,基本摸清了集安地區的文物分布狀況,發現了幾處較大的古代遺址,采集了一批有特點的文物標本,完成了遺址、墓葬、文物的測繪、畫圖、拍照和記錄。6月至7月,博物館統一組織對老嶺前后的文化遺跡進行了重點復查,再經過省文化廳方起東、李殿福等人的檢查驗收,進入資料整理階段。同時對于館藏文物進行全面核對摸底,揀選可以進入文物志的重點文物,登記造冊、測量、繪圖、拍照。10月,集安博物館組成《集安縣文物志》編寫小組,我和林至德、傅佳欣、張雪巖、孫仁杰參加編寫,分別承擔一些章節、條目的文字,還有繪圖和拍照。經過多次討論,我和傅佳欣進行了文字統一和修改,通過了吉林省文物志編委會終審,1984年出版。集安作為高句麗都城長達425年(公元3—427年),現在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遺產所在地,保存著眾多珍貴且重要的高句麗文物遺跡,尤其是丸都山城、國內城、高句麗王陵、貴族墓葬壁畫墓、好太王碑等聞名世界的文化遺產,集安博物館館藏文物中有不少國寶級的高句麗文物。因此,《集安縣文物志》的出版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
1984年第1期《文物》雜志刊發了一組(5篇)集安博物館的發掘報告和研究論文,在高句麗研究學界引起不小的轟動。其中《集安出土高句麗陶器的初步研究》是我第一篇高句麗文物研究的論文,從此開始了我的高句麗研究之路。我的起步較晚,在方起東等先生的幫助下,起點則是較高的。
第二次,是《集安縣文物志》書稿完成以后,為了配合集錫公路建設,對禹山墓區的高句麗古墓進行發掘。當時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方起東總體負責,我則擔任工地負責人。第一階段是1984年6月20日—11月20日;第二階段是1985年5月15日—8月15日。這次清理發掘了各類古墓113座,包括積石墓38座、封土墓73座、土石混封墓1座、石棺墓1座,出土遺物931件。除了石棺墓年代可能要早到戰國時期,還有幾座封土墓要晚至渤海時期,其余絕大多數是高句麗時期的古墓。墓葬類型較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集安的高句麗墓葬,有積石墓和封土墓兩大類。高句麗墓葬的分布、排列、結構有自己的特點,發掘方法及其工具都與自身的特點有關,這些在大學考古課堂上是學不到的,需要到考古工地向老同志們學習,不斷地實踐。我負責發掘的JYM3283是最有特點的,是一座典型的階壇壙室墓,平面接近正方形,邊長17米,殘高3.3米,有四層階壇。壙室遭到破壞,東西長2.7米,寬不詳,深0.5米。墓底部鋪一半鵝卵石,一半碎山石。壙室中出土一批陶器、鐵器、金器、銀器和鎏金器。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了41件鐵魚鉤和167件陶網墜。墓上還發現了少量的瓦片,或許曾有建筑存在,可以推測墓主人應該是管理漁獵生產的官吏,年代大約在5世紀前后。這對于認識高句麗墓葬的類型、結構、年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三次,是1993年至1994年我主持了洞溝古墓群“八五”維修項目,對于山城下墓區和禹山墓區的51座高句麗古墓進行維修。這次工作的重點在山城下墓區,共有47座積石墓和封土墓,包括龜甲墓、蓮花墓、美人墓、兄墓、弟墓、折天井墓、JSM1411、JSM1407、JSM1305、JSM798等重要墓葬。從調查、測繪拍照開始,每一座墓要制訂出維修計劃,還要清理出原型,搞清楚原來墓葬的形制、規模、墓室、壙室的情況,是否存在壁畫,壁畫保存狀況,附屬設施及出土遺物等等。在清理維修過程中,一定要保持墓葬的原來形制規模,即所謂“修舊如舊”。對于階壇、墓室缺損的石材盡量從傾頹堆棄的石材和石料中選取,封土墓要對墓室進行防水處理,特別是對于幾座壁畫墓和墓室較大、保存較好的,更要做好。還要維修墓域、整理環境,為后來建設露天高句麗古墓博物館打下良好的基礎。每天在工地上,無論刮風下雨,很少停工。晴天在室外清理維修,陰雨天在室內整理文物,討論修改維修方案。經過兩年多的工作,國家文物局專家張忠培、徐蘋芳、黃景略等對完成情況都十分滿意,其中部分墓葬后來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項目之中。
第四次,是2003年春,為了申報世界遺產,吉林省與集安市的文物工作者對集安的國內城、丸都山城、12座高句麗王陵(包括好太王碑)和26座貴族墓葬進行清理維修、整頓環境、植樹種草,迎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團檢查。此時,我已經離開集安博物館5年多了,沒能參加高句麗王陵和貴族墓葬的清理工作。在我離開集安以前,曾對太王陵、將軍墳和部分壁畫墓進行清理維修,重要的是吉林省文物局將我所著的《中國高句麗史》一書發給工地的每一位工作人員,用以參考清理維修和附屬建筑的建設。我也算是為集安的申遺工作盡到了微薄之力,用以回報集安博物館對我的培養和教育。2004年7月,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通過了我國申報的“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項目,將其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也是我們這些研究高句麗歷史與考古人的驕傲。
第五次,是2009年至2010年,集安博物館新館建成,我參加了展陳大綱的編寫工作。和我一同參加討論和分工的還有吉林省博物館吳輝,東北師范大學傅佳欣,集安博物館孫仁杰、董峰。由我執筆撰寫展陳大綱,傅佳欣、孫仁杰、董峰遴選文物,設計展陳文物及圖版。我們被安置在某部隊招待所大院內,閉門寫作,最后完成了展陳大綱的初稿。無論從高句麗歷史發展階段,還是從考古文物的年代分期出發,來表現高句麗建國前后兩個階段的歷史,的確有一定難度。集安只是高句麗第二座都城,時間從西漢末年到北魏時期,即公元3年到公元427年。如何處理高句麗建國前的民族狀況,建國初期都于紇升骨城(今遼寧省桓仁縣城附近)的40年歷史,高句麗遷都平壤(今朝鮮都城平壤)時期的歷史,都存在一些難題。更主要的是,需要表現的部分歷史階段文物遺跡較少,而某些階段文物遺跡又很多,特別是同類型的文物數量多,類型又較少,如何平衡與調整,難題很多。最后,還是以集安的文物遺跡為主,按照歷史發展的階段編寫,比照1949年以前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和其他階段歷史與文物,較好地完成了展陳大綱。根據吉林省和國家有關專家的意見,進行了多次修改,最后通過了審查、布展,完成了對外開放。
第六次,是有幸參與集安高句麗碑的問世。2012年7月29日,集安市麻線鄉村民馬紹彬在麻線河發現了一通石碑,報告集安博物館;8月14日,博物館董峰、周榮順、高遠大等捶拓出第一份拓本。當時因公出差至集安的我在博物館見到了拓本,十分震驚,當即決定留下來一同商量保護研究措施。集安博物館、文物局向市委市政府匯報的同時,報告了省和國家文物局。當晚,便組成了專家組和保護研究組。我擔任專家組組長,成員有通化市文物研究所王志敏,集安市文物局、博物館的高良田、董峰、孫仁杰、遲勇。集安高句麗碑的調查與研究當即展開。
集安高句麗碑的碑石為粉黃色花崗巖石質,碑體呈扁長方形,下部較上部略寬,頂部為三角形,是典型的圭形碑,下部有榫頭,右上角稍缺損,殘高173厘米,寬60.6~66.5厘米,厚12.5~21厘米,重量為464.5千克。碑的正面陰刻隸書碑文,右起豎書,計10行,前9行每行22字,最后一行20個字,原有文字218個。后來各專家所公布的釋文數字略有不同。我作為專家組和寫作組的組長,帶領集安博物館的同志們多次現場調查,多次捶拓、辨識文字、考證研究、分工合作,兩個月便完成了《集安高句麗碑》的初稿。年末,吉林省文物局和國家文物局組成專家組,由林沄先生為組長,我也作為專家組的成員參與到現場考察,并討論研究成果。專家組高度評價了集安高句麗碑發現以來的保護、捶拓與研究,通過了《集安高句麗碑》的初稿。2013年1月,集安博物館編著的《集安高句麗碑》一書由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我國學者、韓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分別召開了集安高句麗碑的專題研討會,對這一重要發現給予高度評價,同時對于碑文內容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集安高句麗碑》公布識讀的碑文為156個字,這是集安的專家組集體討論研究的成果。當時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見,集體決定各人的釋文及其不同看法可以在《集安高句麗碑》一書出版之后,以個人的名義發表文章。在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國內外學者發表了17種釋文,其中中國學者發表的釋文有10種,韓國學者發表的釋文有6種,日本學者發表的釋文有1種,同時對于碑文的解釋、內容與年代的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見。我作為集安高句麗碑發現以后最早的碑文識讀者和綜合研究者,對于一些不同意見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多次到集安考察,先后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多篇論文。2017年12月出版了《集安高句麗碑研究》一書,這是對集安高句麗碑發現5周年的最好紀念,也成為我對集安高句麗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問:聽聞了您從業40年的學術經歷,親歷和見證了中國高句麗問題研究的發展與壯大,那么最后您對于中國未來的高句麗研究事業有什么期待呢?
40年來高句麗研究的發展歷程清楚明了,取得成果很多、存在問題也不少,許多問題暫時雖然解決不了,但只要有學者堅持不懈地扎根邊疆,恪守“學術戍邊”的精神,相信不久的將來必然會迎刃而解。我們只有立足于通化這片高句麗人曾經馳騁之地、現在世界文化遺產之地,加強保護研究、培養年輕力量、建設好自己的隊伍、做出第一流的成果,才無愧于先賢們在這塊邊疆之地的百年耕耘和學術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