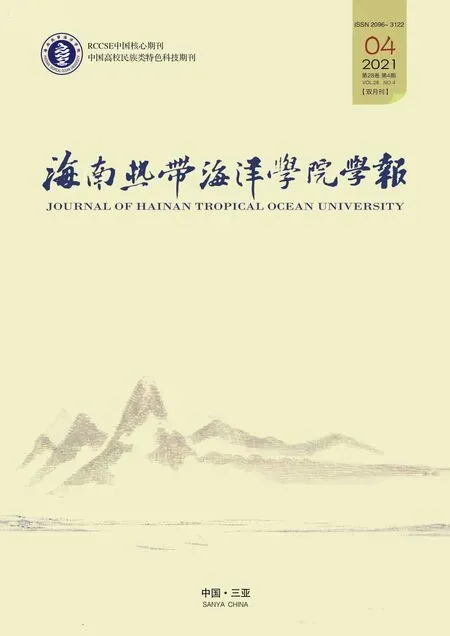張載的道德理想及其建構路徑
——以“橫渠四句”為中心
郭敏科
(首都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北京100089)
大同社會一直以來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張載秉承前人的美好愿望,在《西銘》中進一步描繪了這一藍圖,其志向也通過“橫渠四句”[1]加以總結。但無論是《西銘》所繪的親親社會,還是“三代之禮”的協和有序,抑或是“橫渠四句”的崇高旨趣,都隱隱含有理想化的色彩。在其具體實踐措施上,馮友蘭指出:“王安石的措施是現實主義的,張載所計劃的措施是理想的,或者說簡直是幻想的。”[2]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張載的理想對于政治家來說近乎遙不可及。但是他辟佛造道,重建儒學思想體系,有力地回應了絕大部分的現實問題,這一影響又是為歷史所不能否認的。以此,他的道德理想又與現實的國計民生緊密相連。事實上,張載是從不同維度來回應和建構其道德理想的,“橫渠四句”無疑最為集中地表達了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結合。《西銘》是其“理想國”的基本藍圖,而“橫渠四句”既可看作是其從形而上到形而下完整的表達,也可看作是達致這種理想藍圖的建構路徑。“為天地立心”是以“仁”為心,為人確立價值根基;“為生民立命”是以“義”為命,為人確立應當之路;“為往圣繼絕學”是以“智”相繼,為人傳承文化命脈;“為萬世開太平”是以“禮”相合,使人人均平。“信”者實之,四者皆踐履不懈,則理想可期。這種“理想”,并非是一朝一夕之理想,而是萬世之“理想”。與其說它是一種難以實施的具體政治實踐,不如說它是一種政治實踐背后的正義價值,即他所思考的是,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我們的社會將建基在什么價值之上?如何實現這種價值?“橫渠四句”正是基于這些問題對此進行回應的。
一、 立人心——仁為天地之心
余英時教授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指出,與古文運動和改革運動一樣,重建理想的人間秩序也是北宋道學的政治關懷的中心所在。有所不同的是,“面對著新學的挑戰,他們為自己規定了一項偉大的歷史使命:為宋初以來儒學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一個永恒的精神基礎”[3]。對張載而言,永恒的精神就是在天人之間確立人道價值的基石。在他看來,人為天地之心,而為天地立心,就是以天道為根基確立人心的價值依據,這種價值依據來自天地的生生之德,即“仁”。
人為天地之心,這一論斷歷來為儒家所公認。早在《禮記·禮運》篇就有言:“人者,天地之心也。”[4]277后世南宋哲學家王應麟也說:“人者,天地之心也。”[5]王夫之說:“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6]清朝學者也認為:“天地無心,人者天地之心也。”[7]人何以是“天地之心”?總體而言,是以人之貴與萬物之靈為主要緣由。《禮記》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4]276朱熹似乎秉承了這一觀點:“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于并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而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8]立天地之心,實為立人之心,“故人心即天心,立天之道,所以定人”[9]。
在張載看來,立人心又必須依據天地之心而立,其價值依據來自天。他在發揮《彖傳》時說:“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10]以生物為本就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就是不斷地創生、生生。但是從存在論上而言,生生本身就是天地的特性,心卻不同于生物本身的特性而是具有道德意義的詞語,這二者之間又需要可以聯系起來的橋梁。從傳統儒家一貫的傳統以及他的哲學理路來看,以宇宙觀作為其道德觀的價值來源,是他必然的選擇,“與天地不相似,則違道也遠矣”[11]35。可見,張載之道是來自于天地本身,其價值根基從天地之特性演化而來。他認為天地所行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教法,可以作為“至教”,“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11]35。
因此,對于天地而言,其德為生生;對于人而言,其德為生生之德,為善。從存在論上說,惡并不促進人之生,恰恰是善促進人之生,所以,依據天心的生生之德,人也應該展現出與天地不斷創生一樣的向上的特質,這種特質就是人道所立的基礎,即生生之善——“仁”。“生”與“仁”的這種聯系也為諸多思想家承認,如“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為天地立心,仁也”[5]。戴震在《原善》中說:“生生者仁乎!”[12]馬一浮也認為“天地之心于何見之? 于人心一念之善見之”[13]。
為天地立心,就是使人持“仁”而立,擇善道而從。這種善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善行,而是使人依據天地之生所選擇使人能夠真正發展自己正確價值的善,為人道奠定價值根基。“夫人心至是,幾不立矣,知人心便知天地心。自先生斯言出,舉凡人心皆有以自持,其不至于高卑易位,東西易面者,胥由之矣。是天地之心無能自立,先生為之立之也。”[14]在張載看來,“儒者應該肩負起為社會確立以善為核心的道德文化價值的歷史使命,心中始終想著如何能弘道于天下,而不是斤斤計較個人的得失和安危”[15],立定人道價值基石,方能開拓人之社會理想,此所以為天地立心。
二、 正人路——義立生民之命
人道已立,則人所向何方、所行何處便是張載構建“理想國”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這也是基于對當時現實問題的回應。佛教尚空,無禮無義,人們行無所據,難以真正的安身立命。他從氣一元論出發,分人性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從宇宙論上說明人們把握命運的可能——氣之變動不居順理而不妄,因此人于后天可以窮理盡性、變化氣質。與生生之德的人道相對應,仁之所處當義以行之。為生民立命實為以義立生民之命,確立人之當行之路,使萬千生民皆有安身立命之本。
“生民”與“立命”都出于傳統儒家典籍,但張載賦予了其新的哲學含義。“生民”是人民的意思,《尚書·畢命》載:“道洽政治,澤潤生民。”[16]《詩經·生民》載:“厥初生民,時維姜嫄。”[17]“命”在傳統儒家文獻里也不少出現,但較早完整論述的應屬孟子。孟子將命分為正命與非正命。在孟子看來,人之不能為者為天,不能致者為命。他說:“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18]所以,命無能為不能為,而有正與不正。正其命,就是順承天之所命,正道行之。非正命,就是自己招致禍端。朱熹解道:“人物之生,吉兇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19]馮友蘭對這一句也解釋說:“此整個的環境中,有絕大的部分,不是他的才及力所能創造,亦非他的才及力所能改變……是就其非才及力所能創造及改變說。”[20]正其命,就是孟子的“立命”。所謂立命,就是把握命運的方向,這種把握,是指人在自己能力范圍之內以當下的作為來為未知命運定向。孟子言桎梏、言非正命都與存心養性、盡其道對舉而言,其實存心養性即修身以俟,二者并列同一,所謂事天就是立命。換句話說,對孟子而言,存心養性、集義盡道都是“立命”的工夫。而立命,實質就是盡其所性的德性之命,張載正是在此基礎上闡釋自己的“立命”說的。
他繼承了孟子的德性之命說,但二者人性論的出發點不同,孟子從四善端出發談德性之命,而張載依據天人之性與氣質之性,將命分為“氣命”與“德命”[21]。張載說:“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其言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其言理也。”[11]23意思是“以天或天道為根源的命運屬于‘德命’,以生理和惡俗等因素為根源的命運則屬于‘氣命’或‘德命’”[22]。人要盡力窮理盡性,以德勝氣。而這種變化的依據又是來自氣的變動不居,“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涂,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11]7。所以,人就可以順氣之理來“變化氣質”。
“德命”是為人可以把握的,也是人所當行的。張載說:“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于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11]311“求在我者”的道義,就是“德命”,而這種“德命”正是通過“義”來體認和證成的。對張載來說也是如此,人應當之路正是在以“仁”為根底的人的價值根據上作出來的,“義,仁之動也,流于義者于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于仁者于義或害”[11]34。生民之命就是所說的大義,“義公天下之利”[11]72。富貴福澤之所以能厚吾之生,就在于此生為德性之善,所以為厚;貧賤憂戚之所以能庸玉汝于成,就在于此等患難更能砥礪德行而以德勝氣。所以存吾順事,存義而順性命之正;沒吾寧也,是盡義而心有所安。張載提出為生民立命,正是要萬千生民在禍福難測、人世無常的命運中,以“義”確立道德價值方向,以“義”來安身立命,以“義”來確立人之應當之路,從而掌控自己的命運,賦予生活以意義。
三、 開人智——智繼往圣絕學
繼立人心、正人路之后,張載構建“理想國”的第三步是開人智,這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辟佛破妄,使人自信自足;二是復興儒學道統,開啟人的生命智慧;三是開發智識,使人勇于為學。如此則人們能夠擔負起道統復興和文化傳承的歷史使命,弘揚和光大人道,為往圣繼絕學。
當時諸多思想家都認為,儒學失落,道喪已久。張載認為,既然能夠使人所知,那么道就有存在和重新喚起的合理性。而往圣絕學之所以不得傳,正在于佛氏之盛而此學者鮮少。所以培育學者,昌明此學便是其使命。但是昌明此學并不容易,因為當時佛氏之說遍布大江南北,“至今薄海內外,宗古立社,念佛之聲洋洋乎盈耳”[23]。這使得社會人倫無序無禮,“甌越之民,僧俗相半,溺于信奉,忘序尊卑”[24],迷信泛濫,“宋代統治階級極力推進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從而促使了封建迷信的泛濫”[25]。溺于信奉在很大程度上轉移了人們對現實生活苦難的關注,從而缺乏了改造現實的動力,更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們的痛苦,于國民生計無益。人倫無序、迷信盛行,加之民生艱難,佛氏無力于此現實生活的改善,無法振奮人之改造精神,都使得張載決意辟佛破妄。
辟佛當以儒學為基,張載從哲學理論高度上來批佛。一是批評佛氏以空論性使人無所立。他意識到,佛氏不立天而以心法起滅天地,是本末倒置。如此,現世虛妄則人無所自立。不難看出,在崇尚性空的背后,是人的現實生活與主體性的退場,“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夏蟲疑冰,以其不識”[11]26。只有立天與性,從現實的人出發,才能使人實際的認識自身之性,從而拓開內在的生命智慧。“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11]63牟宗三對此解道:“清通太虛落實于個體生命即為性,此謂張橫渠之天地之性,也即吾人性體之根源,故萬物一源、寂然不動、感而遂通。”[26]二是批評佛氏不明人倫無序無禮使人無所據,不察庶物空談自誤,使人無所學,“因謂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圣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11]64。他在氣一元論的宇宙論基礎上闡發了人們認識的可能性以及為學的路徑,把人性結構分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指出人們的惡來源于氣質之性,而氣質之性是可以通過學習改變的。這種對人性的解釋批判了佛家的輪回說,使命定理論逐漸瓦解。人們的注意力開始專注在力所能及的現實改變中,“性猶有氣之惡者為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于齊,強學以勝其氣習”[11]329-330。
張載所以基于儒學辟佛破妄正在于佛氏之學不僅有違儒家傳統的剛健有為精神亦使人無法擔負起人世的責任與義務,而他昌明此學就是要使人能夠自立自足,以此拓開人內在的生命智慧,啟發人的智識,以此現世之“實”來破來世之“虛”,以此奮發變化氣質來克生活之艱難困苦,使人能夠在現實的社會中挺立起來——于社會責任中提升人自身的價值和意義。智繼往圣絕學既是張載對自己一生奮斗的寫照,也是對人們擔負道統復興與文化傳承的殷切期望,更使人的本質得以還原先秦儒學的原生血脈——人必定的處在一系列的人倫秩序之中,因此,對于家國責任,我們責無旁貸,而這也是他在第四句話中所要展現的。
四、 理想國——為萬世開太平
“為萬世開太平”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秩序以及如何重建這個社會的秩序問題。《西銘》描繪了這樣一副社會藍圖,其具體的實踐措施則在張載“復三代之禮”的思想中得以體現。對張載而言,“禮”就是秩序的象征,“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12]。道德教育之禮在重建人們內心和行為的道德秩序,而“三代之禮”則是為了重建社會綱常與道德規范的秩序。但是“三代之禮”遠離張載的時代千年之久,為何張載一定要效仿“三代之禮”呢?他所效仿的“三代之禮”到底在哪些地方可以作為他的政治實踐方案?
張載所要恢復的“三代之治”并不是一般意義上對一個朝代制度的完全重復與復制,而是價值理念意義上的因時損益。“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11]262這種因時損益的特質與他的氣之變動不居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時損益就是體會其“精義入神”,得其“真義理”。這種“真義理”則是通過對“禮”的本質的認識而把握的。“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如何可變!……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11]293對他來說,天地之禮是“天敘天秩”,自然而不假于人,其表現便是“尊卑大小之象”。這種天然的秩序是出自其事物本質的內在規定。當我們把握其“真義理”的時候,不僅要看到它外在的這種變化,更要把握其中不變的東西。《西銘》中描繪的相親相愛的道德和諧畫卷,正是在張載天地之禮的本質規定下的應然的社會狀態,這也就是他所說的“萬世太平”。合內外之道就是既要有理想的應然圖景,更要有為之能“開”的可行之策。
“漸復三代之治”的治理之策便是“開萬世太平”之路,即恢復井田、重建封建、恢復肉刑。前兩條措施許多學者對此持批評態度,認為張載之策沒多少可行性。不僅王安石對此不置可否,就連朱熹在與弟子們討論時也說:“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后,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予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后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27]通過張載自身的實踐看來,此法確實很難實行,呂大臨在張載行狀中也說“此皆有志未就”[11]384。但是很明顯,張載并不是憑空杜撰出這樣令人難以理解的政策來,實質上,他是基于當時的社會現狀而提出這樣的對策的。
當時人民貧苦,國家積弱。北宋不立田制,允許土地自由交易,《宋史》記載:“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為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刬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后或兇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為薄。”[28]因此,土地兼并嚴重,從而造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局面。如馬端臨說:“自漢以來,民得以自買賣田土矣。蓋自秦開阡陌之后,田即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貴者可得之,富者有貲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屬役于富貴者也。”[29]民因此流離失所,生計艱難。“恰則炎炎未百年,今看枯柳著疏蟬。莊田置后頻移主,書畫殘來亦賣錢。春日有花開廢圃,歲時無酒滴荒阡。朱門從古多如此,想見魂歸也愴然”[30]。
抑制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使人民生計自足,便成為當政者的首要任務,也被眾多思想家所關注。如慶歷新政時范仲淹就在《答手詔條陳十事》建議“均公田”。他認為,建國之初,民生凋敝,士人之家依靠國家俸祿可以自給自足,等到安定多年物價上漲,俸祿不繼,士人家生存問題便日益顯現,于是便有人行侵民占田之舉。土地私相交易,而徭役不均,受損害最大者無疑是貧弱百姓。“在天下物貴之后,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于守選、待缺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茍朝夕。得官之后,必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貸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31]
因此,均平田地,縮小貧富差距,從根源上為百姓解決生存問題,使其自足,為國家開源節流、振奮武備,便是張載提出治理之策的出發點,而“恢復井田”自然首當其沖,“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11]212。基本的民生與民計才是張載井田之策的出發點,貧富不均是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所謂‘井田’,就是改變土地占有方式,并非改變原來土地占有制度,只是在封建土地制度下,抑制土地兼并,為土地占有不均做些調整”[32]152。張載認為田地上的均平需要政治制度的支撐,這種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上的,“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11]259。保證朝廷有世臣,在于確立“宗子之法”,但是宗子之法不是一個家族所宗,而是以國為家之宗,作為家庭的“宗子之法”僅僅是一種個人德性,而作為國家的“宗子之法”則上升為保家衛國,“在張載看來,僅僅依靠個人內在德性的忠義是不夠的,還需要將國運與家世聯系起來”[33]150。于此我們可以看到張載之所以提出恢復井田與封建的真正緣由:一般意義上的家與國并沒有在人們的情感中建立起一種于家一樣的親密聯系,而以國為家,在宗法意義上來建構的家國一體才能真正喚起人們的家國情懷和擔當意識。這也正如學者李蕉[34]指出的,張載是在人民之利的層面來思考問題,其意在“公天下”。張載之所以將封建制視作治國政體的最佳選擇,是因為他認同“封建制度”中所內蘊的“公天下”價值追求。張載意識到“公天下”才能充分調動政體中各個階層的積極性,從而提高治國效率。兼顧“公”“私”利益平衡,尤其注重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新的時勢下封建制有可能復興。
結 語
“橫渠四句”是張載在面對時代之問時做出的積極的、正面的、強力的儒者式回應,正如張立文指出的,“宋明理學家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職志;以建構倫理價值本體,給出安身立命、精神家園為標的;以格物致知、修養心性、自利自律、存理去欲為工夫。他們是當時的社會脊梁和社會良知的擔當者,是時代精神和價值理想的創造者”[32]3。它不僅涵蓋了張載對現實問題的回應,同時也內蘊著對理想國度的追求。所謂“理想”之意味是在應然狀態而言的,而前置的每一個動詞,又將這種理想轉變為一代儒者的艱苦實踐和不懈努力:責任之在我也,當仁不讓于師!
時值儒學式微與文明危機,現有的儒學自此無法解決人們安身立命的問題,也無法解決人們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佛學以其形而上的信仰構建的報應說、輪回說雖然吸引著人們,但是佛學尚空,在亂世之中逃避社會責任,這一點與自古以來儒家士大夫的擔當精神格格不入,也無法真切的有力的解決人們的苦痛和迷惘。先秦儒家的學說缺乏形上理論性深度的說明,董仲舒的神學倫理學在封建王朝的更迭中也完全被淹沒,玄學儒學則趨向順其自然,這一切的學說,都無法對現實問題給予非常有力的回應,并不是真正的解決問題之道。
在此情形下,張載意識到必須建立和恢復正常的秩序,重建人們的價值信仰,使人們行有所據。《西銘》實質上是其道德理想的政治實踐表達,是他道德理想的基本藍圖。他將家和國緊密地聯系起來,使宗法關系由舊有的血緣政治結構變作了哲學本體論,觀念上的宗法想象變成了維系社會秩序的一條紐帶,從而使人們開始覺醒一種家國意識和擔當意識,這使得天下在理論意義上成為一家,各個階層擁有了理論上的血緣關系,從而給了家國另一種意義上的聯系。“這表明張載巧妙地彌合了經學與時政之間的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而大得士人的歡心,傳統的修齊治平獲得了新的社會格局的支持,本屬于先秦社會的親親與尊尊的社會秩序也因此而獲得了新的落腳點,毫無皇族血緣的士大夫階層也由此而重續了血統,和皇族攀上了親戚,變成了孟子所謂的‘貴戚之卿’,自然也承擔起‘貴戚之卿’而非‘異性之卿’所當承擔的責任,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便自然具備了扎實的理論基礎,這便是宋代知識分子對時政之擔當精神的一個出處。”[35]
而“橫渠四句”則是“理想國”具體的建構路徑。重建人在天地的地位,立定人道的價值根基,此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是對綱常無序、道德規范失調做出的回應,義以立命,是使人有所立,正路有所行。為往圣繼絕學,是他意識到儒學式微危機做出的回應,智繼往圣絕學,是使人能夠安頓身心與精神信仰。為萬世開太平是他的天下大同道德理想的政治實踐。我們不必苛求一個哲學家能如一個政治家抑或王安石、張居正一樣提出具體可操作的政治改革措施,但我們卻可從其中管窺其宏大無私的政治價值指向:他重視民生,力求使民自足而不為盜;力求均平,使耕者有其田不為貧不為亂;他教人變化氣質,使民自信,天下可治,仁德可昌。
張載的道德理想是一個哲學家對一種完美社會的理想和向往的認真思考,同時也反映著他對現實問題的強烈關注。“北宋道學雖然關注北宋王朝具體的政治實踐和操作,但更為核心的關切仍在于理想人間秩序的形而上學基礎的建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達成理想人間秩序的根本途徑上,道學家更強調的是禮樂和風俗的重建,而非王安石在熙寧變法中嘗試的政治制度的變革。”[33]142在這一意義上,他的道德理想更多的指向的不是具體的政治實踐,而是政治實踐背后的正義性質。他以嶄新的理論形態重新闡釋了人和天地、人和社會的關系。此心安處是吾鄉,于中國人的心中所安,正是“橫渠四句”所喚起的在“公天下”理念之下的一個民族的家國情懷和擔當意識,為其傳人呂大鈞等“堅持用儒家治世理念求得國家的穩定”,“將禮學思想融入社會實踐中去”[36]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