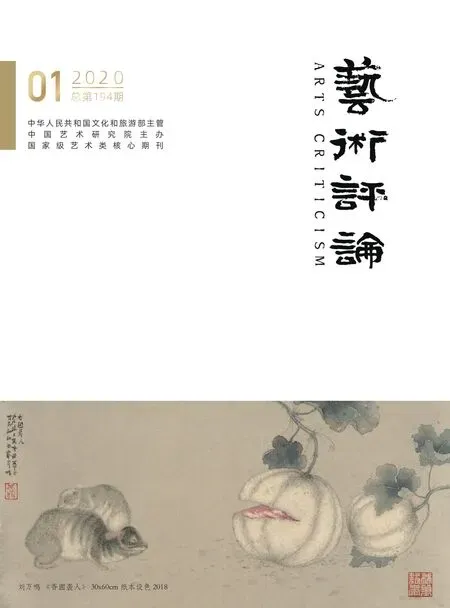“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
——上海芭蕾舞團芭蕾舞劇《茶花女》觀后
于 平
【內容提要】芭蕾舞劇《茶花女》進入上海芭蕾舞團的劇庫,是上海芭蕾舞團為建團40周年所做的一個重要舉措。用團長辛麗麗的話來說,“這是海派芭蕾專業(yè)化、國際化、市場化的充分體現(xiàn)”。該劇由芭蕾舞劇《哈姆雷特》的英籍編導德里克·迪恩創(chuàng)編,全劇充滿了激情、陰謀、背叛與愛,其故事背景具有強烈的戲劇感和層次性。舞劇按上、下兩個半場分為兩幕,兩幕之間是由瑪格麗特(即“茶花女”)的主觀視角來展開的,從而使整部舞劇呈現(xiàn)為一部“心理現(xiàn)實主義芭蕾”。不僅如此,編導迪恩專注于獨特創(chuàng)作技法的運用、敘事節(jié)奏的把握以及形式感的建構,既塑造了阿爾芒注重細節(jié)、乃至拘泥于細節(jié)的性格,又輔助了中國觀眾認知瑪格麗特的善良、純潔和心性的崇高。
當鮑里斯·艾夫曼的“心理舞劇”近年來在中國掀起一陣舞劇風暴之時,我就說過上海芭蕾舞團(下稱“上芭”)委約帕特里克·德·巴納創(chuàng)編的芭蕾舞劇《簡·愛》無論是從對原著的提煉、舞劇結構的構思,還是編舞理念的呈現(xiàn)都不輸于艾夫曼的《安娜·卡列尼娜》。不久前,當我應上芭團長辛麗麗之邀觀看該團新近委約創(chuàng)編的舞劇《茶花女》之時,我同樣覺得該劇亦呈現(xiàn)為特立獨行于“艾夫曼舞劇”之外的追求——就對歐洲文學經(jīng)典的改編而言,上芭近年來的委約創(chuàng)編使我們對艾夫曼認識得更為客觀一些——艾夫曼只是當今優(yōu)秀芭蕾編導中的一員,并且他所有的舞劇作品并非都足夠的優(yōu)秀。如果我們把德里克·迪恩先后為上芭創(chuàng)編的《哈姆雷特》《茶花女》與艾夫曼改編自俄國文學經(jīng)典的《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馬佐夫兄弟》進行比較的話,就知道我們的前述判斷“此言不謬”。
一、“海派芭蕾”專業(yè)化、國際化、市場化的充分體現(xiàn)
芭蕾舞劇《茶花女》進入上芭的“劇庫”,是上芭為建團40周年所做的一個重要舉措。用團長辛麗麗的話來說,“這是海派芭蕾專業(yè)化、國際化、市場化的充分體現(xiàn)”。實際上,這可以視為上芭近十年來的創(chuàng)意追求和審美定位——從最初的《簡·愛》《哈姆雷特》到當前的《茶花女》都是如此。我們大可不必細究“海派芭蕾”的內涵,只把它理解為辛麗麗和她領導的上芭力圖形成舞團的藝術風格,并向“學派”挺進的核心理念;而結合著“專業(yè)化”“國際化”來談“市場化”,本身就是“海派舞蹈”特有的取向。這個“市場化”顯然面對的是一個高端的市場——想想艾夫曼領導的舞團在中國火爆的市場,你就能理解辛麗麗“市場化”的取向。
這一次,辛麗麗還是請出了在芭蕾舞劇《哈姆雷特》創(chuàng)編中口碑極佳的德里克·迪恩。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將英國文學經(jīng)典《簡·愛》改編為同名舞劇的巴納是德籍編導,而身為英籍編導的迪恩,這次要改編的是法國文學經(jīng)典《茶花女》。為什么是《茶花女》?現(xiàn)在已擔任上芭藝術總監(jiān)的迪恩說:“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故事,充滿了激情、陰謀、背叛。最重要的,它也充滿了愛——這種具有強烈的戲劇感、層次性的故事背景對編導來說是夢寐以求的,因此我們創(chuàng)作了它。”實際上,迪恩或許還有潛在的渴望,即世界上有許多個著名的芭蕾舞團創(chuàng)排過此劇,特別是時任漢堡芭蕾舞團藝術總監(jiān)約翰·諾伊梅爾為瑪茜西·海蒂度身定制的版本(首演于1978年)。迪恩或許渴望在四十余年后做一次更為獨到的解讀——為自己、為上芭,也為他一眼選中的上芭舞者戚冰雪!
二、迪恩的創(chuàng)編可稱為“心理現(xiàn)實主義芭蕾”
舞劇按上、下兩個半場分為兩幕,兩幕之間是由瑪格麗特(即“茶花女”)的主觀視角展開的。由舞劇首席主觀視角來展開劇情,現(xiàn)在往往被視為“心理描寫”的舞劇。艾夫曼的舞劇《柴可夫斯基》就是這樣展開的,以至于他直呼自己的舞劇作品為“心理芭蕾”。“心理芭蕾”或者“心理描寫”的舞劇當然也可以用“順敘”的方式娓娓道來,只是“倒敘”的方式對于首席人生歷程的展開會體現(xiàn)出更清晰的軌跡——因為這是主人公對已然人生的追溯,必然包含著對那種“已然”,特別是“已然”中“無奈命運”的反思。如同艾夫曼的舞劇《柴可夫斯基》是從躺在靈床上的柴可夫斯基逐漸消失的意識中升騰起人生的幻想啟程的,迪恩的《茶花女》也是從病榻之上處于彌留之際的瑪格麗特的幻覺開始的——這時的舞臺在并無刻意分隔的空間中呈現(xiàn)為兩個區(qū)域:一個是位于下場門前區(qū)的那張病榻,病榻兩側是體現(xiàn)瑪格麗特“彌留之際”的醫(yī)生和女傭;另一個便是除此之外的整個舞臺空間。舞劇后來的敘述告訴我們,在這個瑪格麗特意識外化的空間,她看見了自己的葬禮——葬禮的隊伍從上場門后區(qū)緩緩而行,自己摯愛的阿爾芒終于到來。于是她不顧一切地從病榻上爬起追去,卻見那曾經(jīng)為她提供經(jīng)濟來源的公爵不斷地將阿爾芒推開,直至消失。與舞劇《柴可夫斯基》的幻想啟程不同,這個“意識外化”的空間很現(xiàn)實,是一個極其真切平實的生活場景;同時,這個場景卻道破了瑪格麗特悲劇人生沖突的起點。讓公爵而非阿爾芒的父親推開阿爾芒,說明迪恩并不急于吐露這個悲劇的根源——這個根源其實在于阿爾芒的父親要求瑪格麗特寫給阿爾芒的分手信!
現(xiàn)在,舞劇要使病榻上的瑪格麗特進入自己“幻覺”中的現(xiàn)場了——幻影般的天使要將她帶去天國。在她最后對塵世的依戀中,一個鏡框緩緩垂下,鄰居普呂當斯和女傭在這個穿衣鏡前為瑪格麗特換上盛裝。當垂下的鏡框再度升起時,瑪格麗特已置身于當年的巴黎社交圈了。看著迪恩的《茶花女》,我會想起他三年前為上芭創(chuàng)編的《哈姆雷特》。迪恩的這兩部舞劇的確都重視人物的心理刻畫,只是這種“心理刻畫”并非隨著人物意識的隨性流動而任意飄浮,而是兼顧著情節(jié)的客觀敘述,甚至還十分看重細節(jié)的真實。比如作為瑪格麗特遇到阿爾芒之前的鋪墊,在舞會的場面消散后,一位年邁的公爵、一位中年的男爵以及年輕的蓋斯頓爭相以錢財禮物、甜言蜜語來博取瑪格麗特的好感。普呂當斯和女傭亦忙不迭地幫著瑪格麗特應酬。這種以三位個性迥異的男士組成有合有分的“小群舞”,以及瑪格麗特時而融入其中,時而又回到普呂當斯和女傭身邊舞動,在舞會的社交舞和此后瑪格麗特與阿爾芒的“相遇舞”之間,成為一個恰到好處的過渡,體現(xiàn)出原著所說的“巴黎的貴族公子紛紛拜倒在瑪格麗特的裙擺之下”的“細節(jié)真實”[1]——在這個意義上,我倒愿意視迪恩的創(chuàng)編為“心理現(xiàn)實主義芭蕾”!

《茶花女》劇照 攝影:陳倫勛

《茶花女》劇照 攝影:祖忠人
三、“臺中臺”演繹極具象征意味的“戲中戲”
瑪格麗特第一次見到阿爾芒是在上述“小群舞”之后,他由年輕的蓋斯頓引見。只是帶著甜點來向瑪格麗特示愛的阿爾芒,讓瑪格麗特覺得他固然清純但過于稚嫩。此時,舞臺場景從“舞會”瞬間轉換到“劇院”,目的是盡快使兩人的愛情熱度升溫——舞臺底部天幕前是“劇院的舞臺”,瑪格麗特和阿爾芒分別坐在舞臺前區(qū)兩側的“包廂”中。“觀劇”期間,兩人離開各自的包廂在舞臺前區(qū)中央相聚,表現(xiàn)出阿爾芒對瑪格麗特的狂熱追求以及后者對前者的真誠接納。而這時,“臺中臺”演出的是芭蕾舞劇《吉賽爾》的片斷——已成為“鬼魂”的吉賽爾以德報怨,將那個玩弄自己情感、從而使自己離開人世的阿爾伯特從幽靈的世界中救助出來。很顯然,這個“臺中臺”演出的“戲中戲”極具象征意味,它仿佛預兆出瑪格麗特與阿爾芒的愛情結局,當然也預兆了瑪格麗特的悲劇人生。40年前諾伊梅爾的版本中,在那部三幕舞劇的第一幕也有這樣一出“戲中戲”,只是諾伊梅爾版本的“戲中戲”是《曼儂》。那出戲對于劇中瑪格麗特而言只是情感態(tài)度的一個借喻——瑪格麗特不齒于曼儂的輕浮不忠,由此引出在蓋斯頓引見下來到瑪格麗特身邊的阿爾芒。迪恩將這種“戲中戲”的功能由“借喻”改變?yōu)椤跋笳鳌保瑥亩鴱娀嗽搫 耙缘聢笤埂钡闹黝}。
我想起了坊間的一則傳聞:寫下不朽文學經(jīng)典《茶花女》的小仲馬,是以《基督山伯爵》《三個火槍手》等作聞名于世的大仲馬的兒子。當小仲馬因《茶花女》一舉成名,大仲馬作為父親顯得極為興奮。頗有自知之明的小仲馬盛贊父親的作品《基督山伯爵》,而大仲馬回應兒子的是:“我最好的作品是你!”初聞之時并未細想這則傳聞的意義,現(xiàn)在似乎有點感悟:我在初讀《基督山伯爵》時,該書書名被譯為《基督山恩仇記》,講的是愛德蒙·鄧蒂斯從死亡之境復活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故事——這顯然是大仲馬的“正義觀”。當他對小仲馬說“我最好的作品是你”之時,他應該是認同《茶花女》的價值取向,即瑪格麗特對阿爾芒的“以德報怨”——這是大仲馬對自己既往“正義觀”的反思。諸多芭蕾大師一再審慎地去改編小仲馬的《茶花女》,應該首先是認同這種以“隱忍”示“大愛”的價值取向;至于那些頂尖的芭蕾女星都以挑戰(zhàn)這個復雜的角色為榮,是因為瑪格麗特欲愛不能、銜悲亦難恨的表演挑戰(zhàn)著芭蕾既有的美學風格。
四、“瑪格麗特”的形象塑造爐火純青、出神入化
當瑪格麗特發(fā)現(xiàn)自己真心愛上了阿爾芒,編導迪恩并沒有如通常舞劇那樣迅速展開“大雙人舞”,而是迅速推進情節(jié),將空間從巴黎的豪華客廳轉換到鄉(xiāng)間的樸素小屋。按照諾伊梅爾的版本,這座鄉(xiāng)間小屋是瑪格麗特用公爵提供的經(jīng)濟來源購置的;而按照小仲馬的原著,公爵的施舍是因為瑪格麗特很像自己因肺病去世的女兒。其實,舞劇很難講清公爵提供經(jīng)濟援助的前提是瑪格麗特必須改變原先在巴黎社交圈的生活,而這是瑪格麗特希望阿爾芒不向外公開兩人戀情的緣由。迪恩認為舞劇的這一空間轉換就舞劇敘事而言重在強調兩點:一是阿爾芒對瑪格麗特身體(也是肺病)無微不至的關心;二是阿爾芒的父親懇請瑪格麗特離開自己的兒子而逼其簽署的分手信。在鄉(xiāng)間的拮據(jù)生活中,瑪格麗特變賣自己的首飾來維持兩人的生活,而阿爾芒則希望處理好一筆遺產來幫助瑪格麗特——當然這都是場刊上的提示。上半場這一幕的終結,就是瑪格麗特無奈簽署分手信后,看著阿爾芒的父親帶著分手信離開而痛悔不已的情景。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編導迪恩的敘事節(jié)奏:首先,他一方面注重細節(jié),一方面又省略細節(jié)——他為了強調瑪格麗特的魅力而著力強化“巴黎的貴族公子紛紛拜倒在瑪格麗特裙擺之下”的細節(jié)真實,但同時他也淡化了為瑪格麗特提供經(jīng)濟援助的公爵在“動機”和“緣由”方面的細節(jié)真實。其次,他一方面把瑪格麗特墜入愛河而又欲愛不能極大地壓縮在第一幕中,一方面又在第二幕中鋪張出自認為成為巴黎社交圈新寵的奧琳普——這個擠占了瑪格麗特社交空間的奧琳普反襯出瑪格麗特為阿爾芒做出的犧牲;但另一個無奈簽署分手信的“犧牲”只能在瑪格麗特心中隱忍著,她甚至還要裝出“移情別戀”的假象。這使得迪恩在第二幕留出充裕的時空來敘述不知底里的阿爾芒對瑪格麗特的傷害,而且還要在瑪格麗特一再的隱忍中去表現(xiàn)一種極難表現(xiàn)的心理活動——那種欲說無言、欲哭無淚的心情!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上芭舞者戚冰雪在對瑪格麗特的形象塑造中,已經(jīng)達到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地。
五、在隱忍中彰顯人性的純粹與崇高
舞劇的第二幕中,除了如同一幕一樣以“舞會舞”來營造社交圈的理念外,“社交圈”的內涵已然發(fā)生改變:雖然自認為可以取代瑪格麗特的奧琳普大出風頭,但她的輕浮反倒更襯托出瑪格麗特的“憂郁”之美——實際上,這才是瑪格麗特人格美的本質所在。從鄉(xiāng)間回歸社交圈的瑪格麗特是挽著一位富商的手臂出現(xiàn)的,在沒有絲毫炫耀的表情下明顯有一種無以言表的悲哀。不知隱情的阿爾芒認定這是一種對于忠貞的背叛,是瑪格麗特水性楊花的本性,于是他接受奧琳普的邀舞并帶著對瑪格麗特不加掩飾的“侮辱”。但瑪格麗特之所以贏得了已知緣由的觀眾的認同,在于她真切地把這所有的“侮辱”當作阿爾芒“始終愛我的證據(jù)”!在我有限的視野中,雖然瑪格麗特的確有“身不由己”之處,但她的“以德報怨”卻在一種隱忍中彰顯出某種人性的純粹與崇高。這使我想起在作為“中國話劇元年”的1907年,我們確定《黑奴吁天錄》(即《湯姆叔叔的小屋》)作為中國話劇的“開山之作”時,其實同時也由李叔同男扮女妝“反串”了《茶花女》。但顯然,當時更需要的是“抗爭”,而非“隱忍”;是階級的對抗,而非人性的和解。

《茶花女》劇照 攝影:760 studio

《茶花女》劇照 攝影:陳倫勛
其實瑪格麗特也希望與阿爾芒和解,但難題是她一方面要信守對阿爾芒父親的承諾,一方面還要阿爾芒理解自己簽署的分手信。編導特意讓眾人遠去,舞臺上孤獨的瑪格麗特讓觀眾明白她已被社交圈冷落。看到向自己走來的阿爾芒,瑪格麗特不知該如何解釋,她只是一味地哀求——這段“大雙人舞”的創(chuàng)編的確難為編導:時而是瑪格麗特哀求絲毫不能感化阿爾芒的冷漠,時而是阿爾芒近乎冷酷地要求瑪格麗特放棄所有來以示誠意,時而是瑪格麗特應允阿爾芒的苛求時的孤注一擲,時而是阿爾芒虛情假意地答應與瑪格麗特和解……但誰知,當眾人重回舞臺(其實是阿爾芒領著瑪格麗特重回社交圈的中心),阿爾芒掏出由父親交給自己的“分手信”,狠狠地摔向瑪格麗特。這是瑪格麗特完全不曾預料的結局——即便她心中仍然相信“這種侮辱是你始終愛我的證據(jù)”,但誰又能對這種侮辱般的“愛”處之泰然呢?有些極端自私的愛情是施暴者與相愛對象同歸于盡,潛臺詞是“我得不到的,也不讓任何人得到”;但阿爾芒的侮辱極其卑劣,他的潛臺詞是“我看不上你,也要讓任何人都看不上你!”在這個意義上,真正導致瑪格麗特死亡的不是她多年不愈的肺病,而是阿爾芒已然幾乎變態(tài)的“侮辱”。
同樣用“舞會舞”來營造社交圈的敘事語境,第二幕明顯有別于第一幕的,是在底幕上方懸掛著一面闊大的堂鏡。在它的映照下,舞會顯得極其喧囂。阿爾芒不加掩飾的、不屑乃至鄙夷的神態(tài),是一波又一波刺透瑪格麗特心靈的侮辱。小仲馬在原著中寫了瑪格麗特為此而寫在日記中的一段話(這本日記在瑪格麗特死后由鄰居交給了阿爾芒):“除了你的侮辱是你始終愛我的證據(jù)外,我似乎覺得你越是折磨我,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你眼中也就會顯得愈加崇高。”芭蕾舞劇《茶花女》將原著中的這段話鄭重地印在場刊中,顯然是將其視為舞劇敘事所要揭示的主題。
六、上芭版《茶花女》對我們舞劇創(chuàng)編的有益啟示
諾伊梅爾版《茶花女》的序幕是瑪格麗特香消玉殞后的遺物拍賣:一個顯著的細節(jié)是女傭帶走了瑪格麗特的日記。而來參加拍賣的人之中有阿爾芒的父親;當阿爾芒失魂落魄地沖入現(xiàn)場,觀眾很難在第一時間想到他是得到并且閱讀了那本日記;此后進入的舞劇敘事似乎是阿爾芒回憶的倒敘。由阿爾芒的回憶來展開舞劇敘述,從客觀事理來說當然是正確的——誰見過一個彌留之際的人能如此深切地傾訴衷腸?并且又有誰能如此細膩地傳達這種傾訴呢?迪恩創(chuàng)編的版本從病榻上彌留之際的瑪格麗特的幻覺開始敘述,并非迎合芭蕾舞劇近年來“心理描述”的時髦,而是堅定地要用瑪格麗特的主觀視角來敘述——這將比阿爾芒借“回憶”當“懺悔”的立意更崇高,也會真正實現(xiàn)瑪格麗特留在日記中的心愿:“我在你眼中就會顯得愈加崇高。”
上芭版《茶花女》如同該團近年來推出的《簡·愛》《哈姆雷特》一樣,每次都會在舞劇創(chuàng)編的表意理念和敘事策略上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第一,提煉并牢牢把握住舞劇的主題立意是重要的,但以何種敘述方式才能更準確地凸顯主題立意,也需要審慎地斟酌。比如上芭版《茶花女》確定以瑪格麗特的主觀視角來進行敘述,對于瑪格麗特的心聲——“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你眼中也會顯得愈加崇高”這一主旨會有更為真摯和深邃的表現(xiàn)。第二,在確定主觀視角后,特別是這一“主觀視角”是舞劇第一首席(相對于該劇的“男首席”而言)的視角時,就要縝密安頓好第一首席的視角及其行動之間轉換關系。在某種意義上,這有點近似于文學作品寫作時第三人稱客觀描述和作家夾敘夾議的關系。這種舞劇敘事方式可以更清晰地表述好主題立意,但處理失當則可能使舞劇敘事或失之于淺白,或失之于澀滯。上芭版《茶花女》可以說是恰到好處地安頓好了二者的關系。
接下來是舞劇如何在服從、服務于主題立意的敘述中建立自己獨特的形式感的問題。諾伊梅爾的版本由三幕構成,場景分別是巴黎的奢華劇院、瑪格麗特的鄉(xiāng)間寓所和一個混雜著香榭麗舍大街、盛大年會、奢華劇院的場景。三幕中這個混雜的場景表現(xiàn)的是阿爾芒瑣碎而雜亂的記憶,但似乎并沒有能緊扣住“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的主旨。迪恩的版本由兩幕構成,雖然第一幕的場景也比較混雜,有舞會、劇院、鄉(xiāng)間小屋,但迪恩的用意很明顯:瑪格麗特如何紅極一時,阿爾芒如何進入瑪格麗特的視野,兩人如何墜入愛河,瑪格麗特如何無奈地簽署分手信……這一切只需一筆帶過;而第二幕之所以把場景鎖定在一個盛大的舞會,是因為在此展開的全部敘述都是瑪格麗特永遠無法釋懷的心結——面對阿爾芒毫不節(jié)制的侮辱和折磨,瑪格麗特只有一個信念,即“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這有點像許多冤案中的主人公“以一死來證實自己的清白”。瑪格麗特期待的仍然是在阿爾芒眼中“顯得愈加崇高”!
為了使這兩幕構成獨特的“形式感”,除了以天使對瑪格麗特的召喚首尾呼應外,兩幕以“舞會舞”來營造社交圈的理念:只是在第二幕由懸掛的堂鏡映照出的“鏡像”似乎更強化了“心象”的隱喻——強化了瑪格麗特主觀視角中的離群念想和淡出意識。而從第一幕啟始時天使對其召喚時的依戀塵世,到第二幕終結時順從地追隨天使的召喚步入天堂,也在首尾呼應中體現(xiàn)了瑪格麗特的至善人性和至美人性。在瑪格麗特最初“幻覺”的送葬隊伍中,終于來到自己跟前(盡管是人天兩隔)的阿爾芒手捧著一束白山茶花;而在瑪格麗特順從天使的召喚步入天堂之時,天幕的一側也有擴放的白山茶花軟景。我們知道,瑪格麗特之所以被稱為“茶花女”,是因為她隨身的裝扮總是少不了一束白茶花。如果在劇中對這一細節(jié)加以適當?shù)貜娬{——比如在群富以炫富之舉爭寵于瑪格麗特之時,阿爾芒精心送來的便是一束白山茶花。這不僅對于強調阿爾芒注重細節(jié)、乃至拘泥于細節(jié)的性格十分得體,而且對幫助中國觀眾認知瑪格麗特的善良、純潔和心性的崇高也是大有裨益的。
【注 釋】
[1]舞劇《哈姆雷特》也十分強調“細節(jié)真實”,參見于平.莎翁的精粹 哈氏的魂——原創(chuàng)芭蕾舞劇《哈姆雷特》觀后[J].舞蹈,2017(7):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