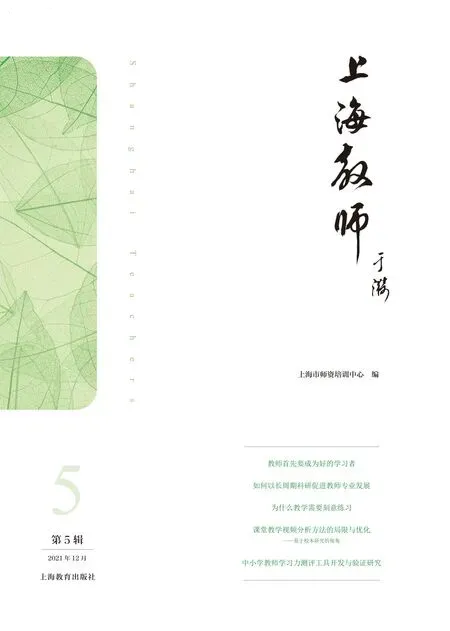如何以長周期科研促進教師專業發展①
顧泠沅
(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 上海 200032)
一、老的話題遇到了新的時代
我認為現在是老的話題遇到了新的時代。這是我想說的第一句話。
最近我看報紙,相信大家都關注過兩個問題,其實都是老問題。
一個問題是減輕學生學業負擔。這是個敏感的話題,也是個老問題。20世紀60年代,毛主席就號召要減輕學生的過度的負擔。1964年到現在,57年了,這個老問題又引起了關注。兩個月前,我出席了一個教改座談會。我說這些年成績很多,不可否認。但說問題的話,有一句話反映了一個比較普遍的情況:不做作業,父慈子孝;一做作業,雞飛狗跳。我們搞了那么長時間的科研了,結果還是弄得雞飛狗跳。這是什么原因?今天論壇的主題是“長周期科研”,長周期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也是很早就講過,就是五育并舉。德智體美勞很早就提出來了,現在叫五育并舉。我最近碰到一個特級教師,她從“老掉牙”的小學課本里面讀到這么幾句話:貓會抓鼠,狗會看門;不會勞動,貓狗不如。我說,這幾句話有道理。孩子們四體不勤、不會勞動怎么行啊!我們搞的是人的教育啊!這是勞動教育的問題。現在從家庭到學校,分數競爭愈演愈烈,值不值得研究?是什么原因?有沒有育人理念的問題?
當前,很多任務已經提出來了,中央出臺了很多剛性文件,里面有很多剛性的東西。是怎樣,不準怎么樣,有多少時間的限制,多少量的限制,文件里都有。寫文件寫到了這個程度,我想大概是蠻緊迫的。這樣的關注抓住了要害,這些問題確實都還沒有解決。幾十年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在新時代要有勇氣去解決它們。
我最早做過教師進修學校的校長,主要搞教師教育。因為搞教師教育,我非常看重自己的這個崗位。我覺得學校要改革,教師是最重要的關鍵推動力。于漪老師說,教育質量說到底是教師的質量。7月下旬,我應邀回母校復旦大學參觀交流,談到中小學課程改革、創造力培養,大家干勁十足,涉及減輕負擔,卻有杯水車薪、救不了火的困惑,但所有人都同意教師重要的觀點。
蘇步青先生很早就說過,把教師的質量提高一點,這是教育改革的關鍵問題。今天這個論壇很重要,主題放在“科研與教師成長”的關系上,抓教師成長抓在點子上。而且現在正好是新的時代,就要著力解決這些問題。
現在,各位老師是不是還被叫老師?我聽說最近的文件里面提出全員導師制,那么,各位都是導師了。每位老師都是導師,就是人生的引導者,是不是這個意思?叫“導師”,和單純地叫“教師”,或者“我就是教書的”,這些叫法,內涵不一樣了。這些問題,我們有沒有課題去研究呢?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是時候研究這種深入的問題了。長周期的課題,是深刻的、能夠使我們的民族振興的重要課題。機遇擺在我們面前,有志于研究的老師要好好干這個事情。
我問主持人王老師:“你覺得科研管用嗎?”有的老師認為科研沒用,在中小學分數一定要提起來;搞科研,遠水救不了近火。這個看法不對,科研非常緊迫,我們要用科學的辦法分析和解決問題,哪怕不是徹底解決,哪怕只是使這些問題有一個解決的起步思路。
二、學校改革和教育科研需要守正創新
現在,學校改革和教育科研,也有一個守正創新的問題。這是我想說的第二句話。
科研是要創新的,創新要創在做老師的本分上。有一次我們在一所師范大學,討論基礎教育如何建成高地。當時,著名教育家呂型偉先生在現場一言不發,到最后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各位都說得很高很高,高大上。我是從低處走來的,高等教育追求科學技術高大上,是可以的;基礎教育往下走,深不可測,要追求所有人的素質都有所提高。”
如果我們搞教師教育的,只是想著搞出C刊發表的文章,恐怕不夠。我們還得堅持一條路,往下走,跟老師們一起走,哪怕解決一兩個具體問題,只要是有意義的真問題,其價值不一定就比寫出一篇C刊的文章低多少。我始終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不要忘記那一代人,其中還有徐匯區的趙憲初先生。趙憲初先生跟我說過一句話:“《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意思是,如果水積得很淺,那么要走大船是沒有指望的。然后他創造了一句話:“師之蘊也不足,則其育長才也無望。”我一直記到現在。教師的內蘊(現在也叫理念、信念、知識、技能、功力)不足的話,那么要培養高素質的人才,也是沒有指望的。
這句話說得多好!所以,科研有用嗎?我問你的這句話,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說,科研當然是有用的!
我的導師劉佛年先生,曾任華東師范大學校長。他說,現在最需要的是既懂得中小學教育,又肯從事教育科學研究的善于思考的人,與中小學教師結合起來,尋找一些有效的途徑。這是前輩教育家的重托。我們干了幾十年,任務有沒有完成?完成了一小步,并沒有多少貢獻。所以有人采訪我時,我說我們大概是屬于過渡的一代,這一代人大多70多歲了。令人欣慰的是,下一代的中青年才俊,已經形成了群體,他們的起點很高,任務更重。重要的是,搞好學校科研,一定要牢記前輩的重托。
此時此刻,我想說一說自己親歷的一個長周期課題。我曾跟隨呂型偉先生主持全國重點課題“面向未來的基礎學校”,遍及全國13個省市,貫穿1986至2011年。耳提面命25年,有一件事讓我無法忘懷,那是呂老到生命最后時日,我代表課題組去華東醫院病房向他作“最后的匯報”。當我說到,我們揣摩他關于學校教育的研究方法:第一,改革目標明確,路徑要靠大家創造的“摸石頭過河的實踐路線”。第二,石頭在哪里?看來要學點教育史、改革史和國內外的多種經驗,“用學習的力量避免盲目”。第三,最終怎么應對未來?這就是重要的第三條,“看懂現在就是面向未來”。我剛說完這三條,他突然從彌留中緩過神來說,這三句話的意思他都說過,它們是一個整體,不能割裂。他說完還想說,但渾身發抖,再也說不出話來。后來,醫生叫我們立馬離開,他到臨終還惦記著面向未來的基礎學校!
各位同行,如果我們冷靜看待自己的基礎教育,成就很大,問題也不少。我們有的時候很自信、很榮耀、很光鮮;有的時候,我們又很無奈,這個辦法不好解決,那樣做會遇到障礙。但是,所有這些東西,還得如同嚼甘蔗,哪怕是個困惑,哪怕是個焦慮,把它像嚼甘蔗一樣,嚼出汁水,吐掉它的雜質。哪些是雜質,哪些是汁水?分清楚了,那就是看懂了。而看懂現在,才能真正地面向未來。
三、今天教師怎樣做科研
這是我想說的第三句話。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作為中青年教師向于漪老師請教:“您怎么成為名師的?”她的話極簡單:“我上語文課,一篇課文三次備課,堅持三年一定成為好老師。”真話就這么簡單。這是一輩子學做教師的過程,過程里有周期性的循環。幾次循環,不斷改進,就越來越好。
在此基礎上,我們總結成教師在職研修的“三關注兩反思”經驗。第一個關注,是關注現有的自我經驗,自己備課,不要東張西望、抄來抄去,獨立鉆研,自己寫。第二個關注是向外學習,看別人的設計,比自己做得好的地方有沒有,差別在哪里。找到差別,理念就變了。第三個關注是落實到自己的課堂,看所教的班級與好的設計有沒有差距,還可做怎樣的行為調整。做好調整,學生才真有收獲。其實,三個關注之間就有理念更新與行為跟進這兩個不可或缺的反思支架。“三關注兩反思”建立在以課例為載體的合作平臺上,這樣的循環往復,彰顯了我國教研特有的組織文化和行動路線,深刻體現出中國特色教師專業化和源自“知行合一”認識論血脈的精華。
“教師成為有研究能力的實踐者”,一直是我們在培養優秀教師方面的期許和追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早些年,我們對骨干教師提出課堂現場觀察的要求,不放過每一堂課,即時即景,觀察其中的利弊得失,思索改進的各種方法,從中鍛煉教師的教學敏覺力,很有成效。但這種觀察有一定的局限性,常受信息不全的限制,有時時間一拖很容易遺忘。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引入信息技術,先是錄像帶,后來是視頻光盤,技術帶來了研究的突破。多角度的全息記錄,可以提取大量數據以供分析;回放、定格與“顯微”,可以考察一瞬即逝的細微行為(包括語言、動作與表情)。更為重要的是,教師“既是演員又是觀眾”的角色轉變,這最要害的一步,成就大批好教師有了便捷的途徑,大家不妨試一試。那時候,我剛從青浦調到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普陀區挑選了40位年輕教師要我指導。當時,我說院里工作忙得很,經常來不行,結果就用了這個辦法,不斷把自己和幾個人的課錄下來,自己看,幾個人討論,有些情境忘記了,重新再放一遍。一兩個月集中一次,哪些地方自己的教學不行,哪些地方有了轉變,哪些地方還需改進,大家一起說。這個指導歷時兩年多時間。現在他們有的成為校長,有的成為教研員,有的成為特級教師。其中有些人已近60歲了。回憶當年,大家都覺得這段經歷太重要了。這樣做培訓,不需要很多的講座。比如有位教師,某一句話重復太多,老是改不了;自己看錄像,發現“我怎么會這樣,講得這么多”,馬上改。
如今,不少教師正在成為基于證據的“循環改進者”。到了這一步,就是上海教研、科研中相當前衛的狀態了。課堂教學也好,現在的跨學科、項目學習、教師成為導師等也罷,你就用錄像機錄下來,看視頻,你是教師還是導師,一看就清楚了。其實視頻分析大大擴展了證據的多樣性,這主要是因為數據統計的資源大大豐富,事例分析的素材更為精致,教研過程中,有人可以據此做經驗性的解釋,理論工作者可以就此做理性的演繹。
以上幾個方面,要能夠形成多角互證。尤其是教育科研的論文,最好是多角互證。說老實話,只看單一數據的研究報告,我總是半信半疑,因為數據也可以生成假象,數據也是有傾向的。既有數據,又有案例的支撐;既和經驗相符合,又在理論上講得通;或者,至少要有其中幾個方面的東西支撐起來的科研結論,才能站得住。基于多種證據互相印證的循環改進,使“教師成為有研究能力的實踐者”走上了一個全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