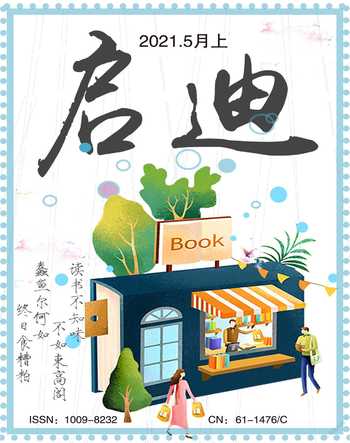小學低年級語文快樂游戲課堂的構建
張魚
摘要:小學低年級學生普遍都缺乏自主意識,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也比較弱,因而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應當大力營造快樂的環境,提升小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為順應時代的發展,教育部門針對教育方式方法進行了改革,以往教育總是以教師為中心,要求學生跟隨教師的腳步進行,而現在應該充分考慮學生的主體地位以及學習感受。
關鍵詞:小學;低年級;語文教學;游戲
引言:社會的快速發展對于教育產生了更高的要求。在小學階段的日常教學中,教師們為了挖掘學生的學習潛能,開始尋求一些有效的教學方法。小學生剛開始步入學習生活,所以對要學習的內容會有很強的了解興趣。基于此,教師們可以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選擇合理的教學方法,讓學生獲得更多的知識。
一、充分利用多媒體
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小學語文教學帶來了很多先進的教學技術。在日常教學中,教師們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教學技術,讓學生們能夠對最新的語文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因為語文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內容,所以教師們也可以對內容進行不同角度的詮釋,促進學生多種感覺器官的利用,讓學生可以在學習語文的過程中掌握其他的知識,提高自己的語文學習能力。快樂課堂的構建離不開學生的認真參與,教師需要有效利用多媒體教學讓學生對本節課的內容產生濃厚的興趣,同時,教師也應該變換教學形式,讓學生時刻保持好奇。除此之外,教師們在教學中還應該與學生進行積極交流,了解每個學生的實際和心理狀況,讓他們能夠感受到老師的關懷,從而敞開心扉,在語文課上表達自己的想法。
二、采用抽卡的教學游戲
從當前小學低年級語文課堂教學的整體情況來看,盡管很多教師對快樂課堂有一定的認識,也做了一些有針對性的設計,使快樂課堂建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有個別教師在構建快樂課堂的過程中不具有針對性和特色化。因為剛開始接觸漢字和拼音的學習,所以小學生難免會有些不適應,在學習過程中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為了讓學生能夠高效記憶相關的漢字,教師可以在備課階段制作一些漢字卡片,在課堂上讓學生認讀卡片上的內容。例如,在學習部編版二年級上冊《坐井觀天》這一節課的內容時,當進行漢字學習時,教師可以把每個漢字分別寫在卡片上,讓學生能夠清晰地認讀。教師在教學中需要將卡片發給每個學生,然后讓學生站起來大聲朗讀卡片上的漢字。對于表現較好的學生,教師可以給予他們一些獎勵,而對于出錯的學生,教師也不能一味地指責他們,而是要通過鼓勵幫助他們建立學習信心[1]。
三、采用圖片敘述的方式
低年級的語文教學內容相對簡單,充分考慮了小學生的實際情況。針對具有敘事性的課文,教師可以采用圖片的方式展示情景圖片,從而幫助班上的學生理解課文中的相關內容。除此之外,教師還可以讓學生在學習課文內容之前觀看圖片,并且用自己的語言說出圖片中的內容,從而讓學生們能夠鍛煉自身的語言表達能力。例如,在講解部編版二年級《小蝌蚪找媽媽》這篇課文的過程中,教師可以提前準備相關的卡片,并說:“同學們,圖片中的小動物是什么呢?你們知道他們的關系嗎?其實小蝌蚪長大以后就變成青蛙了,本節課就讓我們一起跟隨課文,和小蝌蚪一起去尋找它們的媽媽吧!”這樣一來,學生就會更有代入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也會全神貫注。在這樣的學習氛圍中,學生能夠感受到語文為其帶來的快樂,也能夠讓自己以積極的心態面對所有的學科學習[2]。
四、采用繞口令的方式
在長期的教學中,教師們發現學生的學習離不開漢字。只有掌握一定數量的漢字,學生才能夠快速理解所有學科中的文字。因此,漢字學習具有非凡的意義。但是漢字學習也是困難的,小學低年級學生年齡較小,在學習漢字時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傳統的漢字教學中,教師們選擇讓學生反復寫來加深印象,這種教學模式會讓學生感到枯燥,甚至對學習失去興趣。在教學中,教師們發現學生對于新奇的知識會產生學習的興趣,而繞口令就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教學方式,可以讓學生認真聆聽老師講解的各種內容,也會跟隨教師張口朗讀,從而發現學習的樂趣。例如,在為學生講解部編版二年級上冊《拍手歌》這一節課的內容時,教師可以結合課文的內容,編寫繞口令,然后讓學生在拍手的同時說出繞口令,從而加強學生的游戲和學習體驗。在整個過程中,學生必須全程聚精會神地聆聽和學習,這樣才能夠完全跟掌握本節課的所有內容。學生在讀繞口令的同時,也會對發音相似的漢字形成一定的認知,從而擴充學生的知識儲備量[3]。
結束語
總而言之,小學階段的語文教學是基礎,是非常重要的。作為小學語文教師,我們需要考慮學生的實際情況,尤其在小學低年級,教師們還需要認真思考啟蒙教育的重要意義,讓學生們從學習中掌握語文知識,并且對語文這門學科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這樣有助于他們在未來的學習中更加得心應手。
參考文獻
[1]王麗. 思維導圖在小學語文閱讀教學中的應用研究[D].揚州大學,2017.
[2]張敏. 小學語文整本書閱讀教學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8.
[3]梁麗萍. 基于核心素養的小學語文綜合性學習教學策略研究[D].淮北師范大學,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