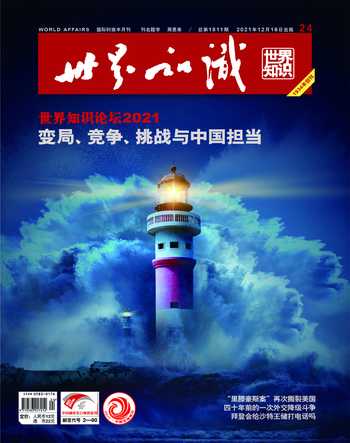對區域合作的思考(五)
張蘊嶺

區域的地緣性為開展區域合作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托。地緣區域國家比鄰而居,有著割不斷的聯系和諸多共享的利益。友好相處、合作共利是鄰國間最優的選擇。
但是,地緣本身并不必然導致所在區域的國家間一定或者能夠開展合作。地緣相近,也往往引發國家間為利益而爭奪,因糾紛而結仇。古往今來,“近而不親”的現象也并不少見。
域內國家間良好的關系是開展區域合作的重要保障。在有些情況下,良好的關系受益于內在的近親因素,比如,同民族、同宗教等,這些因素使國民間相處更容易,有親近感,愿意交往,即便出現矛盾,化解起來也比較容易。而如果缺乏這樣的近親因素,國家間建立良好的關系就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比如,在利益上相互照顧,在關系上相互尊重,在出現分歧、爭議、矛盾時,互諒互讓,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否則,則會走向惡化。
在現有的區域合作中,有一些就是因為國家間關系出問題而受到影響,甚至使得區域合作機制名存實亡。像南亞區域合作組織(南盟),就是因為印巴關系不能和解,關系長期緊張,難以開展深度合作。除非區域組織具有超國家的合法管理職能進行干預,否則,在區域層面,難以避免因國家關系不好而損害區域合作。
現代區域合作是在基于共識的基礎上進行的。國家無論大小,都以平等的身份參與,作為成員,在地位、權利上是平等的,在利益上是共享的。如果域內國家間力量對比失衡,特別是在一個大國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開展區域合作的難度就會增加。當然,如果大國能夠對其他國家平等相待,且提供更多的公共資源,則是有利于推進合作的。
區域合作機制本身也是具有推動國家間關系改善功能的。成員通過參與區域合作,在合作進程中分享共同利益,從而提高維護合作的責任意識,進而有助于國家間關系的改善。在歐洲合作中,法德關系和解,共同承擔推動區域合作的責任,也使兩國從世仇的陰影中走出來,這是一個區域合作促進國家關系改善的范例。不過,也是因為歐洲有著特殊的政治背景(二戰),把法德逼上除了合作沒有其他選擇的道路。在很多情況下,由于“本國優先”的政治驅動和壓力,政府采取主動讓步的行動往往會受到制約。
要使區域合作不斷深化、可持續,需要制定具有約束力的共守規則。區域合作的規則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大規則,針對整體合作定位的,對成員具有法律效力,涉及組織、權利、原則、責任等,如關于區域組織的條約、憲章等;一類是功能規則,是針對領域合作的,具有法律效力,涉及面比較廣泛,像自貿區協議(FTA)、投資協議、數字協議等,有些還涉及標準、程序等。對于區域合作來說,無論是大規則,還是功能性規則,越細化、越具體,對深化合作的作用越強。
在一些情況下,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區域合作是建立在軟約束基礎上的,并無法律效力,多是合作的導向性目標,而無具體的規則,落實也是基于參與方的共識、自覺行動和責任意識。還有的則是區域性對話合作機制,具有多重目標,主要是通過領導人、政府職能部門的對話,就開展合作達成共識,推動制定合作議程、合作項目,也可以在此基礎上推動制定功能性規則。
值得關注的是,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網絡的發展,在提升區域合作水平、提高合作利益的共享性的同時,也對基于地緣區域的合作形成挑戰。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具有超地緣的特性,可以創建超地緣或者跨地緣的利益,還可以規避因地緣區域兩國或者多國間關系不好而對開展合作制造的障礙。鑒于此,國家在參與區域合作的選擇上,可能會更多地考慮獲益因素,而不是地緣因素。這是一個值得重視、需要進一步觀察和深入研究的問題。不過,從研究的角度,這涉及如何對區域合作的概念進行定位,在我看來,既然是“區域合作”,還是需要對區域有一個范圍認定——地緣是區域的基本構成。這點一定要明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