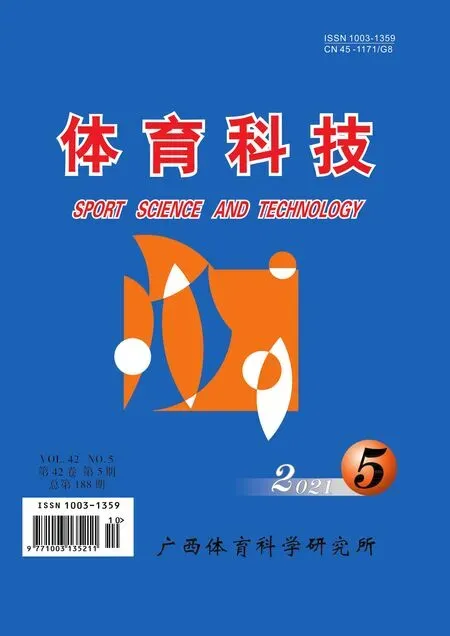基于具身認知理論的體育核心素養(yǎng)意蘊與培養(yǎng)路徑研究
王艷瓊 張亞文 譚周榮
基于具身認知理論的體育核心素養(yǎng)意蘊與培養(yǎng)路徑研究
王艷瓊1張亞文1譚周榮2
(1.廣西師范大學 體育與健康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6;2.廣西體育局江南訓練基地,廣西 南寧 530031)
從離身到具身認知的發(fā)展流布,揭示以身體為依托的體育核心素養(yǎng)與具身性邏輯的內(nèi)涵相吻合。在對現(xiàn)有文獻研究反思的基礎之上,闡述具身認知理論的教學論意義、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具身性”意蘊及培養(yǎng)路徑。認為學校體育作為培養(yǎng)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基本場域,在體育教學的情境中,教師應從明晰“具身性”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邏輯結構、樹立身心一體觀的體育教學理念、創(chuàng)設體驗式的體育教學情境、創(chuàng)造具身思維的體育教學過程等方面將具身認知的科學理念與體育教學實踐相結合,促進學生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形成與發(fā)展。
具身認知;體育核心素養(yǎng);素養(yǎng)意蘊;培養(yǎng)路徑
《中國學生發(fā)展核心素養(yǎng)》文中指出,核心素養(yǎng)主要指學生應具備的、能夠適應終身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需要的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1]。自核心素養(yǎng)提出以來,研究層面主要集中于個體應具備的核心素養(yǎng)與學科意義上的核心素養(yǎng),以此論之,體育核心素養(yǎng)則為個體應具備的核心素養(yǎng)。
以核心素養(yǎng)為頂層設計的教育理念逐漸引起學界關注,已有學者將“具身認知理論”嵌入到體育與核心素養(yǎng)的研究中,為體育與核心素養(yǎng)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論視角,推動了體育學研究與認知科學研究的融合。但當前研究,一方面缺乏對“具身認知理論”教學論意義的闡述,忽視體育教學的“體育核心素養(yǎng)”必須以具身認知為本、為棲。另一方面,缺乏對“具身認知理論”之于“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進階生成的闡釋。基于此,該研究從具身認知科學視角,闡述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具身認知性與培養(yǎng)路徑。
1 具身認知理論的基本意涵與教學論意義
具身認知(embodiment cognition)又譯涉身認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涉及人類認知過程的新概念。自提出以來,逐漸發(fā)展成為一種哲學認識論主張,在教育學范疇,具身認知理論的研究對于教學理論具有重要的再思考意義[2]。
1.1 具身認知理論的基本意涵
傳統(tǒng)認知科學認為,認知只發(fā)生在腦中,認知過程無須關注人的身體以及人與環(huán)境的交互作用[3]。18世紀以來,這種身心分離的二元論思想開始受到質(zhì)疑,一種新的認知科學開始萌芽,身體與思維、認知的關系開始受到學者的關注,如洛克認為一切知識皆來源于經(jīng)驗,主張通過身體感官來獲得經(jīng)驗知識。20世紀以來,基于對離身認知的批判,具身認知理論在哲學現(xiàn)象學、發(fā)展心理學等相關理論基礎上逐漸成熟[4]。生物學家、神經(jīng)科學家瓦雷拉(Varela)對“具身”一詞進行了詳細解釋:首先,認知依賴于體驗的種類,而這些體驗均來自具有各種感知運動的身體;其次,這些個體的感知運動能力自身含在一個更廣泛的生物、心理和文化情境中[5]。可見,一方面具身認知理論強調(diào)身體介于知覺體驗對認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強調(diào)環(huán)境在認知過程中發(fā)揮的作用。
以此謂之,那么具身認知理論的基本意涵是什么呢?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探討,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瓦雷拉、E.湯姆森以及E.羅施,他們認為身體介于知覺體驗對認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強調(diào)環(huán)境在認知過程中發(fā)揮的作用[5]。我國學者葉浩生認為“認知內(nèi)容是由身體提供的;認知過程的進行方式和步驟實際上是由身體的物理屬性所決定的;認知存在于大腦、大腦存在于身體,身體存在于環(huán)境,認知、身體和環(huán)境組成動態(tài)的統(tǒng)一體”[6]。綜合上述對具身認知的討論,再次從教育學的視角出發(fā),具身認知在教育學話語建構語境下的理論內(nèi)涵可以概括為具身性(embodiment)、情境性(situation)、生成性(emergence)三個方面[7],具體而言:
1)具身性(embodiment):具身認知理論強調(diào)認知的切身性,身體是人們認知與思考的基礎,即人們的認知依賴于身體的物理屬性(身體肉體、身體體驗、身體感官、身體經(jīng)歷、身體運動、身體結構以及身體狀態(tài)等)[8],則思維和理性的形成基于對外部世界現(xiàn)象的感知,在認知過程中具體依賴于身體部位、空間關系和力量運動的交互作用。如海德格爾將人的存在概括為“在世存在”,也就是說人在與世界交互作用的過程中通過身體來感知世界(即世界—身體—認知的認知模式),將身心關系統(tǒng)一到經(jīng)驗層面。
2)情境性(situation):在具身性的論述中認知依賴于身體的物理屬性,而情境則是身體的延展,在具身認知理論語境下,不僅心身一體、而且心身與環(huán)境也為一體,這就必然使得人的認知產(chǎn)生于具體的情境之中、與情境交互對話[9]。
3)生成性(emergence):“生成”概念也是我們理解具身認知理論的一個概念框架,認為認知是在與大腦、身體以及歷史文化背景構成的動態(tài)統(tǒng)一體中不斷生成的。瓦雷拉等人也認為:“知識和經(jīng)驗既不純粹是人對外在世界的表征,也不純粹是心智的臆造,認知是身體在同環(huán)境、歷史文化相互作用之下不斷生成的過程”[10]。
1.2 具身認知理論的教學論意義
以具身認知理論為基礎的第二代認知科學超越了第一代認知科學的身心分離的基本假設,其具身性、情境性以及生成性概念框架不僅影響了心理學、認知科學領域的研究,而且還具有重要的教學論意義。
1.2.1 教學主體的具身性與經(jīng)驗性
具身認知理論的觀點更新和拓寬了人們的教學認識論,使得科學主義與符號主義的教學認識論偏向經(jīng)驗主義、直觀主義與生活主義。在前者的影響下,知識是可以被單獨分離出來進行教學的單元,學習主體身心分離,僅是抽象的“我”,與身體意義無涉。而后者更加傾向于身體經(jīng)驗,身體不僅是心智發(fā)生的“場所”與“載體”,還是認知獲得的源泉與生成動力。具身認知理論認為“身體和心智是主體經(jīng)驗的兩個不同方面,有什么樣的身體經(jīng)驗就有什么樣的認知方式,因此,身體的性質(zhì)決定了‘我’的思維方式和內(nèi)容,決定了‘我’怎樣形成概念和進行推理。[11]”
以此謂之,教學和學習本身就是一種具身認知活動,認知過程依賴于主體的身體經(jīng)驗等物理系統(tǒng)得以產(chǎn)生并且實現(xiàn)。在具體的教學活動過程中身體是經(jīng)驗、認知與學習的根源,“身體在知識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過程中不是被認識的客體或?qū)ο螅钦J識的主體,發(fā)揮著構建知識的作用。[12]”因此,強調(diào)具身認知理論的具身性與經(jīng)驗性對于更新當代的教學認識論具有重大意義,即當代教學論不能夠忽視身體感知經(jīng)驗與體驗對于學習過程的重要性。
1.2.2 教學發(fā)生的情境性與生成性
具身認知理論認為情境是身體的延展,身體所處的情境是一個廣義的范圍,包括物理情境、心理情境以及人文情境,并構成認知的外在環(huán)境影響認知的過程、結果與方向[13]。根據(jù)這一觀點,有無情境以及情境是否生動是情境教學的重要體現(xiàn),教學發(fā)生的情境性為個體學習的身心體驗、體驗式學習創(chuàng)造了條件,改變傳統(tǒng)的教學方式,使其成為符合具身認知的教學必然。總而言之,情境教學應鼓勵學生在具體的情境過程中去體悟、對話與溝通,充分調(diào)動學生的具身信息表征。
另外,具身認知理論認為認知產(chǎn)生于行動,源于身體與環(huán)境的互動。因此,發(fā)生在具體情境之中的教學,是基于身體活動經(jīng)驗生成的,而不是大腦以符號方式表征的。也就是說,生成性的教學過程是對認知、身體和環(huán)境的整合與運用,也是對認知主體、學生和教師角色的重新安排,如處于環(huán)境中的教師有其特殊的信息體系,成為信息環(huán)境的組成部分,而處于環(huán)境中的學生則根據(jù)以往個人的生活史事、體驗與過往經(jīng)驗與環(huán)境以及作為組成環(huán)境的教師不斷相互對話、彼此建構,那么在教學過程中則代表教師與學生兩個不同的信息體系中相互融合、生成、涌現(xiàn)或轉(zhuǎn)化成新的知識結構。
1.2.3 教學過程與場域的動態(tài)性
教學過程是教的過程與學的過程的動態(tài)融合,關于這一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受傳統(tǒng)教學認識論的影響,教學過程是頭腦符號的轉(zhuǎn)化,與身體無涉,即便是具有切身性與場域性特點的體育教學,也是在規(guī)規(guī)矩矩的隊列中進行教學,教學信息單向傳遞。
具身認知理論認為,認知是一個基于主體身體經(jīng)驗與情境互動的自然流動的過程,是一個在生命場域中不斷發(fā)生的過程。在強調(diào)具身的課堂教學環(huán)境中,“學習不再是學生個人的事情,而是和學習共同體這個動力系統(tǒng)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且具有一定的共同體規(guī)則”[14],在互動中學習知識、體驗意義和享受樂趣。
2 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具身性”意蘊
關于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概念研究,體育學界尚無統(tǒng)一的認識。學者尚力沛、程傳銀根據(jù)對體育素養(yǎng)的認識與理解(體育素養(yǎng)是個體在一生中保持適當水平的身體活動動機、信心、身體活動能力、理解力和知識[15],體育素養(yǎng)的要素包括體育知識、體育技能、體育品德和體育個性等[16]),認為“體育核心素養(yǎng)是在體育素養(yǎng)的基礎上,聚焦和關注適應個體的終身發(fā)展和社會生活需要的關鍵素養(yǎng),功能價值上是體育素養(yǎng)的精髓,量少而精”[17]。因此,體育核心素養(yǎng)體現(xiàn)“素養(yǎng)”的核心要素,且這種要素是最核心、最實用和最穩(wěn)定的。
根據(jù)上述觀點,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構成可從體育的一般素養(yǎng)中篩選出核心要素作為體育核心素養(yǎng)。學者程傳銀、于秀梅[18]認為,分析體育的本質(zhì)、作用和功能是體育核心素養(yǎng)要素的核心來源,以體育的本質(zhì)與功能為邏輯起點,體質(zhì)和健康、運動技能、體育社會情感則為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構成。
2.1 體質(zhì)和健康的“具身認知性”
體質(zhì)是指人的身體質(zhì)量,具體而言是指人體的健康水平和對外界的適應能力。它是在遺傳性和獲得性的基礎上,表現(xiàn)出來的人體形態(tài)結構、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的綜合狀況和特征[19]。而健康是指“個人在身體、心理、社會適應和道德四個方面的健全”[20]。體育不僅育“體”,而且育人,育“體”的體育即是對體質(zhì)、體能及運動強度等生物指標的執(zhí)著,而育“人”的體育既是對情感、精神、意義體驗的追求,如1)心理調(diào)節(jié):調(diào)節(jié)情緒、緩解壓力、提高自信;2)豐富情感與審美體驗:享受成功、超越、挑戰(zhàn)的樂趣,承擔失敗、失誤等負面壓力,體驗運動之美、人體之美和生命之美;3)培養(yǎng)價值精神:勇敢、進取、耐苦、意志品質(zhì);4)培養(yǎng)道德規(guī)范以及社會品質(zhì):遵守規(guī)則、尊重他人、團隊合作。從育體到育人、從生物屬性到人文情懷,身體皆是生存意義——人文教育的環(huán)境和載體,身體運動系統(tǒng)對體質(zhì)和健康等信息的反饋與整合,使得體質(zhì)和健康在形成和發(fā)展中表現(xiàn)出明顯的具身性。
身體是情境的延展,作為生存意義——人文教育、體質(zhì)——健康的環(huán)境與載體,其形成和發(fā)展必定在具有情境性的外部環(huán)境的作用下得以實現(xiàn)。個體對體質(zhì)健康的追求并不全是自發(fā)性的,也需要外部環(huán)境適宜的刺激和引導。如人類文明的高度發(fā)達使其陷入自設的理性悖論:工具理性所創(chuàng)設的物質(zhì)世界正在慢慢的吞噬著物質(zhì)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人”。生產(chǎn)自動化、生活家電化正在一步一步的侵蝕著人的健康,現(xiàn)代性趨勢下誘發(fā)的“文明病”“運動饑餓”“亞健康”等造成人的身體健康的缺席和自我意識的喪失,健康意識的喪失是現(xiàn)代社會最大的危機。針對于此,國務院于2016年印發(fā)《“健康中國2030”規(guī)劃綱要》,將健康提升至國家戰(zhàn)略層次,并全方位、體系化地構建了從“醫(yī)養(yǎng)”到“康養(yǎng)”的社會健康實踐體系,采用多種方式來促進健康,其中體醫(yī)融合理念的提出標志著以“治病”為主轉(zhuǎn)向以疾病“預防”為主的人民健康理念[21]。
體質(zhì)和健康是在與外界環(huán)境諸因素間相互作用中不斷建構的、也是不斷生成的,因而也具有生成的具身屬性,這就決定對體質(zhì)健康的追求是一個長期循環(huán)和發(fā)揮個體主觀能動性的過程。
2.2 運動技能的“具身認知性”
運動技能是指通過練習而鞏固下來的,自動化的、完善的動作活動方式,它主要借助于骨骼肌的運動和與之相應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部分的活動而實現(xiàn)的對器械的操作或外顯的肌肉反應[22]。運動技能是通過學習或練習獲得,并非生而有之,動作操作過程中有一個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的具體操作必須符合某種運動法則,因此,身體必須與外界環(huán)境交互作用,通過各種感知覺信息,在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形成關于認知層面的記憶指令,從而建立起能支配肌肉層面的實際技能操作——身體運動。因此運動技能的學習包括認知層面記憶指令的學習和肌肉層面實際技能的操作兩方面,其形成和發(fā)展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具有明顯的具身性。
運動技能是大腦皮層指揮下由骨骼肌參與的隨意運動,隨意運動是指這種運動的發(fā)生與形成,是受意識支配的,服從一定的目的和任務,與本能不同,需要后天學習[22]。運動技能的后天學習特征決定了其必須在具有情境性的外部環(huán)境的作用下才得以形成,如通過教師指導、環(huán)境刺激、視頻學習、群體學習以及比賽學習等方式來習得和掌握運動技能。因此,運動技能的情境具身認知性體現(xiàn)在,一方面,個體通過環(huán)境刺激能習得與掌握基本的運動技能,如走、跑、跳、投以及一些復雜的組合動作;另一方面,個體通過環(huán)境刺激提升運動技能,如通過激烈的運動競賽(足球比賽、籃球比賽等對抗性比賽),在對抗中運動技能得以提升,群體運動意識得以加強。
運動技能形成和發(fā)展的情境性決定著它同時具有生成性。一項運動技能的習得和掌握,需經(jīng)過認知階段、聯(lián)結階段和自動化階段[23]。在各個階段,運動技能的表現(xiàn)特征均不一樣,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沒有突然變化,而是逐漸地轉(zhuǎn)移、慢慢生成的,如在認知階段的感知覺與表象特征是“視聽知覺、運動知覺及其留下的表象模糊不清、不準確”;聯(lián)結階段的感知覺與表象特征是“視聽知覺、運動知覺及其留下的表象逐漸清晰、準確”;自動化階段的感知覺與表象特征是“運動知覺精細分化,并形成專門化知覺,運動表象清晰、準確”。可見,運動技能的學習是一個階段化、生成化的過程。
2.3 體育社會情感的“具身認知性”
體育運動是一種極富感情色彩的高尚活動,它豐富著人類的情感寶庫。現(xiàn)代人的情感需求呈現(xiàn)多層次性,具有強烈的責任感、道德感、事業(yè)心,對未來充滿執(zhí)著的追求,同時,現(xiàn)代人的情感表達是具有理性的、是復雜多變的。因此,體育運動承擔著充實現(xiàn)代人高級情愫的功能,體育社會情感在人的發(fā)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通過身體運動來影響身體認知、通過身體表達來傳遞思想情感,由此得知,體育社會情感形成以及發(fā)揮作用的過程就是體育社會情感具身性顯現(xiàn)的過程。
體育社會情感只有在社會環(huán)境中才得以實現(xiàn)和表現(xiàn),學校是培養(yǎng)體育社會情感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一,也只有在學校氛圍中才能滋養(yǎng)學生的體育社會情感能力。因為學校氛圍是校園中彌漫在學生周圍的環(huán)境、關系與氣氛集合,它與學校的顯性課程相對,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認知和情緒、言談和行為。在體育支持性的學校氛圍中,學生可以獲得更多的尊重和關注、滿足與安全、自由與快樂。由此可見,體育社會情感也是在具有情境性的社會環(huán)境中養(yǎng)成,內(nèi)化成為學生的一種能力。
相較于體質(zhì)與健康,運動技能的生成性,體育社會情感的生成性則更加顯現(xiàn),體育社會情感的形成是一個動態(tài)的變化過程,是在認知、身體與環(huán)境三者的交互構造中不斷生成。認知是對外部環(huán)境的反饋,身體是體育社會情感生成的主體,環(huán)境則是體育社會情感生成的承載場域,三者缺一不可。其中,身體充當媒介的作用,將認知與環(huán)境有效連接在一起,能夠保證體育社會情感在身體實踐中不斷生成[24]。
3 “具身性”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路徑
3.1 明晰“具身性”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邏輯結構
體育核心素養(yǎng)是核心素養(yǎng)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體育課程應充分發(fā)揮學科的教育功效,圍繞培養(yǎng)學生的體育核心素養(yǎng)來設計。以體育的本質(zhì)及概念為邏輯起點而提出的體質(zhì)和健康、運動技能、體育社會情感為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構成,發(fā)展學生的體質(zhì)和健康、運動技能、體育社會情感是學校體育教育功效的價值體現(xiàn)。在學習設計過程中,以身體為體育學習主體,與心智、外部環(huán)境交互構造,影響學生自我高級認知的形成(如圖1所示),進而影響學生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形成。

圖1 “具身性”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邏輯結構
明晰“具身性”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邏輯結構,是具身性體育教學理念樹立、體育教學情境創(chuàng)設以及創(chuàng)造具身思維的體育教學過程的首要前提。在具身認知理論關照下,身體練習的體驗式教育尤為凸顯,學校體育教育功效的價值體現(xiàn)于:體育是發(fā)展身體的教育,通過身體練習來發(fā)展學生體能、強健體格,真正達到野蠻其體魄;體育是通過身體的教育,以身體為載體文明其精神;體育是利用身體的教育,利用身體促進學生的社會化[25]。
3.2 樹立身心一體觀的體育教學理念
由傳統(tǒng)教學理念或思想生成的“灌輸”教學理念,使得身心分離,“離身性”的體育教學模式影響著整個體育教學過程。在“離身性”體育教學的運作過程中,體育教師仍以既定的標準來進行教學設計,教學環(huán)節(jié)按部就班,教學評價統(tǒng)一標準,另外,學生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墨守成規(guī)、被動接受,享受樂趣的體育課嫣然成為整體化一的廣播體操比賽,趣味無存,學校更像是工廠,體育課為流水線,學生即為“產(chǎn)品”,按照社會需要的“理想人”的“科學化”理念塑造產(chǎn)品,學校體育發(fā)展身體的教育、通過身體的教育、利用身體的教育的教育功效無從體現(xiàn),具身思維難以實現(xiàn)。這種壓制身體主體的教育勢必影響學生體育技藝的塑造與體育品德的形成,“完善人格,首在體育”“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等時代口號流變的價值斷裂,受教育者體知世界原初情感的視野和路徑被遮蔽。
具身思維生成的“身心一體觀”體育教學理念,改變了意識主體產(chǎn)生的身心二元論教學理念,身心雙重融通的教學理念進駐教學設計序列過程,體育教學設計應站在身心整全意義的角度,彰顯“身體主體”的教學理念。學者張洪潭認為“體育教學,以傳習運動技術為主旨,不強調(diào)健身強體之效果,也不追求運動技術這種操作性知識的任何實用效益。”這種不強調(diào)、不追求并非真正的淡化,其認為“不講究實用效益的教育才是本真的教育,其客觀效果將是運動技術傳習活動雖不追求卻必有強化體能之功效”[26]。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體育教學具身性特征,學練技術、強化體能是體育教學的根本所在,也是激發(fā)學生感悟身體,發(fā)展學生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邏輯前提。
在具體體育教學實踐中,要不斷踐行“身心一體觀”的教學理念。具體而言:首先,教師要營造一個身體互動、自由寬松的教學氛圍,教會學生運動技能。基于青年學生身心發(fā)展的規(guī)律,培養(yǎng)學生的運動技能,使學生形成基本的運動能力,而以體質(zhì)和健康、運動技能、體育社會情感為主的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皆是通過以身體練習為手段的體育活動而獲得,因此,身心一體的教學理念,應教會學生運動,才能使其具備體育核心素養(yǎng)。其次,教師要充分考慮學生的個性特征,善于挖掘?qū)W生主體表現(xiàn)的“閃光點”,正確認識學生身體差異及體育認知的螺旋式上升,激發(fā)學生的運動興趣,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應使學生喜歡運動,持久良好的運動興趣是體育核心素養(yǎng)形成的保障。再者,通過教學設計、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等落實身心一體觀的教學理念,培養(yǎng)學生的體育核心素養(yǎng)。
3.3 創(chuàng)設體驗式的體育教學情境
杜威認為“教學必須要有一個實際的經(jīng)驗情境作為思維的開始”,需要有“產(chǎn)生和引起富有思想探究問題的情境”[27]。也就是說要以學生的生活經(jīng)歷與過去存在的“經(jīng)驗”作為教學情境,即學習要在情境中進行,學習要形成積極參與的實踐共同體[28],教學情境是教師與學生共同作用的客觀環(huán)境,一般具有認知、學科、社會交往、過程、發(fā)展和生成等屬性。基于此,教學情境是指由對教學行為有重要影響的各種物質(zhì)的、制度的、精神的因素構成的課堂環(huán)境和氛圍[29]。體育教學情境是指依據(jù)教材內(nèi)容以及學生的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營造以身體體驗為目的、激發(fā)學生體育學習的動力、凸顯體育教學教育作用的特定課堂環(huán)境和氛圍[30]。因此,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要在具有具身性的體育教學情境中進行。
具身認知理論強調(diào)身心一體的認知觀,因此,體育教學情境的創(chuàng)設,要凸顯教學情境的認知、學科、社會交往、過程、發(fā)展和生成等多元屬性,營造積極身體生成的、體驗式的體育教學情境。具體而言,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
(1)教育者要充分認識到心智、身體和環(huán)境的整體性關系,營造情境啟發(fā)、切身體驗、學生積極參與的體育教學氛圍,使學生的身體、心智與環(huán)境互融,激發(fā)學生體育學習的原生動力。如課堂教學可采用競賽的形式,在特定的環(huán)境、場域中提高學生的體質(zhì)和健康、運動技能,體育社會情感。
(2)在運動技能形成的認知定向階段、練習形成階段和自動熟練階段,教育者要積極引導學生實踐反思、善于總結、提高認知,外顯于體質(zhì)、技能的形成,內(nèi)化于健康和體育社會情感的形成(具備體育核心素養(yǎng))。通過特定的教學情境,提高學生的情感體驗與價值判斷,推動學生具身認知的進一步深入。
(3)身體是學習的主體,體育技能、體育情感的習得是通過身體練習。因此,積極發(fā)揮教師的引導作用,鼓勵監(jiān)督學生對運動技能的反復練習,體驗身體思維的表達,體知運動技能,促進運動技能的自動化生成。
3.4 創(chuàng)造具身思維的體育教學過程
教學過程是教的過程與學的過程的動態(tài)融合,體育教學課程是學校體育課程實施的核心活動。具身思維的教學過程,既是獲得良好的身體體驗、完美的身體感受、豐富的身體認知的過程。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需要按照具身思維的邏輯主線來進行教學設計,在具身思維的體育教學過程中進行。
在體育教學實踐過程中,首先,獲得良好的身體體驗。體育與健康課程的實施,首要目標是使學生獲得良好的身體體驗,這是教的過程與學的過程動態(tài)融合的前提,也是體育社會情感獲得的前提。其次,獲得完美的身體感受。完美的身體感受只有基于運動技能、教學環(huán)境對身體器官的刺激,引起神經(jīng)系統(tǒng)機制反射,才能刺激身體感受,進而強化運動技能,增強體質(zhì),增進健康。最后,獲得豐富的身體認知。豐富的身體認知能夠提升學生的自我認知,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判斷,逐步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學生具備體育核心素養(yǎng)。
4 結語
身體是探索世界的媒介。基于身體、情境與生成的認知進路,審視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具身性意蘊,探尋“具身性”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路徑,為體育核心素養(yǎng)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論視角,以此推動體育學研究與認知科學研究的融合。
[1]《中國學生發(fā)展核心素養(yǎng)》總體框架正式發(fā)布[N].天津教育報,2016-09-14.
[2]焦彩珍.具身認知理論的教學論意義[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57(4):36-44.
[3]夏皮羅.具身認知[M].李恒威,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2014.
[4]LAKOFFG,JOHNSON 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
[5]王凌雪.從離身到具身:論教學思維中的身體轉(zhuǎn)向[D].重慶:西南大學,2015:6.
[6]葉浩生.具身認知:認知心理學的新取向[J].心理科學進展,2010,18(5):705-710.
[7]曹周天.具身認知理論引領下的有效教學變革[J].當代教育與文化,2021,13(1):40-44.
[8]Goldman &Vignemont.Is social cognition embodied?[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2009,13(4).
[9]胡萬年,葉浩生.中國心理學界具身認知研究進展[J].自然辯證法通訊,2013(12):112.
[10][美]F·瓦雷拉,E·湯普森,E·羅施.具身心智:認知科學和人類經(jīng)驗[M].李恒威,李恒熙,王球,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11]葉浩生.認知與身體:理論心理學的視角[J].心理學報,2013(4).
[12]葉浩生.身體的教育價值:現(xiàn)象學的視角[J].教育研究,2019(10).
[13]殷明,劉電芝.身心融合學習:具身認知及其教育意蘊課程.教材.教法[J].2015,35(7):57-65.
[14]肖菊梅,李如密.從“離身”到“具身”:課堂學習環(huán)境的新構建[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8(1).
[15]陳思同,劉陽.加拿大體育素養(yǎng)測評研究及啟示[J].體育科學,2016,36(3):44-51.
[16]余智.體育素養(yǎng)概念研究[J].浙江體育科學,2005,27(1):69-72+80.
[17]尚力沛,程傳銀.核心素養(yǎng)、體育核心素養(yǎng)與體育學科核心素養(yǎng):概念、構成及關系[J].體育文化導刊,2017(10):130-134.
[18]于秀梅.學生體育學科核心素養(yǎng)及其培育[J].中國學校體育,2016,36 (7):29-33.
[19]郭瑞芃,徐建方,李良,等.中外青少年體質(zhì)健康測評體系對比研究[J].中國體育科技,2019,55(6):3-13.
[20] D.Mechanic.Social Policy, Technology, and the Rationing of HealthCare.Medical Care Review, 1989(46):113-120.
[21]李璟圓,梁辰,高璨,等.體醫(yī)融合的內(nèi)涵與路徑研究:以運動處方門診為例[J].體育科學,2019,39(7):23-32.
[22]于志華.網(wǎng)球初學者類比學習與外顯學習的協(xié)同效應[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7(4).
[23]何靜.具身認知研究的三種進路[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6):53-54.
[24]馮振偉,張瑞林,杜建軍.基于具身認知理論的體育教學意蘊及其優(yōu)化策略[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17,26(5):98-102.
[25]鄧若鋒.身體練習體驗的體育教學理論框架構建[J].體育學刊,2016,23(1):113-117.
[26]張洪潭.技術健身教學論的理論基礎與基本思路[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07(3):1-8.
[27][美]杜威著.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68-171.
[28][美]戴維·H·喬納森著.學習環(huán)境的理論基礎[M].鄭太年,任友群,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66.
[29]陳佑清.教學論新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300-305.
[30 鄧若鋒.積極身體練習體驗的體育學習動因[J].中國學校體育,2014(5):45-47.
Research on the Meaning and Cultivation Paths of Sports Core Literacy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WANG Yanqiong, etal.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Guangxi, China)
基金項目: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研究生教育創(chuàng)新計劃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專項課題研究項目“廣西體育碩士研究生核心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模式研究”(JGY2020032)。
王艷瓊(1974—),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體育人文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