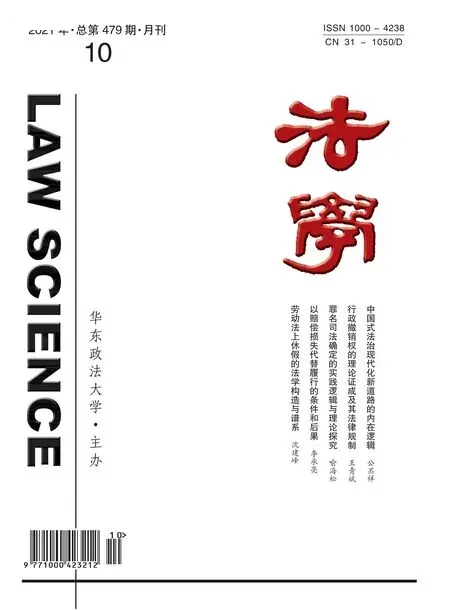WTO法律解釋權的錯配與重置
2021-02-27 14:15:13胡加祥
法學
2021年10期
關鍵詞:法律
●胡加祥
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的“停擺”固然與多邊貿易體制存在諸多深層次問題密切相關,但是美國阻撓上訴機構成員遴選導致其癱瘓的一個主要理由便是上訴機構過于“能動”,對于不少多邊貿易協議的解釋已經超越了其本身含義。〔1〕See Stat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Meeting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Geneva, February 25, 2019.換言之,WTO爭端解決機構的法律解釋應該放棄“能動主義”傾向,回歸“克制主義”的常態。“司法能動”與“司法克制”本是一對司法的概念,源于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法官在國內司法審判中的表現。前者意味著司法審判應反映現實變化和社會需求,敢于通過司法方法和現代技術突破既有規則,創造法律;后者意味著法官在司法審判過程中應嚴格信守法律條文,排斥政治、道德、政策以及個人情感、偏見、價值觀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司法能動主義強調面向未來,司法克制主義則傾向維持現實。〔2〕參見姜世波:《國際法院的司法能動主義與克制主義政策之嬗變》,載《法律方法》2009年第1期,第203-214頁。WTO爭端解決機構是WTO總理事會下的一個專門機構,爭端解決采用的是類似于法院的二審終審制,通過的裁決報告對當事方具有約束力,與國內司法具有一定的同質性。但是,從本質上講,它們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法律實踐。從“司法能動”和“司法克制”的視角來討論WTO爭端解決機構的法律解釋,只是一種類比,多邊貿易體制的特殊規定注定了WTO爭端解決機構的法律解釋有其固有之特性。
一、一個謬誤的緣起:從“皇冠上的明珠”說起
WTO成立……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新少年(2023年9期)2023-10-14 15:57:47
法律方法(2022年1期)2022-07-21 09:17:10
法律方法(2021年3期)2021-03-16 05:57:02
法律方法(2019年4期)2019-11-16 01:07:16
法律方法(2019年3期)2019-09-11 06:27:06
法律方法(2019年1期)2019-05-21 01:03:26
法律方法(2018年2期)2018-07-13 03:21:38
學生天地(2016年23期)2016-05-17 05:47:10
山東青年(2016年1期)2016-02-28 14:25:30
中國衛生(2015年1期)2015-11-16 01:0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