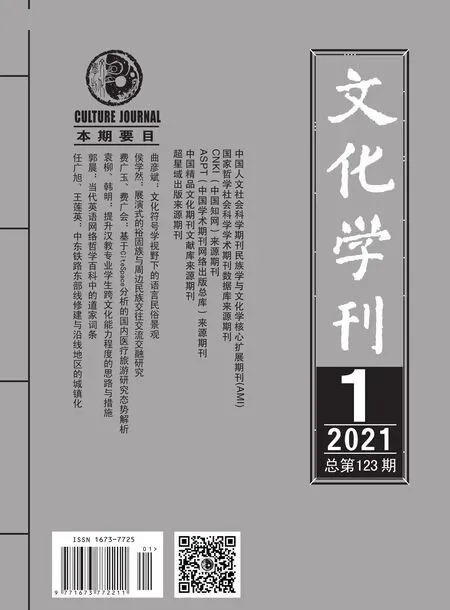從“人格二重性”淺析風格與人格的關系
孔祥睿
一、人格雙重內涵的闡釋
人格在心理學上被稱作個性,這個概念來自希臘語中的“面具”,類似于中國京劇中的臉譜。那么問題就來了:根據人格這個詞的基本含義,人格是人所具有的區別于其他人的獨特而又穩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風格,可見它是每個人特有的一種人本質的生存狀態。既然是一種內在的狀態,為什么會被說成是外在的面具呢?因為人格可以脫離人本身而存在,外化表現為道德的、審美的、法律的、社會的各方面的要素去展示自身的價值,追根溯源我們會發現,人格其實就是人本質的生存狀態的外在表現。
這樣人格解釋為“面具”也就不再難理解,因為在社會中存在的每個人都是渺小而獨特的個體,為了能更好地生存,我們不得不給自己戴上“面具”,將一部分真實的自我掩蓋起來,以求在社會中更好地保護自己、發展自己。生活就好似戲劇舞臺,每個人為了能夠在舞臺上完成出色的表演,不得不扮演著各種角色,也就需要我們戴上各種各樣的“面具”。原本這些“面具”并不是人本身的一部分,但是時間久了,這些“面具”似乎變得難以丟棄,逐漸融進每個人的個體存在之中。由此,作為人格就具有了兩種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種是“面具”之下的人格,另一種是“面具”所呈現出來的人格。我們將其稱為“人格的二重性”:第一重是戴著“面具”的,為的是在生活中能夠趨利避害;第二重就是“面具”下真實的自我狀態,在這種狀態下“面具”更像是一個保護傘,可以使人自身的潛能被無限激發,隨意發揮創造力,自然流露真情實感。
關于雙重人格形成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個人與周遭環境(包括他人、自然、社會、階層)的復雜關系造成的。舉例說明,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受到宗法制度的影響,這種通過血緣關系所連接成的看似溫情脈脈的政治制度,我們在不否認它進步性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其缺陷。在這種制度下的文人,既要用宗法制度來規范自己,又要在此基礎上表達出自己真實的情感,這顯然限制了文人人格的豐富和發展,文人在夾縫中求生存,便逐漸形成面具內外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格。就嵇康來說,作為“竹林七賢”中性情比較豪放剛烈的人之一,在寫《與山巨源絕交書》的時候那樣憤慨地表達對于仕途的不屑一顧,完全想不到《家戒》也是出自他手。在《家戒》中,我們完全感受不到這是一個有棱角的嵇康,他告誡自己的兒子:對于當地的長官表示尊重就可以了,切不可交往過密,因為官場險惡以免招惹是非,陷入困境;不要隨意接受邀請去參加聚會,因為參加聚會就避免不了要喝酒,不管你愿不愿意喝都要裝模作樣地端起杯子,以免人家說你不合群。我們從《家戒》中看到的更像是一個畏首畏尾的嵇康,與之前那個意氣風發的嵇康判若兩人,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這樣“面具”內外有雙重人格的文人比比皆是。
二、人格與風格的一致性
作家創作為的是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抒寫自己的理想壯志,闡發自己對生活的一種理解,最終升華為自己的人生體悟和價值追求。這就明顯可以看出作家主觀方面的因素對于文學創作風格的形成有巨大而又深刻的影響,而在主觀因素中又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格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影響文學風格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在社會中礙于各種現實因素,人們可能不能夠完全將自己的人格釋放出來,那么在作家進行創作的過程當中就會將自己藏匿于“面具”之下的人格展開出來,這時候“面具”下的真實人格與創作風格具有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和統一性。這種一致性僅僅在一種情況下出現:作家真正具有偉大的人格,因此他的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帶有偉大的風格。換句話講,就是作家“面具”內外的人格是一致的。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到:“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1]正如王國維所說,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中,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文天祥等文人,他們的人格就和他們的文學創作風格是高度一致的。具體以莊子來說,他的散文創作呈現出來的是汪洋自肆、博大精深的創作風格,這與他的偉大人格具有一致性。究其原因,作為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總是表現出以樸素自然的審美理想、審美情趣、收放自如的想象空間、心齋坐忘的方式追求自然主義,并希望能夠和大自然融為一體。莊子在創作的過程當中對自己的人格進行改造、升華和轉化,最終形成了專屬于他的藝術風格,“面具”之下的真正人格和創作風格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
關于風格和人格的一致性問題,有兩個非常鮮明的觀點:一個是中國古代所提出來的“文如其人”,另一個是布封所提出來的“風格即人”。但是,我們要注意一個理解上的誤區,不管是“文如其人”還是“風格即人”,都不能說明風格和人格是簡簡單單的對等關系。雖說作家的創作風格是他們精神面貌的展現,但是我們只能說人格是構成作家創作風格的重要一環,而不是作家創作風格的全部,當人格和審美理想達到一致和統一的時候,作家的人格和創作的風格才會達到一致,但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做到這一點,即真正將“面具”之下的真實人格揭開來給人們看。
三、人格與風格的矛盾性
矛盾性更多體現在作家創作時戴著“面具”,將完美的一面示人。換句話講,作家是戴著“面具”在創作,實際上“面具”下面真實的人格并沒有示人,這就造成人格和風格不一致。總結起來,矛盾性主要表現為兩種情況:一種是作家具有復雜的人格,但是他的作品卻具有簡單明了的風格;另一種情況是“面具”示人的人格與“面具”下的真實人格有著巨大的差異。
第一種情況即在現實中作家為了能夠更好地適應生活,他們可能會選擇佩戴不同樣式的“面具”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但那都不是他們真實的人格,他們更愿意在創作過程中展現真實的人格。典型的例子如我國當代著名的作家孫犁,孫犁所面對的現實情況比他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要黑暗得多、痛苦得多,但是孫犁卻沒有因為現實生活影響他的人格和創作風格,在他的心底裝著的還是真、善、美,所以他說:“我看到真、善、美的極致,我寫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惡的極致,我不愿寫。這些東西,我體驗很深,可以說是鏤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寫這些東西,我也不愿意去回憶它。”[2]糟糕的外部環境并沒有改變其內在的風格,是因為這些實際的人生境遇并不能很好地給孫犁帶來真正的審美體驗以及并不適應他的審美理想,并且達不到他的審美訴求,所以他還是選擇保持他的原本。
矛盾性產生的原因不外乎審美理想高于作家現實人格。文學作為一種創造活動,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主觀性。“只是要作文章,令人觀賞而已。”[3]由此可見,作家都期許作品能夠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期許在作品中能夠自如地表達自己的審美理想并由此激發出讀者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一個作家所追求的審美理想和現實中所追求的理想相一致,那么人格和風格就會具有更高的一致性;如果一個作家追求的審美理想高于現實生活中追求的理想,那么人格和風格就會呈現出矛盾性。具體舉例,唐代著名的作家韓愈,后人對于他的散文贊不絕口,但是當提到他的人品的時候不免有些微詞。朱熹說,在現實生活中韓愈是一個貪權慕祿、貪財好色的人,這與他文章所彰顯的那種大氣磅礴、浩然正氣的風格相差甚遠。我們明顯可以看出,韓愈在生活中很少以儒家的倫理道德規范來約束自己,但是他在行文過程當中卻時刻按照儒家的規范來要求自己,他的審美理想和他的真實人格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這樣既勢必會導致人格和風格之間相差甚遠甚至出現矛盾。
四、結語
如今我們重提風格與人格的關系,不論是探討人格與風格的一致性還是矛盾性,都是為了擺脫我們已經墨守成規的一些觀念,如“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認為作家人格與創作風格就是簡單的對等關系。事實上,人格和風格的關系是復雜的。同時,探討人格和風格的關系又是為了明確作家創作的本初目的:以人的精神品質、思想道德為創作的標準,作家在現實生活中不僅要戴好“面具”創作,求得更好的生存,而且不要忘記“面具”之下的真實人格,達到真實人格和創作風格高度一致。只有這樣,才能夠創作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