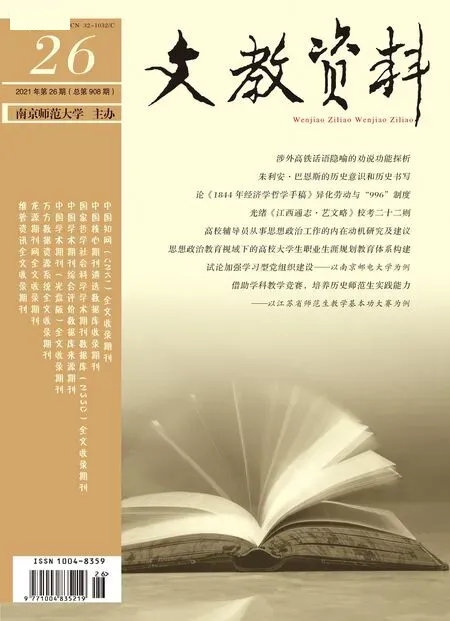文人安邦:管窺張坦熊與玉環地方展復構建
鄧 琳
(寧波大學 人文與傳媒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浙江玉環在清初曾遭政府遷棄,直至雍正年間才再次開墾。學術界對玉環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探討了玉環廳是直隸廳或是散廳的問題[1],以及追溯了玉環從遷棄再到展復這一過程,介紹了玉環的開墾設訊、玉環的經費來源、島民的戶籍與身份等相關問題。[2]然而,地方的發展離不開以人為主體的生產建設活動,《玉環古志》《玉環縣志》《玉環縣人物志》和《玉環縣文史資料選輯》等當地資料都有對首任玉環同知張坦熊生平及在任事跡的介紹,但未能詳細闡述。本文試圖通過梳理相關文獻,明確張坦熊在當地發展的奠基之功。
一、玉環的歷史沿革
在漫長的歷史沿革中,玉環的發展因時局變化、朝代更替呈現巨大的波動:明朝因抗擊倭奴內遷人民,清順治年間因沿海反清復明勢力,下《遷海令》遷棄,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鄭克塽投誠之后,清廷頒《展海令》解除海禁,玉環等東海岸島嶼才有民眾陸續上島。
玉環地區地理位置險要,張坦熊在《展復玉環論》一文中描述道:
外截海洋,內資保障;崇岡峻嶺,周匝環流;依山筑堡,險足以守;四面泥涂,捍衛亦易;此玉環之內勢然也。山外有南麂、北麂橫截對峙,又為玉環之屏塞,此玉環之外勢然也。[3]
這樣重要的地理位置使玉環地區的復設成為必然。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撫李衛兩次向朝廷奏請展復玉環,其中于當年十月上《請展復玉環山奏議》,詳細闡述了玉環開復的必要性和相關問題的解決辦法。雍正六年(1728),批準展復,朝廷正式置玉環廳,并置玉環同知。
玉環山明以前為濱海荒島,舊無記載。國朝雍正五年,浙江巡撫李衛奏開,其地始筑城,設清軍餉捕通知駐防其地,以桐廬知縣漢陽張坦熊為之。[4]
對于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封建社會,社會生產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勞動力的投入,故展復之初首要之務即遷周圍百姓到此地開墾恢復生產。玉環島方圓700余里,有可墾土地10萬余畝,土性肥沃且有鹽利,由張坦熊主管墾殖之事。[5]玉環展復,“首先是福建惠安崇武漁民徙居坎門,創海洋捕撈的延繩釣業,繼而平陽、永嘉、樂清、瑞安等玉環周圍五縣居民上島圍墾”[6],至此玉環島人口復升,農業生產活動逐漸恢復。
大規模的人口遷移,為該地區的生產建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促進了社會發展,社會的發展和地區經濟恢復推動了地區行政單位的復設,反哺于地區的建設與開發。
二、張坦熊其人
自雍正六年(1728)玉環始設廳至宣統元年(1909)設咨議局進行資議員選舉,這一期間歷任玉環同知或代理同知前后共92任89人。[3]但自玉環展復之后,對此地貢獻最大且為后世發展打下基礎的應是第一任玉環同知張坦熊。
張坦熊,字男祥,號郎湖,湖北漢陽人,乃漢陽張氏一族,與清代蜀中第一家黑柏溝張氏異派同源。其祖父張三異是清順治己丑年(1649)進士,科舉入仕、政績卓越且子孫多有成就。在張三異的子、孫、曾孫三代中,出仕者達三十人。張坦熊之父張仲璜,曾以貢生選任中書舍人,改授廣西梧州府丞,父張三異去世后告老還鄉。張坦熊,康熙二十三年(1684)甲子生,與其兄張坦麟同為康熙五十五年(1716)舉人。[7]為官經歷記載有:
初任浙江桐廬縣令,調仁和縣令,補玉環同知,擢守臺州,不久轉任天津道。乾隆三年(1738)升任云南按察使,乾隆十六年(1751)去職還鄉。[8]
康熙五十九年(1720),張坦熊任桐廬縣令,治理能力頗強,在當地實行革除陳規陋習、免除苛捐雜稅等措施[9],當地人民安居樂業。袁枚曾作《書張郎湖皋使逸事》一文,以小說的形式敘述張坦熊在任桐廬知縣時的趣事,稱贊其治理有道、公正廉明,清官形象躍然紙上。[10]張氏在這些地區的管理經驗為其治理玉環打下堅實基礎。
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撫李衛奏請玉環展復并得到上同意后,令時任桐廬知縣的張坦熊兼理玉環開墾等事宜。張氏遂于雍正五年(1727)三月初一日委辦玉環墾務,招徠周圍各縣良民并驅逐當地流民。在此期間他為展復玉環所做的努力得到周圍人的贊許和認可,“溫臺玉環同知張坦熊實心辦事,不辭勞怨,勇往有為,于海外新展地方招來開墾事宜,辦理妥協,屬賢能之員”[11]。除辦理墾務外,張氏在任玉環同知期間繼續實施各項措施恢復當地正常活動。下文據張氏在任期內所作《新筑楚門南塘說》《玉環城記》《展復玉環論》等文,輔以玉環第一部方志《特開玉環志》,分析張坦熊治下玉環所發生的積極變化。
三、整治措施
張坦熊自署理玉環同知,在任六年。其間采取興建基礎設施、清理四周隱弊等措施,對玉環復興發揮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一)基礎設施建設
張氏認為文官治理海疆,須有防患意識,遂以“防”為主,“文職居安思危,將民壯亦寄干城,故本山險要,均宜熟悉于平日,籌畫于未然則也”[12],注重城池、堤塘修筑。以下列舉幾例。
玉環城:玉環因是新開復之地急需修繕城池。雍正八年(1730)秋,張坦熊在玉環筑城鑿池,“高其城垣以資屏障”,動工修筑城垣至雍正十年(1732)三月竣工。玉環被稱為“海外孤城”,地處深山大海之中,筑城之石需從其他地方運往,施工尤為不便。是時正值秋季雷雨季節,洪流在塘垟、后蛟一帶沖出一條河道,使得載石之舟得以進入,工程迅速完工,張坦熊將此自然之力造成的河流稱為“天開河”,意為上天幫助而開的河流助玉環城池之修建,并作《天開河賦》紀念。玉環城周圍長九百六十一丈五尺五寸,城垛六百七十五個,開靖海、永清、鎮遠、寧濤東西南北四門,修好之后“其屹然巍然駕青山而臨滄海者,豈獨溫臺之屏障哉,抑將為全浙之藩籬矣”[12],城池固若金湯方可保境安民。
楚門南塘:歷來養民首重農田,農田首重水利。楚門乃“太平之屏障,亦玉環之要津”。此前在此筑城以御寇,且筑南塘以防潮水內沖。然而自人民內遷,南塘一處早已廢棄。隨著玉環展復,南塘的重筑提上日程。雍正五年(1727)秋動工修筑,張坦熊集結當地貧民壯丁修筑楚門南塘,最初新修之塘基礎薄弱,幾次海潮沖毀即坍塌,功之不可卒圖,重建久廢之塘來抵御浪潮,并非易事。“非浮土衰草之力所能勝也。因知石塘為上,草塘次之,土墻最下,為之輦石砌于其外,使實而堅。適值春來霖雨如注,內精亦多坍塌,星即培草增寬,使內無蝶陬之可乘”[12],雍正六年(1728)冬竣工,楚門萬頃之田成膏腴,“自此南塘之形勢直如長虹,舉洪潮巨液不能損其毫末”。南塘修筑好之后,每到夏雨秋潮之時,都會令識水性之人潛探,若有縫隙即填實其中。雍正八年(1730)五月初九日突發洪水,邊海之塘俱毀,唯南塘安然無恙。成事雖在天,而防患在人,張氏“居安思危”成效初見。
城隍廟:在農耕文明社會,民眾往往信仰神靈以求庇佑。在地區建設中,廟宇的建設必不可少,尤其是在自然環境影響較大的海島。祈佑城隍神保護當地,成為民間的重要活動,地方官組織修建城隍廟蘊含了為當地祈福的愿望。雖正值豐年,玉環當地已恢復生產生活,但是因特殊位置,水旱等天災隨時可能降臨,此“維神之職”,因而城隍廟的修建提上日程,“議建城隍廟于府治之東”[12]。廟宇的修建由官府全權負責,未有侵擾百姓,“工役財務悉出于公,不以擾民,凡閱九月而公竣”,嶄新的殿宇修好后,百姓民心安定。
隨著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玉環步入正軌,逐漸發展。
(二)清理四周隱弊
沿海口岸,隱弊無窮。玉環周圍一地名為石塘,“田地二千余畝,盡屬沃壤”,本欲和玉環當地一同開墾,然因其孤懸海外,四面通洋,且無文武稽查,多閩人在此地聚集偷運,滋生事端。
停泊船只查有三項;內有湘船,系挾費商船,俱有身家,頗能守法;又有般糟,借名換魚,其實偷運酒米豬鹽,以致近海產谷之區,歲登豐稔,市價反行騰貴,且令玉環官鹽堆積二十余萬斤,塞阻不行……且閩人性多強悍,現今墾民王子爵砍存搭廠干茅數十擔,公然率黨搶奪。[12]
新復之地亟待明確規章制度。張坦熊提到治理石塘需對過往商船登記船照,按季造冊以備查驗。同時將不法船只緝拿糾察,驅逐無牌閩人棚廠。以下可見船照相關規定:
按船照字號著落實刊,不許浮釘小板,桅篷亦大書縣分字號,一望了然,便于物色。漁汛一畢,給還原照,聯腙并返。仍將釣糟若干只何日到岙,何日返棹,汛防照進口出口之例,按季造冊,并具不致容留船照不符甘結,申送憲核。[12]
其中如有船只私自偷販,即將其移回原籍,并將船只收歸官方,禁止其出洋貿易。并規定來往船只泊有定所,以杜絕奸良。
雍正六年(1728)正月,張坦熊向李衛提請開墾石塘,隨即勘察。稽查當地盜匪,驅逐私懇民眾,將當地民眾編入保甲以便治理:
當即會同太平縣履勘情形,稽查奸匪,驅逐私墾之民,詳請照依玉環之例,許無過窮民有妻子者,丈明田地若干,取具族鄰保結,編入保甲在案。
玉環自開復后,以自然之利養生繁之民。張氏當此海疆重任,“思深慮運,精畫萬全,既足以消釁于未萌,亦可以有備于臨事,而為久安長治之謨也歟”[12],興利除弊,卓有政聲。初到此地時滿目瘡痍,今水師游巡海上,匪無可入;戰艦泊海口,詭船易擒;嚴行保甲,奸匪無容,至此玉環當地保障已足矣。
張坦熊在桐廬時不畏強權,清廉為官;在玉環時“工役財務悉出于公,不以擾民”。張三異曾告誡其后人“移孝作忠,汝輩聞之已熟。第守祖父母清白忠厚、不愛錢、做好官之訓,尤以活人為念。宜城默,毋自矜侈。宜省刑,毋多事以擾民”[7],此番家訓告誡,想必已被張坦熊牢記在心,并運用在任職的每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