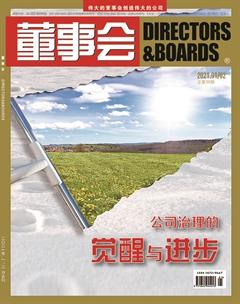并購失控:究竟誰惹的禍?
沈永鋒

2019年,對公司來說是遭遇困境的一年,公司于2015年12月以現金9億元收購的子公司上海新高峰生物醫藥有限公司之全資子公司上海新生源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未履行公司對外擔保事項正常的決策程序,擅自為他人提供擔保,且2019年經營業績突然出現大幅下降,為全面核實相關情況,加強子公司管理,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派工作組進駐上海新高峰,管控工作受阻,上海新高峰無法恢復正常運營,公司無法對上海新高峰及其子公司的重大經營決策、人事、資產等實施控制,公司在事實上對上海新高峰及其子公司失去控制。
這是上市公司亞太藥業2019年年度報告披露的部分內容。公司稱,通過自查發現上述事項后,主動向監管部門匯報,主動披露,目前公司正努力協調各方工作,進一步核實債權債務,清查資產,并積極配合監管部門的調查工作,將采取各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司法等手段維護上市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合法權益。
不難看到,上市公司失去對并購目標公司控制后的惡果,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是并購事實上失敗,財產損失發生;二是目標公司違規擔保問題,導致損失存在不確定性;三是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被證監會立案調查。
無獨有偶。2017年年底爆發的新日恒力對其子公司博雅干細胞失去控制一事,當時就引發了媒體的熱議。失控事件還寫進了上交所《2017年滬市并購重組及監管情況答記者問》,其中提到“四是更加關注重組后續整合和承諾履行情況。將重組問詢、年報審核、臨時公告監管結合起來,持續監管重組信息披露的前后一致性以及業績承諾的完成情況,重點關注業績承諾完成率逐年下滑、上市公司無法有效控制重組標的等異常情況,督促相關方及時、足額履行補償義務。例如,某公司2015年收購某干細胞類資產,雙方簽訂有業績補償協議,但該資產2015年與2016年均未完成業績承諾,交易對方未按前期承諾履行業績補償及股份回購義務。而后,上市公司又發生與標的資產方的借款糾紛,公司無法審計標的資產的業績完成情況。發現問題后,前后發出5份問詢函,及時向投資者提示標的資產業績承諾未完成、補償義務未履行、大額商譽減值、喪失控制力等重大風險。經督促,大股東承諾協助解決相關糾紛并通過收購標的資產,彌補上市公司損失。”
上述兩家上市公司對并購目標公司失去控制事件,是2013至2016年并購潮一個必然的“后遺癥”,有很多的共同點可以總結,究其根源,成因至少有以下三點。
“三高”并購惹的禍
兩起并購都是典型的“三高”并購,即:高估值+高溢價+高業績承諾”。兩個目標公司在并購之前除了受資本市場追捧的“題材”“概念”“市夢率”“想象型增長空間”之外,并沒有耀眼的業績。以博雅干細胞為例,交易估值較其賬面歸屬母公司股東凈資產約8771萬元評估增值約18.88億元,增值率高達2152.83%。
三高并購在2013至2016年中國并購潮中非常普遍,尤其兩起并購的時間2015年,正是這次并購潮中的高潮。并購潮中,上市公司對這些“市夢率”類目標公司非常熱衷,追漲情緒高漲,市場也失去了理智,給出高估值。而評估公司往往迎合甲方金主的期望,可以找出很多令人信服的理由給出高估值。之后就是高溢價,打著“輕資產”的旗號,并購交易價格順理成章地脫離了目標公司的可辨識資產價格,溢價統統計入一個叫做“商譽”的資產。2013至2016年中國并購潮形成的商譽資產高達萬億元以上。
對上市公司來說,唯一能夠制約交易對手的方法,就是要求他們做出高業績承諾,而后監督和執行這些業績承諾的兌現。在新日恒力收購博雅干細胞時,博雅干細胞的實際控制人許曉椿曾做出高業績承諾:博雅干細胞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合并報表口徑下,實現歸屬母公司股東凈利潤分別不低于3000萬元、5000萬元、8000萬元、1.4億元。
這輪并購潮業績承諾的未完成率大致在25%-30%之間,這其中還不包括交易雙方彼此默契配合完成業績承諾的情況。筆者估計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業績承諾是沒有真實完成的。
以上述兩個案例為例,博雅干細胞在2015年、2016年實現扣非后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分別約為2599.62萬元和2877.35萬元,僅分別完成業績承諾的86.65%和57.55%。到了2017年上半年表現更是糟糕,只到了承諾值的四分之一。而上海新高峰在勉強完成業績承諾之后,業績馬上變臉。
圖窮則匕現。當業績無法完成時,當后續業績變臉時,必然引發上市公司判斷此前買貴了,這時,上市公司控制人必然將全部過錯歸結于目標公司出售方欺騙所致,定義出售方為“騙子”。試想一下,面對一個“騙子”騙取了自己巨額的錢財,導致自己巨額經濟損失,會是怎樣的一種憤怒狀態,這種情緒之下,雙方之間必然爆發水火不容的激烈沖突。
“三高”并購,本質上就是一場欺騙,而欺騙者并非是出售方一方,買家也是一種自我欺騙,雙方都陶醉在未來一帆風順的好運和持續增長的神話中,沉醉在共同的欺騙和自我欺騙的迷局中不肯醒來,直到目標公司業績變臉時,現實的殘酷才驚醒了買方。
跨界并購惹的禍
并購是為了追求協同效益,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證明橫向并購更容易產生協同效益,道理很簡單,避免了一定范圍的自相殘殺(惡性競爭),雙方的資源可以進行一定的整合,產生規模效益,同時可以避免重復投入帶來的浪費。
2013至2016年中國的并購潮中,橫向并購并沒有引起上市公司的興趣,反而是跨界并購吸引了眼球。韭菜們也更容易為此埋單。
新日恒力作為生產鋼絲繩的傳統企業,收購博雅干細胞是典型的跨界并購,并購之初,跨界轉型為上市公司帶來了各種熱議和期待。一場喜樂之后,跨界并購的結局大家都看到了。博雅干細胞與上市公司形成了一系列的糾紛(包括失去控制),最終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向上市公司購買了博雅干細胞的股權,幫助上市公司止損。博雅干細胞從一個香餑餑到燙手的熱山芋,也就短短的兩三年時間。
亞太藥業與并購的目標公司新高峰之間,亞太藥業主要從事醫藥制劑業務,新高峰屬于CRO服務為主。并購之初,2016年11月1日某證券公司研報以《亞太藥業(002370)母公司業績低于預期,CRO延續快速成長態勢》為題,其中將新高峰夸成了一朵花。CRO已成公司戰略主業,為新藥品政策明確受益標的。CRO行業處于醫藥研發產業鏈核心位置,為新藥研發不可或缺。上海新高峰已累積服務了550多個項目,其中450多個為創新藥CRO項目,中報顯示在執行項目共計330項左右,公司已成為創新藥CRO服務領域的行業領先者之一。考慮到上海新高峰已通過GRDP管理體系,籌劃、參與并組建GLP、GCP和GMP產業聯盟,并積極籌建一致性評價技術平臺和醫療科研服務與精準醫療技術服務平臺,為新藥品政策如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和上市許可人制度的明確受益標的。
醫藥制劑和CRO還是有很大的區別,從事醫藥制劑的亞太藥業并購新高峰,無疑也是一種細分領域的跨界。跨界的買家往往是霧里看花,要參與和引領目標公司,存在一定的難度。外行領導內行,也會遭遇內行的激烈反抗。上述兩家上市公司都與并購目標公司原大股東爆發過激烈的沖突。
忽視治理惹的禍
并購是一場資產和股權的交易行為,這沒錯。被忽視的是,并購也是一場目標企業公司治理的變革,是一個團隊對另一個團隊的替代。2013至2016中國并購潮中,資產和股權的交易行為,過戶手續基本都完成了,即所謂的“交割”。但目標企業公司治理的變革,做得好的不多,多數因為業績承諾需要由目標公司原來的大股東(多兼任管理層主要人員)來完成,上市公司對目標企業進行公司治理大變革的,很少立即發生。實際控制權沒有被上市公司掌握,而是由原來的大股東繼續掌控。博雅干細胞管理層拒絕審計行為,新高峰管理層違規擔保問題,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失控事件警示上市公司,對于有業績承諾義務的目標公司管理層,不能一概聽之任之。并購之后,要主動進行目標企業公司治理的變革,盡快完成對目標公司的控制及整合。
反思上市公司對并購目標企業失去控制問題,找出根源也就解決了一半以上的問題。杜絕“三高”并購是根本,只有合理的估值、合理的價格、合理可行的業績承諾,才會讓并購各方心平氣和地開展并購的各項事務,這是前提和基礎。慎重開展跨界并購是避免紛爭的有效方法。在并購之后,要立即開始公司治理的變革,完成對目標公司的控制和整合,避免為了完成業績承諾,而對目標公司原來的管理層聽之任之,最終導致不可挽回的失控局面。
路漫漫其修遠兮,資本市場因并購而引發的公司治理問題,值得我們不斷深度研究與實踐探索。
作者供職于上海市中浩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