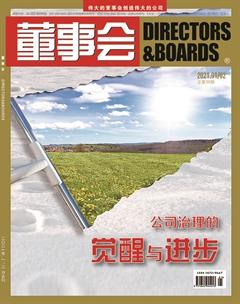君明樂官:戰略決策的啟示
吳捕快

魏文侯,戰國時期魏國的開國君主,魏國百年霸業的開創者。魏文侯選賢任能,手下聚集了一大批響當當的人才,文有翟璜、李悝,武有樂羊、吳起,讓人驚嘆的是,這些人才全被魏文侯收入麾下,并且各自發揮著光與熱,更為難得的是,這些人才在魏文侯在位時期鮮有不和,可以說魏文侯是一個相當出色的老板。
在《戰國策》與《資治通鑒》里均記載了魏文侯與田子方一起喝酒的小故事。喝酒時,宮廷音樂在旁伴奏。魏文侯忽然說:“編鐘的聲音有點不協調,左邊的高了。”田子方沒有回答,只是笑了笑。魏文侯問:“你為什么發笑?”田子方說:“臣下聽說,作為一個君主,只要懂得任用樂官,不必懂得音樂(君明樂官,不明樂音)。現在國君您精通音樂,我擔心您會疏忽了任用官員的職責。”魏文侯恍然大悟,“說得好呀。”
田子方是孔子弟子子貢的學生,道德學問聞名于諸侯,魏文侯聘他為老師。田子方這段論述很精彩,他認為做君主的,主要任務應該是選拔任用樂官,而不是自己研究音樂的具體內容。這是有道理的,君主要管理國家各方面的事務,不可能什么都學,什么都懂,什么都精通。而且把過多精力花在具體工作上,就會影響宏觀思考和決策。所以應該任用適合的專家人才去管理國家的各方面事務,而不必親力親為。
漢代開國皇帝劉邦曾經說過,“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由此可見,劉邦的想法和田子方倒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企業的高級管理層的戰略決策也非常有借鑒意義。
“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公司的高級管理層尤其是最高領導者可能是某方面的專家、學者,但不可能是全才型的“百事通”。很多時候,我們不怕不懂,因為知道不懂可以“知恥下問”,可以學習。甚至也不怕不懂裝懂,裝懂畢竟心虛,不會胡亂拍板。最怕自認為自己的本事隨著職務長,脾氣隨著官位長,不管在什么專業,無論在什么領域,都自命不凡、底氣十足,這樣的話,很容易導致公司在戰略決策時“拍腦袋”。
山東三株藥業董事長吳炳新曾經自述“15大失誤”,其中有一條就是“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有待于進一步加強。過去,我們采取的是中央集權制,決策權過分集中,缺少智囊團,所以決策出現了一些失誤,對公司的整體影響很大。”
無獨有偶,沈陽飛龍集團的總裁姜偉在公開承認的20條失誤中,第一條便是“決策的浪漫化”,第二條是“決策的模糊性”,第三條是“決策的急躁化”。
巨人集團的史玉柱也有過類似的總結:“巨人”的決策機制難以適應企業的發展。巨人集團也設立了董事會,但那是空的。我個人的股份占90%以上,具體數字自己也說不清,財務部門也算不清。其他幾位老總都沒有股份。因此在決策時,他們很少堅持自己的意見。由于他們沒有股份,也無法干預我的決策。總裁辦公會議可以影響我的決策,但拍板的事基本由我來定。現在想起來,制約我決策的機制是不存在的。這種高度集中的決策機制,在創業初期充分體現了決策的高效率,但當企業規模越來越大、個人的綜合素質還不全面時,缺乏一種集體決策的機制,特別是干預一個人的錯誤決策乏力,那么企業的運行就相當危險。
從眾多企業的發展史中,可以看出,公司創業初期,一把手獨裁,是最常見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顧企業發展階段,一直把公司決策的決定權維系在一個人身上,是非常危險的。無論這個人原來的決策多么英明,都很難避免下次不犯錯誤。這對企業的長遠發展來說是非常致命的。
按照學者楊少杰的觀點,類似于史玉柱的這種決策模式屬于單人決策模式,所有權力高度集中于單一決策者——史玉柱手上,這種公司治理結構中出現的董事會,可以稱之為單一型董事會。單一型董事會的設置更多是為了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因而是一種形式上的決策機構,雖然公司治理結構也有基本的運作流程與規章制度,但基本形同虛設,董事會僅僅發揮“橡皮圖章”的作用。
隨著商業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越來越強,戰略型董事會的概念應運而生。一般認為,就股權結構與董事會類型的匹配度而言,戰略型董事會主要適用于股權分散或股權中度集中的企業;就企業規模及其所處的發展生命周期而言,戰略型董事會適用于進入成長期后期或成熟期的企業;就行業領域的復雜性與變動性而言,戰略型董事會適用于不可預測性強或可塑性強的行業。
戰略型董事會能否發揮作用,核心問題在于董事的履歷和能力。日前,中芯國際新任副董事長蔣尚義上任,聯席CEO梁孟松鬧出了辭職風波。據外界猜測,估計是梁孟松與蔣尚義在技術方向上的理念不同。而如今,二人的爭論已經有了結果,那便是在先進封裝、先進工藝兩方面共同突破。這樣的結果,皆大歡喜,中芯國際的戰略也變成共同突破。蔣尚義是專家,進入中芯國際的董事會,必然能夠優化中芯國際的董事會治理結構、提高董事會科學規范決策能力。
高效發揮戰略董事會的作用,必然需要優秀董事的加入,這一點如果實現比較困難,那不妨考慮通過增加外部董事來改變董事會結構。引進比現有董事會成員專業能力更強、更懂經營的優秀外部董事,不僅能把最高管理者不切合實際的想法扼殺于萌芽之中,更關鍵的是能夠發揮外部董事不一樣的指導作用,更好地發揮董事會的決策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