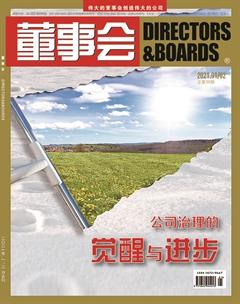適度分權,經濟不景氣時更具競爭力
Philippe Aghion和Isabelle Laporte

想象一艘船在海上航行,暴風雨越來越猛烈,船隨時有沉沒的危險。這時候,是授權船員盡一切努力拯救船只更好,還是每一個決定依然要由船長和高級船員做出?
同樣,在經濟嚴重低迷時期,企業組織的最佳形式應該是什么?當然,如果要做出一些艱難的決策,譬如裁員,那么將權力集中在公司高層是明智的。但更需要重視的是,一旦環境出現動蕩和快速變化,那么對企業來說,直接面對市場的一線管理人員往往能最快獲得更有價值的信息。
事實上,在2009年大衰退最嚴重的時候,經濟學人智庫對高管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公司的決策權更加集中在最高管理層。其邏輯是:為了能夠重點支持“公司全局性項目(而非個別分支或者單元)”。不過,在三個月前的另一份報告中,經濟學人智庫指出,“在當前的衰退中,企業需要應對更多的不確定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中央集權并不會帶來成功。”
誰來負責和決策:船員還是船長?
一篇題為《動蕩、企業分權與不景氣時期的增長》(2021)的新論文表明,大衰退對分權企業的影響往往較小。當市場充滿不確定性時,經常需要在一眨眼的時間內做出決定。由于一線管理人員擁有著最準確和最新的信息,所以他們往往是公司里面最能夠及時應對變化并作出反應的人。因此,在充滿不確定的衰退環境中,授權他們的公司獲得了優勢。
這篇論文研究了兩個大的微觀數據集:一是來自10個經合組織國家(包括法國和日本)的調查數據;另一個是美國制造業工廠的數據。
暴風雨越猛烈,越有理由分權
在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行業,分散管理的公司在所有方面都勝過集中管理的競爭對手:銷售、生產力,更重要的是生存力。所謂的“沖擊更大”,是指危機下最容易造成銷售下降、產品流失的行業,譬如耐用消費品行業。產品流失是一個重要標志,代表著目標客戶放棄現有產品、選擇新產品的速度。
受危機影響最嚴重行業的國際樣本中,分散管理的公司銷售額下降了8.2%,而集中管理的企業銷售額下降了11.8%,有顯著差異。美國本土樣本中,也存在類似的差異。
有趣的是,這種銷售表現上的差異僅限于危機時期:出現于2008年,曲線在大約5年后趨于一致。因此,在非衰退時期,支持或反對去中心化的決定很難說誰對誰錯——至少純粹從商業角度來看是這樣。例如,一個集中化管理的公司可以形成規模經濟,或者,它可以避免某個特定業務部門蠶食銷售份額等。但當出現危機時,權力分散的公司表現得更好,特別是在最艱難的環境中。
在大蕭條時期,集權公司銷售額的縮水幅度是分散管理競爭對手的三倍。在受打擊最嚴重的行業中,分權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顯著提高,生存概率也明顯增加。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在這一特殊時期,一線管理人員決定產出(銷售和退出新產品)的能力,比他們控制勞動力和資本投資等投入的能力,更加重要。
這對企業和政策制定者意味著什么?
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經濟低迷目前似乎有些緩解,企業改變管理風格是否為時已晚?并不盡然。通常,大型危機其實為企業重新審視自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時間窗口。經濟繁榮時期,每家公司都優先發展業務、為客戶服務。而經濟衰退降低了公司審查其經營方式的機會成本。這就是所謂“壞時期的優點”。
事實上,上述研究數據表明,大衰退之后,很多企業并沒有立即采用新的最優(更分散)組織形式,最終都是在一系列經濟沖擊下逐步實現權力下放。
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這些發現做些什么呢?很明顯,政府的作用不是告訴企業應該如何經營,政府能做的是培養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因為員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分散管理的結構就越有吸引力——公司有更多可靠的員工可以依靠,做出明智的決定,無論是否處于經濟低迷時期。相反,未受過足夠教育的勞動力更適合“森嚴”的等級結構,這種結構屬于過去的時代,曾讓亨利?福特等早期實業家受益。除了充分考慮本國教育體系之外,政府還可以通過撥款或稅收抵免等方式,支持企業開展內部培訓。
此外,各國政府還應該執行促進競爭的政策。這將促進更有效的企業組織結構的出現,通常轉化為更分權的公司。事實上,任何鼓勵創新和創造性破壞的政策都可以為權力下放提供正確的土壤。
超越經濟學范疇的價值:改善社會
正如多位研究人員記錄的那樣,在美國和英國已經出現了一種組織扁平化的趨勢。
越來越好的信息技術正在使得公司變得更加“平坦”,給了員工更多的自主權和更大的控制范圍。早在1991年出版的經典著作《改變世界的機器》(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中,就探討了精益制造如何推動分權趨勢。
除了在經濟低迷時期提供的明顯商業優勢,扁平化的組織還能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這些工作與更高的薪酬、更好的培訓、更好的工作保障、更好的晉升機會以及最終更好的社會流動性有關。當然,扁平化組織的運動也有可能使其他利益相關者受益。例如,更多的創新產品可以進入市場。
商業環境越來越像洶涌的大海,風暴不斷潛伏在地平線上,企業必須隨時準備應對危機。今天是健康危機,明天可能是環境危機。將決策權下放給聰明、忠誠的“接地氣”管理者的公司,最有可能達到理想的目標。
來源:歐洲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