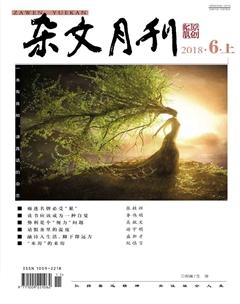鮑翅之珍
馮磊
讀《隨園食譜》,看到一段文字:“海參、燕窩,庸陋之人也,全無性情,寄人籬下。”袁枚把燕窩、海參比作庸庸碌碌之才,自然有他的道理。
國內的宴席,總以燕窩、魚翅、鮑魚為珍品。中學時代,生物老師曾教導我們:“燕窩、魚翅,無非是些普通軟骨、蛋白質一類的東西。”———說歸說,有家長宴請,他還是逢叫必到的。
燕窩、魚翅自身的味道并不怎么樣。“翅饌的美味,皆賴雞腿和火腿熬出”,真正提味的是雞湯和火腿。但我們習慣性地認為,這都是些陪襯。
雞肉和火腿價格低廉。畢竟,這世上活蹦亂跳的雞和滿地走的豬太多了,能值錢嗎?!
幾十年前,來自紹興的周大先生說:“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水果店頭,尊為膠菜。”這南方人眼中的稀奇之物,在北方每年不知被豬拱爛多少!但是有人稀罕,畢竟“物以稀為貴”。倘若燕窩和鮑魚遍地是,瘋子才會花大錢去買。
這樣無情地討論美食,大廚們會舉手抗議的。不僅如此,那些習慣了享用鯊魚軟骨、海味蛋白質的人,也會憤憤不平的。
遭人質疑的不僅是燕窩、魚翅,還有茄子。
《紅樓夢》里,賈母讓王熙鳳夾一塊茄鲞給劉姥姥吃,劉姥姥品嘗了一下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
劉姥姥家后來當然沒有只種茄子。她感慨一番后,鳳姐兒交代了這道菜的做法:“你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簽了,只要凈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肉并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釘子,用雞湯煨干,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
劉姥姥道:“我的佛祖!倒得十來只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
一只普通的茄子,用雞肉、蘑菇及其他佐料眾星捧月一般幫襯了,輕而易舉就把大家的嘴巴給騙了。這種糊弄嘴巴的把戲,一度讓多少草包成為圣賢。
燕窩、魚翅和茄子,說到底是一路貨色罷了。
十余年前,網上流傳過一份權威人士的研究成果。大致是說,那些讀書拔尖的學生,后來在社會上混得大多平平;倒是一些學業稍次但會來事的學生,多成為成功人士。
作為局外人,我不知道這項研究可信度究竟多高。我只是想,如真是這樣,恰恰說明問題所在:真才實學在貶值,口水和潛規則在盛行。真真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