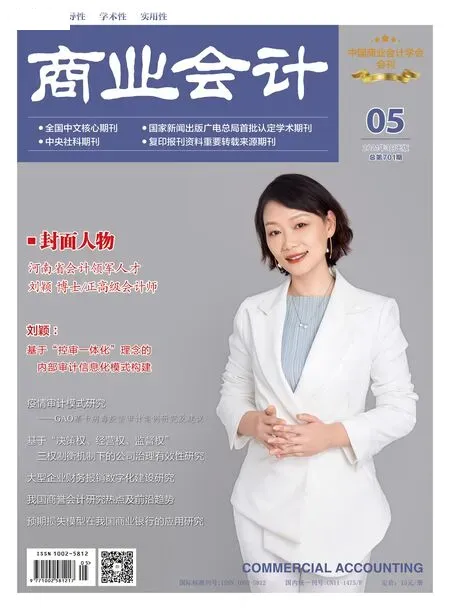資產減值會計存在的問題與改進
陳茂麗 林斌(教授)(江西農業大學 江西南昌 330000)
互聯網經濟的迅速發展,科學技術質的飛躍,在給生產、生活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也在向我們傳遞著一個訊號——資產的加速貶值。作為創造利潤的主要動力——資產在企業中無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上市公司數量的有限性和上市條件的嚴苛性,使得上市公司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根據規定,我國被冠以“ST”的上市公司,只要能使財務報表完成扭虧為盈就能成功摘帽。上市公司要想向利益相關者傳遞信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過財務報表的形式向預期信息使用者披露,其中凈利潤是最受關注的點之一。而影響凈利潤的一個重要且靈活的因素是資產減值準備的多少。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越多,企業的凈利潤就越少,相反轉回的資產減值準備越多,企業的凈利潤就越多。當然對于利潤操縱學者已經做了不少研究,本文不再贅述。本文重點介紹存貨和固定資產減值會計處理存在的不足以及如何改進。
一、減值會計存在的問題
(一)存貨減值會計。根據現行準則的規定,存貨在期末計量時應當按照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孰低原則進行計量。當其可變現凈值低于成本時,應當計提存貨跌價準備,而在存貨銷售時,要把前期計入存貨跌價準備的金額予以轉銷,也就是存貨跌價準備從原來的貸方轉到了借方。
例1:晟信公司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期末對存貨采用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孰低原則進行計量。2019年末該批存貨的賬面余額為1 000萬元,可變現凈值為900萬元。這表明存貨的可變現凈值低于成本,應當對該批存貨計提存貨跌價準備。假設晟信公司在此之前未計提過任何減值準備,則晟信公司2019年的賬務處理如下:
借:資產減值損失 1 000 000
貸:存貨跌價準備 1 000 000
假設晟信公司于第二年(2020年)將上述存貨全部賣出,則相對應的存貨跌價準備應該予以轉銷,會計處理如下:
借:主營業務成本 9 000 000
存貨跌價準備 1 000 000
貸:庫存商品 10 000 000
倘若晟信公司2019年沒有對該批存貨計提減值準備,則2020年銷售該批存貨時,所編制的會計分錄如下:
借:主營業務成本 10 000 000
貸:庫存商品 10 000 000
以上的兩種方式對企業利潤的影響并沒有什么區別,都是減少了利潤1 000萬元。相較于非減值會計而言,減值會計將負的100萬元利潤提前一年確認,這也正是體現了減值會計的謹慎性原則。
由前述可知,減值會計與非減值會計的處理對企業的營業收入沒有什么影響,而作為銷售毛利的被減數“營業成本”而言,卻有所不同。在減值會計下,企業2020年的營業成本是900萬元,而在非減值會計下,企業的營業成本是1 000萬元。顯然減值會計的處理虛減了主營業務成本,虛增了企業的銷售毛利,改變了主營業務收入與主營業務成本的配比關系,歪曲了商品銷售的獲利能力,直接傳遞了公司“產品價格競爭力提升”“成本控制成效顯著”等“利好”的錯誤信息,夸大了公司主營業務的“能力”,同時也會被上市公司管理層在業績歸因時用于“邀功請賞”的依據。另一方面也會誤導擬通過這些財務信息進行投資的投資者的決策。
(二)固定資產減值會計。根據現行準則的規定,若是固定資產有計提過減值準備,則固定資產在計算折舊額時,所采用的基礎就應當是將計提的這部分減值準備金額扣除后的余額。并且由于固定資產的數額較大,為了避免管理層利用這一規則進行利潤操縱,減值準備金額一經計提以后會計期間都不允許轉回。
例2:晟信公司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公司有一項固定資產原值為50萬元,預計使用年限為5年,預計凈殘值為0,公司采用年限平均法對其進行會計核算。假設2019年前對該固定資產沒有計提過減值準備。
固定資產隨著不斷的消耗,需要對其計提折舊。若是有計提過減值準備需要按照按減值后的賬面價值來計算,這也就意味著計提了固定資產減值準備后的年份的折舊費用相較于之前的年份會有所下降。根據表1,企業的具體會計處理如下:

表1 固定資產折舊情況表 單位:元
1.2019—2020年。
借:制造費用——生產成本——庫存商品 100 000
貸:累計折舊 100 000
2.2020年計提固定資產減值準備。
借:資產減值損失 100 000
貸:固定資產減值準備 100 000
由于2020年計提了減值準備,因而在后面的年份固定資產的折舊金額將會減少。
借:制造費用——生產成本——庫存商品 66 700
貸:累計折舊 66 700
通過上述的處理可知,采用減值會計,實質就是將本應在未來三年內分攤的10萬元通過確認資產減值損失的方式提前到2020年確認,這樣的會計處理也是符合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中的謹慎性要求的。
但是上述會計處理同樣引起主營業務成本虛減而衍生出一系列不利影響。減值會計導致產品成本構成因計提減值準備而被歪曲,在向信息使用者傳遞錯誤的信息時,更是不利于為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提供真實的成本信息,從長遠來看,會阻礙企業的發展。
(三)減值會計中的主觀性太強資產是否要計提減值準備,主要取決于資產的賬面價值與可收回金額(可變現凈值)的對比,若前者大于后者,則將其差額確認為減值金額。資產的歷史成本記錄在前,經濟持續發展、技術不斷進步、設備的加速老化都將導致資產存在嚴重的貶值,這就使得資產減值的確認更加復雜,因而所需的時間也更多。對于可收回金額的確定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計提的金額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主要依靠的是會計人員的判斷。主觀上會計人員可能由于缺乏應有的職業道德會根據公司的“需要”靈活計提公司的資產減值,客觀上由于會計人員的專業勝任能力不足,無法對資產減值金額的多少進行準確的計量,加之我國價格機制的不完善都可能導致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依據不準確。
(四)內部控制不夠完善。當前我國很大一部分企業的內部控制還不夠完善,還有部分企業即便制定了內部控制制度,也沒能堅持執行。需要計提減值準備的資產、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具體計提金額、以及計提的方法等都沒有得到監督,具有一定的隨意性。
(五)依然存在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出于謹慎性原則,企業要定期對資產進行減值測試,并相應地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由于可收回金額的不確定性,給企業留下了利潤操縱的空間。另一方面則是我國會計準則對減值會計,只規定了一些長期資產的減值不能轉回,而對于一些短期資產,比如存貨和應收賬款則沒有此項規定。這也就意味著雖然企業想通過長期資產進行利潤操縱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抑制,但是還是可以利用短期資產來實現。另外,對于長期資產通過實質性交易的轉回也沒有作規定,這就使得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資產重組、資產的變賣等方式來實現盈余管理的目的。
(六)選擇性信息披露,使得信息披露缺乏完整性。大部分企業對于信息披露的重視程度不夠,他們只是把信息披露作為一項額外的工作,而沒有結合自身的特征進行披露。對于一些較為重要的資產,會進行披露,而相對不重要的資產會選擇少披露,甚至不披露,這樣會導致報表使用者無法獲得充足的信息,從而導致錯誤決策。
(七)監管難度大。存貨的減值與否是看存貨的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固定資產的減值與否看的是固定資產的賬面價值與可收回金額的對比,而其中的可變現凈值和可收回金額的確認和計量都依賴于會計人員的專業能力和職業判斷。如若是會計人員的專業能力不足、所選用方法不正確、職業判斷不準確、對企業的實際情況了解不夠深入等都將導致結果偏離實際。也正因為如此,監管者要監管到方方面面,無形之中加大了難度。
二、減值會計的改進
(一)對存貨減值會計的改進。當計提了減值準備的存貨要銷售時,存貨跌價準備應當通過資產減值損失轉回,而不是通過沖減主營業務成本來實現。承接例1,具體的會計處理如下:
借:主營業務成本 10 000 000
貸:庫存商品 10 000 000
同時
借:存貨跌價準備 1 000 000
貸:資產減值損失 1 000 000
改進后的處理方法,一方面保持了會計的謹慎性——2019年存貨發生了減值,還是照實在利潤表中予以披露,另一方面也還原了營業成本的真實性,使得營業收入和營業成本之間的關系能得到正確的反映,進而正確向投資者傳遞企業的經營能力,為其投資決策提供了依據。
(二)對固定資產減值會計的改進。對于固定資產減值后計提折舊時可以按減值前的進度計提折舊。承接例2,2021—2023年間的折舊如下:
借:制造費用——生產成本——庫存商品 100 000
貸:累計折舊 100 000
同時按照相應比例將固定資產減值準備轉入存貨跌價準備
借:固定資產減值準備 33 300
貸:存貨跌價準備 33 300
因為固定資產的部分取得成本已經結轉入存貨(制造費用、生產成本、庫存商品),相應的固定資產減值準備也應同步轉入存貨跌價準備,這樣的處理在更加簡便的同時也更符合實物流轉與價值流轉的一致性。相應的,在商品出售時:
借:主營業務成本 100 000
貸:庫存商品 100 000
同時,
借:存貨跌價準備 33 300
貸:資產減值損失 33 300
這樣的會計處理,保持了作為企業盈利根本的主營業務收入與主營業務成本信息的真實客觀,有利于向外界傳遞穩定、客觀、有用的會計信息。同時,改進前后企業的利潤總額并不會發生變化,報告了前期計提減值對當期利潤的影響,利潤構成信息更加明晰。因此,改進后的會計處理將提升會計信息的可靠性、相關性、可比性、明晰性,不改變原有信息的謹慎性,進而實現更加決策有用的財務報告目標。
(三)提升會計人員的專業勝任能力和職業道德。資產是否發生減值、減值的金額是多少、是否應該轉回減值準備等信息都需要會計人員的判斷,這就要求企業在選拔人員時要多考慮候選人的專業勝任能力。鑒于獨立性的重要性,企業不僅需要崗前培訓,上崗后也應當定期對會計人員進行培訓,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同時要求財會人員必須要樹立“終生學習”的觀念,只有準確地了解新的會計政策,才能做出正確的會計處理。企業還應當積極引進復合型會計人才,為企業的發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四)進一步完善減值會計。盡管相對于舊準則,新準則已經有了一定的完善。但準則中“明顯高于”“大幅度”等字眼還是不夠清晰。各個行業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論。所以在準則的制定過程中應當對各行各業提出具體的規定,減少企業利用準則漏洞的概率。此外,還可以對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和轉回的金額及其時間進行限定,最大限度地減少利潤操縱的可能性。
(五)加強對信息的披露。為了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諸多問題,會計準則應當完善披露的相關規定。對于上市公司資產減值計提的金額、計提的原因、哪些符合減值跡象、具體的計算方法以及這些操作對凈利潤產生的影響,都應當重點說明,并且提供完整的信息,便于信息使用者鑒別。
(六)增加企業的違約成本。利用互聯網的優勢,將各企業按所處的行業進行劃分,分別建立所屬行業板塊。對企業的行為進行一一評價并且逐一記錄,同時對舉報者給予一定的獎勵,這無形中會對企業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
加大懲戒力度,增加違約成本。當違約成本大于利潤操縱成本時,企業操縱利潤的動機就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對不遵守職業道德,沒有保持應有的獨立性的會計人員也應當給予相應的懲罰,情節嚴重者,可以取消其從業資格。尤其是對于CPA,必須從思想上和法律上加強引導,強化其審計監督職能。
(七)提高對現金流量表以及其他非財務信息的重視。企業能夠利用一些規則漏洞,對資產負債表、利潤表進行粉飾,但是這種方式對現金流量表卻往往不奏效。現金流量表最需要關注的是作為造血功能的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非經營活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準確地判斷企業的盈利能力。若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凈流量小于凈利潤,則表明企業的財務報表存在一定的問題。非財務信息中諸如創新能力、人力資源、客戶與企業的合作年限、產品的質量等可以按比例納入業績指標,從而讓信息使用者對企業的情況有綜合的了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業盈余管理的動機。
三、結論與展望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相關的會計理論也在不斷完善,與此同時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也在提高。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不夠完善,仍然存在部分企業利用會計準則中的漏洞進行盈余管理。利潤的操縱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失真的信息,會誤導信息使用者的決策。同時,也錯誤地給企業管理層傳遞了不當的“利好”消息,造成管理層人員無法獲取企業的真實狀況,進而無法制定真正符合企業發展的規劃。過度的盈余管理更是阻礙了企業的發展,因此這一問題亟待解決。當然,任何問題的解決都是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這就要求會計人員要不斷地加強自身的綜合素質,企業要披露更多的真實可靠的信息,監督部門要充分發揮其作用,會計學界也更應當為之不斷努力、不斷研究,從而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