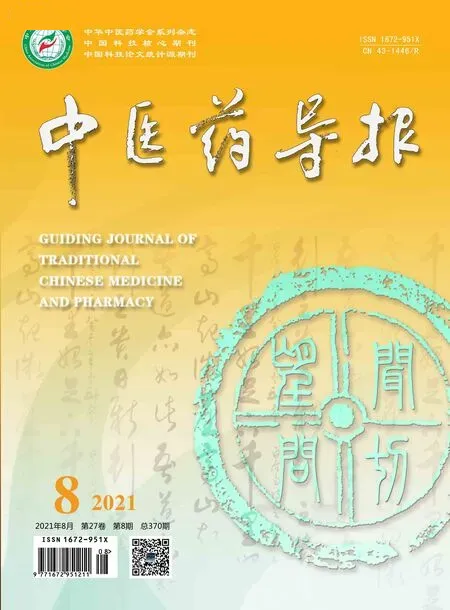中醫藥治療全髖關節置換術后疼痛的研 究 進 展*
孫 鈺,楊利學,譚龍旺,朱 偉
(1.陜西中醫藥大學,陜西 咸陽 712000;2.陜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陜西 咸陽 712000)
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是目前較為成熟的人工關節技術,1958年聚乙烯酸甲酯骨水泥首次應用于人工關節假體的固定,這成為現代髖關節置換術的標志,迄今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1]。隨著理念的不斷進步和技術的發展,其理論體系也逐步成熟。但由于術中創傷較大,出血量較多,THA術后疼痛長期困擾著患者,明顯降低了患者術后的生活質量,增加了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同時也成為不利于術后康復鍛煉的最主要原因[2]。
然而目前西醫針對THA術后疼痛的治療無規范統一的臨床方案,其術后鎮痛的方式多種多樣,多模式鎮痛在眾多鎮痛方式中已得到公認[3]。但多模式鎮痛花費較大、副作用較多,且極少有人針對多模式鎮痛的效果進行橫向對比,如臨床工作中很多人通過研究證明了圍手術期多模式鎮痛的積極作用[4-6],然而進行聯合鎮痛時,由于鎮痛藥的作用機制不同,未有明確的橫向研究說明療效更好和副作用較小的鎮痛藥搭配方式。而近些年中醫藥治療THA術后疼痛以其療效確切、副作用小、花費少等特點與優勢,其應用越來越廣泛。基于此,筆者總結并綜述了近年來國內外THA術后疼痛的病因、高危因素,以及中醫藥治療THA術后疼痛的作用機制。
1 THA術后疼痛的病因
THA術后疼痛的高危因素眾多,系統全面掌握THA術后疼痛的病因對其疼痛的治療具有重要作用。常見病因主要包括假體因素、手術因素、感染、患者因素等[7]。
1.1 假體松動 假體松動是THA術后疼痛較為常見的高危因素,GOODMAN S B[8]研究發現,THA術后人工假體松動的主要原因為術后髖關節間的摩擦與微動使其形成了微粒,同時微動與患者自身對于假體的異物反應形成了界面組織,最終在手術部位形成了骨吸收因子,導致了骨質的溶解破壞,使得假體松動。REGIS D等[9]對THA術后常見的假體松動類型及其引發疼痛的部位進行了統計,結果發現臨床上假體松動最常見于人工髖臼的松動和股骨柄假體的松動,而不同部位的松動也可引起不同的臨床表現,如腹股溝區域疼痛最常見于人工髖臼的松動,而大腿中后部的疼痛常見于股骨柄假體的松動,長柄假體松動則可能合并膝關節疼痛。徐衛東等[10]研究發現,THA術后由于體位的突然變化引發的疼痛,如從坐位到站立位或行走時的“開步痛”是術后假體松動的典型表現。莊華偉等[11]通過大樣本統計發現,高齡或體質量較大患者術后假體松動的概率較高。因此預防假體松動對于THA術后疼痛的控制顯得尤為重要。
1.2 手術因素 有部分學者[12-13]認為髓腔高壓癥亦可引起THA術后疼痛,在手術過程中由于擴髓腔的需要,導致大量骨松質、脂肪組織及骨髓堆積于髓腔內,而在安裝假體時強行封閉骨髓腔,造成了髓腔內的骨松質及血脂性滲出無法及時引流出髓腔,從而造成髓腔高壓進而引發疼痛。蒙輝能等[14]報告了4例由髓腔高壓引發THA術后疼痛的典型病例,經髓腔鉆孔減壓引流后短時間內疼痛得到緩解。同時手術過程中,假體柄在髓腔的占有率也是影響THA術后疼痛發生的因素之一。向孝兵等[15]在THA術后引發大腿疼痛的研究中發現,假體柄在髓腔內占有比率失當是引發THA術后疼痛的常見原因。文立成等[16]對35例THA術后患者進行隨訪時發現,假體柄的髓腔占有率為70%~90%之間的患者發生THA術后疼痛的概率最高,而假體柄占有率大于90%的患者則極少發生疼痛。
1.3 感染 感染是THA術后最嚴重的并發癥之一,同樣也是導致患者術后疼痛的主要原因。WU C L等[17]認為THA術后引發感染的危險因素有多種,如高齡、糖尿病、長期大量使用糖皮質激素等,同時手術過程中醫者操作不當、術后引流時間長等因素均為THA術后感染的高危因素。各種原因導致的術后感染會加重傷口周圍的組織水腫程度,升高血液中炎癥因子的水平,增加關節囊中的壓力,從而導致患者術后長時間劇烈疼痛。故術前對于這些高危因素的預防與控制既是減少術后發生感染風險的重要措施,同時也能降低術后疼痛的發生率。熊國忠等[18]針對髖關節置換術后疼痛的病例進行分析,結果表明術后感染是其獨立危險因素。嚴冬雪等[19]對髖關節置換術后感染的18例患者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患者均在手術后2個月內發生疼痛,同時伴有白細胞和血沉升高,傷口紅腫,運動困難等。顏斌等[20]統計了38例THA術后晚期疼痛的病例,結果發現26例患者的疼痛是由術后深部感染引發的。所以消除引起感染的高危因素、控制感染對于THA術后疼痛的預防具有重要作用。
1.4 患者因素 有研究表明[21],THA術后疼痛的發生主要與患者的年齡、性別、體質、基礎疾病、心理狀況等一系列因素有關。GAGLIESE L等[22]通過大樣本的統計發現,老年人常合并較多的基礎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等,這些基礎疾病常常成為THA術后疼痛的誘因。性別因素也可能成為THA術后疼痛的影響因素。ROSSELAND L A等[23]研究表明,女性患者術后疼痛的發生率往往高于男性,這可能與激素的分泌水平相關聯。VANDENKERKHOF E G等[24]研究發現,THA術前對于疼痛的認知也會影響術后疼痛的發生。故術前針對性的對患者進行相關知識的宣教,使患者在手術前就對術后可能發生的疼痛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可以極大減輕患者的焦慮感。適度的焦慮感不僅可以使交感神經處于適度緊張狀態,而且可以使患者迅速適應當前環境,但長期過度焦慮感可減少患者體內去甲腎上腺素的分泌,從而可引起靜脈血栓的形成、增加患者術后發生疼痛的概率[25]。故術前對于不同人群針對性地進行預防能夠明顯降低THA術后疼痛的發生率。
2 中醫學對THA術后疼痛的認識
中醫學將THA術后疼痛歸屬于“痛證”“痹病”的范疇,早在《靈樞·經脈》中針對痛證就有“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結、踹如裂”的描述。THA術后疼痛病位在筋膜與肌肉,即中醫學中“筋”的范疇。《素問·長刺節論篇》曰:“病在筋,筋攣節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靈樞·經筋》中言:“經筋之病,寒則筋急……”,痹病的發生因感受寒邪,寒氣阻滯氣血津液的運行,氣血凝滯,不通則痛。另一方面《類證治裁》云:“諸痹……良由營衛先虛,腠理不密,風寒濕乘虛內襲。正氣為邪所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滯,氣血凝澀,久而成痹。”由于THA術后正氣不足,氣血虧虛,營衛之氣不能調和,此時外感風寒濕氣,則會導致THA術后疼痛。即《醫宗金鑒·正骨心法要旨要》云:“若素受風寒濕氣,再遇跌打損傷,瘀血凝結,腫硬筋翻,足不能直行”。由此后代醫者在治療THA術后疼痛時多選用扶正補虛、溫通經脈、補氣養血為治療大法,多有成效。
3 THA術后疼痛的中醫藥治療
3.1 針刺與耳穴治療 早在《黃帝內經》中針對針刺鎮痛就有“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刺其郄中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的描述。近年來,THA術后疼痛的治療也逐漸主張用非藥物療法替代傳統的鎮痛藥物,而針刺、耳穴等中醫藥特色治療方式也成為了研究的重點[26]。
3.1.1 調控神經遞質分泌 中腦導水管處的某些特定細胞能夠通過針刺效應激活,進而分泌5-HT等神經遞質,最終達到抑制痛覺神經沖動傳導的作用[27]。張吉等[28]認為疼痛可激活腦內內源性阿片肽系統,使其增加腦啡肽、孤啡肽等一系列抗痛神經遞質的分泌,從而抑制痛覺傳導。而適當針刺治療不但能夠進一步刺激腦內內源性阿片肽系統,而且能夠促進脊髓中相關阿片肽系統釋放相應遞質,抑制神經末梢產生P物質,從而降低機體對于疼痛的反應[29]。周長勝[30]在研究針刺對THA術后高齡患者凝血與應激狀態的影響中發現,針刺特定穴位不但能夠調節年齡較大的THA術后患者的凝血,改善應激狀態,而且能有效降低下肢血栓的發病率,抑制術后疼痛的產生。李陽陽等[31]采用鎮痛泵聯合腕踝針療法對35例行THA手術的患者進行干預,結果發現相比于單純使用自控鎮痛泵的對照組患者,35例治療組患者術后疼痛感明顯減輕,且鎮痛藥用量與嘔吐等不良反應的發生率均低于對照組。
3.1.2 抑制疼痛傳導ROMOLI M等[32]運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證明了大腦軀體感覺特定區域與耳穴系統之間的聯系。ASHER G N等[33]通過耳穴結合生物全息理論發現,由于耳部分布有大量神經,若身體某部分出現病變時,此異常信號會通過相應神經傳導通路傳至耳部,因此認為耳穴刺激可以達到改善局部癥狀,調節全身機能的作用。現代研究認為,耳穴還可通過刺激下行傳導通路中的抑痛系統,減弱疼痛信號傳向脊髓,并同時釋放對機體起鎮痛作用的阿片肽,減輕疼痛[34-35]。USICHENKO T I等[36]采用耳穴治療THA術后患者,選取神門、丘腦等穴位,結果發現耳穴治療能明顯抑制THA術后疼痛,且未見明顯不良反應。GOERTZ C M等[37]研究表明,與對照組的傳統鎮痛方式比較,加用耳穴治療的實驗組獲得了更為理想的疼痛評分。李海洋等[38]通過薈萃分析發現,與對照組中的常規鎮痛手段比較,治療組中加用的耳穴鎮痛能夠更有效緩解THA術后疼痛,促進髖關節功能恢復,且能降低不良反應。
3.2 推拿治療THA術后局部血液循環障礙和致痛物質堆積是術后產生慢性疼痛主要誘因,而局部應用推拿手法可以有效增加患處血液循環,促進致痛因子吸收,調節神經遞質的分泌,介導神經-體液傳遞[39],從而達到減輕THA術后疼痛的作用。
3.2.1 促進血液循環、促進致痛物質吸收THA術后早期由于血液循環障礙導致局部血腫消散緩慢、致痛物質堆積,故產生疼痛,這恰好符合中醫學“不通則痛”的理論,而術后局部應用推拿手法不僅可以促進患處的血液循環,還可以提高人體對疼痛的耐受,促進炎性致痛因子的吸收[40]。推拿療法可促進患處血液循環,促進鎮痛物質的含量,加快致痛物質的降解吸收,提高患者的痛閾[41]。正如《素問·舉痛論篇》中所云:“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CHO Y N等[42]研究發現適當的推拿手法治療能緩解THA術后疼痛,改善患者的睡眠狀況,且隔日推拿1次的方式療效更為突出。
3.2.2 參與神經-體液調節 興奮性神經遞質與抑制性神經遞質是人體內調節疼痛的兩大神經遞質,疼痛信號的傳導通過二者共同完成。有研究[43]表明,一定深度和一定節律的推拿手法能夠激活手術后患者體內內啡肽的釋放,從而達到鎮痛作用。林彩霞等[44]通過動物實驗證實了推拿手法可明顯降低軟組織損傷家兔體內5-羥色胺、兒茶酚胺、乙酰膽堿等興奮性神經遞質的含量,同時能提高β-內啡肽等抑制性神經遞質的含量。推拿手法有利于術后疼痛的緩解,以及功能的恢復。
3.3 中藥治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云:“氣傷痛,行傷腫”,認為骨傷病發生后骨斷筋傷,血液妄行,氣滯血瘀,不通則痛。故中醫主張應以活血通絡、消瘀止痛為大法治療THA術后疼痛[45],正如《辨證錄·接骨門》中曰:“內治之法必須以活血祛瘀為先,血不能活則瘀不能去,瘀不去則骨不接也”。現代研究表明THA術后口服活血化瘀類中藥能夠擴張毛細血管、改善局部微循環、緩解術后疼痛、加快康復進程。
徐峰等[46]評價了活血止痛湯聯合舒芬太尼應用于THA術后鎮痛的療效,結果發現,與單用舒芬太尼比較,加用活血止痛湯能夠明顯降低患者疼痛,減少術后應激反應的發生率,且不良反應少。陳文輝[47]采用身痛逐瘀湯治療20例行THA術后的患者,觀察術后患處腫脹疼痛情況。結果表明,與氟比洛芬酯比較,實驗組患者THA術后疼痛發生率降低,且局部腫脹程度減輕。張從周等[48]采用獨一味膠囊治療THA術后患者,取得了較好的術后鎮痛效果,進一步證明了口服活血化瘀類中藥在THA術后疼痛治療中的積極作用。故對于THA術后疼痛而言,早期應用活血化瘀中藥能夠有效改善患處微循環,減少致痛物質堆積,對術后鎮痛、康復均具有較高的臨床價值。
4 中醫情志護理
中醫學認為,肝主疏泄,暢情志,具有調暢全身氣機的作用,情志異常可引起機體氣機不暢、臟腑功能紊亂,影響預后。而且對于一些行THA手術的患者,圍手術期焦慮是其產生術后多種并發癥的高危因素之一[49]。故采用移情相制、氣功調神的中醫情志護理方式對于抑制疼痛的產生具有較好效果[50]。有研究發現,與常規護理比較,中醫情志護理聯合穴位貼敷能夠促進THA術后患者胃腸功能恢復,加快術后康復進程[51]。蔣玉華等[52]對86例老年髖部骨折的患者進行為期4周的護理干預。結果發現,與實施常規護理干預的對照組比較,加用中醫情志護理的實驗組能夠明顯提升髖部骨折術后療效,改善髖部活動度和舒適度。王慧[53]將80例行THA術后的患者隨機分成兩組,分別采用常規基礎護理和加用中醫情志護理,結果發現中醫情志護理能有效減輕THA術后疼痛,促進患者康復,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5 小結與展望
引起THA術后疼痛的高危因素主要包括假體因素、手術因素、術后感染、患者因素等,故圍手術期對于這些高危因素科學合理的預防能夠有效減少THA術后疼痛及一系列并發癥的發生率。針刺、耳穴、中藥、推拿等中醫特色治療方式能夠通過不同作用機制對THA術后疼痛進行針對性治療,且在鎮痛的同時對于患者精神狀況、睡眠質量等均有雙向良性調節作用[54]。
隨著THA術后疼痛研究的逐步深入,治療理念也逐漸由研究單一性質的傷害性感受轉變為以患者情緒-術前認知-術后疼痛三位一體的多維度疼痛研究模式[55],這恰好符合中醫整體觀念的基本特征。故在臨床工作中我們應嚴格遵守鎮痛藥物的使用規范,對THA術后出現疼痛的患者善于運用中醫藥治療的方式,制定出個體化、針對性的治療方案。由于中醫藥治療THA術后疼痛的機制尚未得到全面闡釋,故哪些患者更能從中醫藥治療中獲益尚難以預測。這需要大量、規范的研究指導臨床,以便獲得更為滿意的療效。筆者認為,未來對于THA術后疼痛的治療必然是全方位、多模式、多維度的治療,而中醫藥以其獨特的優勢其應用前景也必將更加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