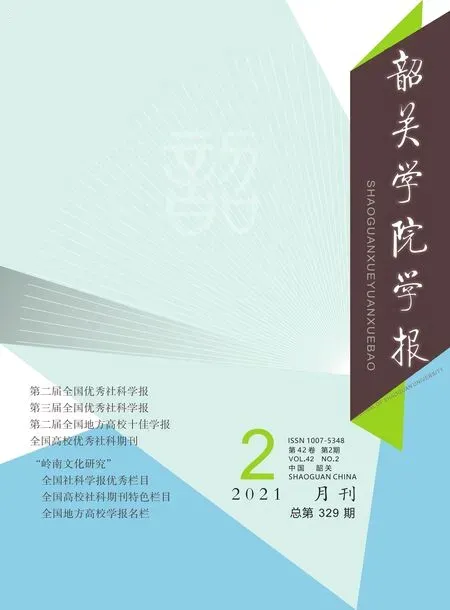本土自然資源在地方院校色彩風景教學中的利用
朱建高
(韶關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地方高校必須走特色化發展道路,與重點院校相比,地方高校存在著辦學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趨同化等問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進一步提出:“發揮政策指導和資源配置的作用,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質化傾向,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1]特色如果不基于區域化就如無本之木,難以生長。地方院校以自身特色構建區域高等教育優勢,促進高等教育區域化,高等教育區域化又反哺地方院校特色生長。
地方院校應該根據自身所處的地理環境、人文社會環境以及內部條件和環境,按照多樣性、特色性、協調性等原則,找準自己的位置,合理利用現有教育資源,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辦出自己的特色,高等美術教育特色課程更是離不開地方資源的有效利用。
色彩風景是高等美術教育中的必修專業課之一,旨在讓學生認識和運用自然風景中的色彩規律,培養他們敏銳觀察和表現自然美的能力,以及使用色彩表達自己的獨特感受和內在情感,提升其審美意識,激發其創造能力。
傳統的色彩風景教學習慣走進名山大川、風景名勝,尋找異于自己周圍的自然資源,以此激發學生的新鮮感,激起他們的表現欲,這比較符合心理學上的新穎原則。心理上的好奇感是心理認知和感知的原動力。也許正是出于這種心理,當下走馬觀花式的寫生遍地開花。“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是古人成功經驗的總結,色彩風景學習既離不開見多識廣的眼界,也不能忽視本土資源的利用。
吳冠中告誡我們:“我以往每到一地寫生,感到很新鮮,一畫一大批,但過后細看,物境新鮮(相對而言),畫境并不新鮮。”[2]我們常說的“行萬里路”可能只是在意追求腳下的路,而忘掉了心靈之路、思想之路。喬治·莫蘭迪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亞,終身幾乎沒有離開出生地,其一生的創作題材都是在畫著幾只瓶子和博洛尼亞郊外的風景,但是,這并沒有影響他成為20世紀最受贊譽的畫家之一 。美國藝術家安德魯·懷斯同樣如此。他曾說:“我連身邊的寶藏都還沒有盡心探測,為什么不應該在一個地方常住呢?”[3]當今,美術教育中的色彩風景教學,不少院校熱衷在名山大川設立寫生基地,師生不惜舟車勞頓跋山涉水,執念遠方的風景,卻忽略了近在咫尺、豐富的本土自然資源,這種舍近求遠的現象,值得深思。
一、遠方與近處的風景
名山大川、風景名勝有其獨特的美,而它們的美被人類發現不過區區幾千年。今天張家界得以名揚天下,最早緣于吳冠中的發現。他的文章《養在深閨人未識——失落的風景明珠》和他的眾多關于張家界的畫作,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湖南省才對張家界進行開發。經過多年努力,張家界逐漸成為著名的寫生基地和游覽勝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產目錄》。地理學家丹尼斯· 科斯格羅夫認為,風景是一種“觀看的方式”,它由特定的歷史、文化決定,那些依賴土地構造全部生活、把土地作為生計和家園的人們,并不把它當作風景,只有通過“外部人士”的視角,土地才被重組成了風景[4]29。或許本土身份限制了畫家的想像力!
其實,大多數人對于身邊風景的審美疲勞可以用心理學的原理來解釋:當刺激反復以同樣的方式、強度和頻率呈現的時候,反應就開始變弱,甚至產生厭煩、厭倦或麻木不仁的感覺。談到本土自然資源,對于色彩風景寫生而言,大多數人對身邊的事物熟視無睹,而對陌生的遠方充滿好奇和向往,從而忽視了本土資源的有效利用。
為了克服這種心理,激發學生的好奇心,筆者將教學大樓畫在黑板上,以教學大樓中心為原點,標上X、Y、Z三個坐標軸,然后,在建筑物周圍畫出半徑不等的類似衛星軌道一樣的圓形軌道,分別任意取點作為視點,畫出不同視點的教學大樓,結果有的像古代城堡,有的像童話世界,有的像八角獸……唯獨不像我們平時眼里的教學大樓!最后,要求學生根據自己的想像,畫出三個不同視點的教學大樓,并根據畫面需要添加色彩。這樣,一下點燃了學生的好奇心!以此為契機,要求他們開展校園及周邊色彩風景寫生。圖1就是筆者從學校畫室的窗戶里環視外面街區畫出的色彩風景作品,采取類似《清明上河圖》的視點平行移動方法。

圖1 紙本水彩 27.5cmX165cm
誠如E.H.貢布里希所言:“繪畫的全部歷史,就是將我們引向解放視點的歷史。”[5]視點定點和動點的運用決定著畫面的結構和面貌,視點上下左右移動,甚至形成不規則外形的寫生作品,這一方面,英國當代藝術家大衛·霍克尼進行過可供借鑒的探索。具體到室外風景寫生教學,筆者鼓勵學生外出寫生時帶上多個大小不等的方形畫框,這樣方便上下左右自由組合,形式靈活,可獲得一種意想不到的陌生感效果。
面對熟悉的風景對象,還可以在不同時間點、不同氣候條件下觀察,藉此獲得迥然不同的感受,激發無盡的想像和表現的沖動。忘掉那些既定的觀察模式和先入之見,應該無條件、專注地移情于對象。中國古代文人不僅畫日光之竹、月影之竹,還畫風中之竹、雨中之竹,相同的風景呈現完全不同的畫面效果,不同環境中的竹表達著不同的寓意,寄托著畫家不同的情思。
E.H.貢布里希在《藝術與錯覺》中認為,所謂“風景”其實就是觀察者從“土地”中選擇出一部分,按照構造“美好景象”的慣有概念進行一定的編輯和修改,從而形成的產物[4]11。圖2是筆者在同一地點、不同時間段觀察過的同一片“風景”:白天平淡無奇的街區,根本無法激起任何畫意;但當晚上萬家燈火亮起的時候,整個街區變成一片五彩繽紛的燈的海洋。白天的單調重復、雜亂無章,在夜色中變得異彩紛呈 ,大小、長短、遠近、疏密、冷暖、深淺等應有盡有。

圖2 紙本水粉 37cmX37cm
法國生物學家貝爾納說:“妨礙人們創造的最大障礙,并不是未知的東西,而是已知的東西。”[6]我們觀看世界和判斷是非的依據是頭腦中積累的知識,傳統的色彩風景寫生強調造型基礎及構圖、形態、空間、色彩等因素的作用,然而,科技的進步給我們帶來全新的視角,既可以深入細胞內部探究微觀世界,也可以遙望億萬光年的宇宙星空。現代科技使畫家站在一個更高、更新的視角,基礎造型元素較為容易被掌握,色彩風景寫生則需要改變觀察與表現自然風景的習慣。藝術家徐冰的作品《蜻蜓之眼》盡管與寫生關系不大,但是給寫生教學提供了無盡的啟示,全新的視角、觀念尤為珍貴。美術界經常就拍照與寫生爭論不休,大多數人容易將人眼功能與大腦功能混為一談,其實機械之眼是人眼的延伸,如同人足與車輪,不能有了車輪而不要人足,各有長短,關鍵要為我所用,各盡其能。
二、真實與謊言的表現
畢加索說,繪畫自身的價值不在于對事物如實的描繪。又說,藝術是揭露真實的謊言![7]我國明代畫家徐渭也說:“不求似而有余,則予之所深取也。”[8]
繪畫究其本質而言就是運用形態、色彩、肌理等視覺語言表達感受和感情。地質地貌、氣候特點無疑會給畫家帶來藝術感受和語言的啟示,色彩風景寫生本身就是體悟自然獲得啟示的方法,在寫生過程中發現新的形式、新的語言和新的意蘊,色彩風景教學特別強調的現場感就是要防止閉門造車,本土自然資源的利用貴在從身邊自然中獲得鮮活的發現。
(一)本土自然資源形態語言的發掘與運用
色彩風景寫生過程中,學生對大自然中景物形態的審視和提煉構成寫生作品的基礎,結合形態的判斷和提煉,將其匯集于一個畫面次序之中,用二維平面的形態完成三維自然的幻象。隨著學生形態語言的增加,色彩寫生能力的提升,其逐漸能夠構建個性化的形態畫面,本土自然資源與寫生者相互激勵,達到最佳結果。
能否將自然資源上升為藝術對象,發現它的審美內容,并轉換成一定的藝術形式,既包含了自然界本身的形態,也包含了藝術家的主觀觀念。每一張作品都是作者自我個性、觀察方法和形式感覺的視覺體現。魯道夫·阿恩海姆在《藝術與視知覺》中說:“藝術家與普通人相比,其真正的優越性在于:他不僅能夠得到豐富的經驗,而且有能力通過某種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體現這些經驗的本質和意義,從而把它們變成一種可觸知的東西。非藝術家則不然,他在自己敏銳的智慧結出的果實前不知所措,不能把它們凝結在一個完美的形式之中。他雖然能夠清晰或模糊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但不能把自己的經驗表達出來。一個人真正成為藝術家的那個時刻,也就是他能夠為他親身體驗到的無形體的結構找到形狀的時候。”[9]
在傳統的色彩風景教學中,往往偏重運用造型因素畫出眼睛所見的自然,甚至認為寫生就是訓練基本功,不惜千人一面,最終形成的一堆冰冷的、大同小異的畫面與藝術簡直是南轅北轍。其實,創作應該是常態!運用直覺判斷,遵循材料和形式規律,用一種特有的形態將它表達出來。色彩風景寫生是一個觀察自然風景的形態、結構、空間的視覺思維過程,給我們提供了運用形式符號描述和塑造思想的方法途徑。
大自然的無限豐富既給學生進行色彩寫生提供了豐富資源,又給他們提出了挑戰:如何從大自然中提煉出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個性的形態語言?這是色彩寫生中永無休止的追求。這種形態語言的提煉與運用彰顯出學生的觀察水平和技巧水平。傳統中國山水畫中所謂“披麻皴”“牛毛皴”“虎皮皴”等,即是古代畫家從自然中發現和提煉的一種山石形態元素,經過不斷傳承,演變成一種藝術語言,成為表現特定自然對象的藝術手段。名山大川往往經過眾多畫家的寫生和創造形成了約定俗成的表現語言,而本土自然資源的利用需要我們去發現和探索,大自然中的形式因素如線條、形體、空間、黑白、疏密均是如此。
丹霞地貌,不同于其他地方山石的棱角分明,其山石形體圓渾,大塊而流暢,有利于整體表現,但也容易流于空洞單調。在教學中,讓學生通過勾畫大量畫面形式草圖組織畫面形態元素,在大塊的山石形態中發現點狀樹林和山石上帶狀痕跡或者光照形成的不同明暗及山體前后重疊造成分割的形態等等,達到多樣統一而又有地域特色的畫面構成。同時,在草圖交流過程中,教師應該激發學生自己特有的形態感覺,并進行形態組合,使得色彩風景寫生達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境地。
(二)本土自然資源色彩語言的發掘與運用
人類在觀察和描繪大自然的歷程中,只是在19世紀光譜被發現后,才看到大自然豐富的光色現象,由此印象派得以誕生。之前“隨類賦彩”的類型化固有色觀念屏蔽了人類眼睛的條件色功能,而對固有色卻異常強化。
同樣,本土自然資源中豐富的色彩也被我們習慣性遮蔽,而選擇性地看到一般性色彩,而缺乏真正的、鮮活的當下“這里”的色彩。說到丹霞地貌,浮現在眼前的就是一種紅色山石,即使來到現場也會選擇性地看到紅色山石,畫出來的色彩寫生作品當然就是概念化的風景。但對于一個有創造力的畫家而言,每一次的色彩風景寫生都是展示其最新發現的機會,即使面對熟悉的本土自然資源,也能不帶偏見地去觀察和感受,而不是訓練某種固有的技法。馬蒂斯說:“我沒有先入之見地運用顏色,色彩完全本能地向我涌來”,“你永遠永遠不能忘記以一個兒童的眼光來看世界。”[10]
傳統風景技法都是前人從特定的大自然中得來匯聚而成,而且墨分五色、冷暖明暗也不是憑空而來。甚至有人問,為什么色彩豐富的油畫首先誕生在歐洲,而濃淡氤氳的水墨出現在中國?那是有地理位置與自然資源的內在決定性的,大部分歐洲陸地與太陽光呈約四十五度角,色彩飽和而豐富,而華夏大地雨水豐富、陽光充足、霧氣升騰,黑白灰層次豐富。
嶺南地區常年陽光充足,郁郁蔥蔥,青山綠水,五彩繽紛。學生外出色彩寫生如果只盯住表象細節不放,畫面極易支離破碎。因此,將畫面規格控制在邊長20厘米左右,使用大號畫刷(刀),抓住最基本、最抽象的形態和色彩,注意大色塊間的對比與協調,才能抓住最本質的地域特色。畫面內容雖然相對有限,但是畫面結構、線條、色彩同樣要求完整、均衡,應樹立作品意識,打破慣常規格下的慣性思維和制作模式,強化色彩感受和整體把握。圖3至圖8為學生色彩風景作業。

圖3 油畫風景 20cmX20cm 賴浩宇

圖4 油畫風景 20cmX20cm 區嘉嵐

圖5 油畫風景 20cmX20cm 劉莉娜

圖6 油畫風景 20cmX20cm 伍煒城

圖7 油畫風景 40cmX40cm 梁梓茵

圖8 油畫風景 40cmX40cm 呂秋娟
今天,生活的快節奏和空間的逼仄,人們的審美向簡約靠攏,視覺元素要求簡單輕松。色彩風景寫生宜采用簡化、規整化的表現方法,抽取與歸納自然中的視覺元素,根據形式規律重新排列組合。寫生較其他方法具有更加鮮活的生命力,這個時代給了色彩風景寫生廣闊的藝術空間,色彩風景寫生已經成為表達自我感受、審美取向的一種藝術形式。
(三)本土自然資源的心靈體驗與意境拓展
本土自然資源的表現不僅是外在形態、光線或者色彩的呈現,還是作者與之對話、體驗和審美的升華,是意境的拓展。《文心雕龍》說:“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水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11]色彩風景寫生從根本上講就是畫家觸及心靈的感受和發現,具有巨大的主體性。
塞尚說過,描繪自然并不是復制那些物體,而是實現一個人的感覺[4]236。在圣維多利亞山,塞尚完成大量風景畫作品時完全沉浸在那個場景中,藝術家與風景有著復雜的交互作用,他表達的已經不僅僅只是一個視覺感受,而是一個復合的心靈體驗——光線、顏色、氣味、聲音、觸覺等體驗的綜合感受,從而創造出一個極具個性的、完全不同于其他藝術家的意境空間。這也是那些走馬觀花式的寫生者不容易達到的境界。1890年至1891年間,莫奈完成了十幾幅《谷垛》,畫作中的那些谷垛就立在他吉維尼的房子后面的空地上。它們都是他熟悉的鄰居,即使再精確的攝影也無法表現這種復雜的體驗,人類感知世界光憑視覺是不夠的,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能力遠超乎想象。
在色彩風景寫生中,天,一定就是藍色的嗎?樹,一定就是綠色的嗎?……未必。如果寫生僅僅追隨照相機效果,沒有想象的參與與創造就不會有真正的藝術!寫生不是機械式反應。我們接受的視覺教育會影響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可能會將書本中的概念化為正常的模式,從而畫出類似的畫面,而缺乏真正來自心靈的觀察和體驗,我們看到的或者佯裝看到的其實是被知識和邏輯所設定的。

圖9 布面油畫 120cmX120cm
圖9是筆者夏天在中國最美小城粵北始興樟樹林公園的寫生,整個環境與冬天毫無關系——即使在冬天當地也極少下雪,色彩應該都是郁郁蔥蔥的綠色。這種突發奇想的變調色彩寫生可能受到現場某個因素的啟示,也許是當時酷熱中的一陣涼風刺激了我的神經,也許是酷暑環境的心理補償作用,也許是調錯顏色的偶遇,完全突破了慣常的色彩風景寫生方式,用一種新的方法利用了本土自然資源。
繪畫的真實不等同于客觀的真實。本土資源色彩風景寫生也不僅是追求客觀真實,它是一種具有精神內涵的發現和創造,只要有利于表達畫者的內心感受,有利于提高學生造型能力和水平,各種表現方法和手段都可以嘗試和運用。
三、求異存同的地域審美
中國地域遼闊,東西南北氣候條件、地形地貌、自然色彩等呈現出較大差異,給色彩風景寫生教學提供了就地取材的豐富資源。同時,相同地域的畫派及其經典作品也是本土自然資源利用的一種參照。
古今中外,不同地域產生了不同畫派,法國有楓丹白露畫派、加拿大有安大略湖七人畫派、中國有嶺南畫派。薛永年先生總結中國古代畫派時認為:中國古代的畫派,大略有兩種——一種是藝術傳派,另一種是地域群體。所謂地域群體,是因思想、風格和創作條件相近而形成的區域藝術圈。這種群體,往往不只是一位代表人物,而是若干代表畫家的風格既有一致性,又各擅勝場,每個代表人物也都各有傳派。不論藝術傳派,還是地域群體,其出現與發展都離不開一定的條件,離不開特定地域的自然風貌、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由此可見,地域資源在畫派形成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具有地域特色的畫派作品是色彩風景教學中不可多得的借鑒摹本和對象,但是地域畫派作品的一致性風格與當下求異存同的審美潮流格格不入,這也是色彩風景教學中面臨的現實挑戰。
董其昌在《容臺別集·畫旨》一文中就南北宗論寫道:“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干、趙伯駒、趙伯肅,以至馬(遠)、夏(圭)輩。南宗則王摩詰(維)始用渲淡,一變勾斫之法,其傳為張噪、荊(浩)、關(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芾、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亦如六祖(即慧能)之后有馬駒、云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12]盡管董其昌的南北宗論并不是建構在嚴格地理意義上的闡述,但是董其昌以“南北禪宗”來比喻南北畫,把抽象的感覺放在具體的物象之中,通過對南北派畫家在用筆、用墨、用水、用色上的不同加以區別,由此發現了山水畫的兩種不同藝術風格和審美取向。在董其昌看來,南宗畫是以淡、凈、雅見長的水墨畫、山水畫,北宗畫則是指畫風剛性的、躁動的、雄渾的、氣勢豪縱的,畫法上使用勾線填色斧劈之法的一類畫。這體現了地理特色對于一定地域內畫家的決定性影響,而且在其流變的過程中,既有傳承,也有創新。
古今中外,人類藝術的傳統就是不同地域的不同藝術家的發現和表現的集合,相同地域的畫派畫家既有類似的啟示和追求,更有求異存同的發現和創造。塞尚晚年總結自己的經驗時說:“盧浮宮是一本教我們學會閱讀的書籍。然而,我們決不能滿足于保持我們那些杰出先驅的美麗公式。讓我們進一步地去研究美麗的自然,讓我們從他們的影子里解放我們的大腦,讓我們按照自己的性情去努力表達自我吧。”[13]
嶺南地處亞熱帶,雨量充沛,綠樹成蔭,山巒疊嶂,繁花似錦,擁有得天獨厚的色彩風景寫生自然資源。我們可以從身邊的自然環境入手,獲得大自然的熏陶和啟迪,于自然之中體驗情景,引發對美的構思與創作。嶺南畫派在傳統中國畫的基礎上融合東洋、西洋畫法,折衷中外,融匯古今,自創一格,著重寫生,多畫中國南方風物和風光,章法、筆墨不落陳套,色彩鮮艷,酣暢淋漓。嶺南畫派以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精神與京津畫派、海上畫派三足鼎立,成為新派中國畫的代表之一。嶺南畫派的最大特征是審美理念的求變革新,這一點給色彩風景寫生教學本土資源利用提供了莫大的啟示:不能沉浸于呈現表面現象,更不能陷入陳陳相因的模仿和抄襲,這是藝術的本質,也是時代的要求。
四、結語
在色彩風景教學中,有效利用本土自然資源是一個方法問題,也是一個價值取向問題。色彩風景教學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培養學生的色彩造型能力。本土風景與名山大川沒有本質區別,尤其是對于學習色彩風景的在校學生而言,更重要的是作為當地人的熟悉與理解,這和走馬觀花者看到的完全不同。大衛·霍克尼說:“我不知道,也許我看世界的方式和別人不太一樣。但我確實仔細審視過自己是如何觀看的,這對我很重要。我正在讀勞拉·J·斯奈德的這本書:《觀者眼中的風景》,她講到觀看視角的再發現。我覺得大多數人沒有‘看’到太多東西,他們只關心前面有沒有障礙,確保自己可以正常行走。我不認為他們是在仔細觀看。”[14]信息時代的藝術已經超越了過去那種表象的獵奇,更需要內在精神的把握,去表現豐富的心靈感受。
要有效利用本土自然資源,對景寫生就是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可以現場探索構圖、色彩、造型和審美等問題,包括對形態的提取、色彩的概括以及審美的取向等,吳冠中稱之為“現場選礦、就地煉鋼”。大自然給畫家以廣泛的啟示,既有思想方面的,也有技巧方面的;可以是寫實的,也可以是寫意的,具體的表現手法根據不同目標、不同感受自由選擇,既要發現視覺元素,又要表現內在精神。
人類文明是一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自然環境也會打上人類思想、行為的烙印。色彩風景寫生建立在自然資源的基礎上,同時也離不開當地人文資源的源泉——人文地理讓我們思考、學習,或有成熟的地域畫派及其經典作品可供借鑒,還有他們的藝術觀念值得學習,使得我們的色彩風景寫生建立在一個更高的、更有效的基礎之上,培養學生的觀察和表現大自然的能力,真正讓藝術教育達到傳承和創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