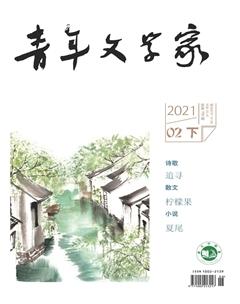錢鐘書《圍城》中的女性形象管窺
鄭光強 楊超 佟明瑋 劉治兵 武思雨
摘? 要:錢鐘書在《圍城》中所描寫的大多是文化女性,父權體制的壓迫,男性在“世襲領地”中扮演著精英地位創造者的角色,這些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算是“先進”的女性以或悲劇或喜劇的方式對傳統男性圍圈做著無聲的反抗。大歷史背景中,個體的生存遭際在整體的歷史格局中打亂錯位,女性在男性圍圈里一次又一次掙扎突圍。
關鍵詞:圍城;女性形象;博弈;婚姻悲劇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6-0-02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說道,“女性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女性是第二性,是附庸者。在當時處于女性服從的文化體系中,是否應該以消失個性特征為代價獲取個人幸福呢?女性應如何實現自身需求,奮力擺脫男性附屬品的身份。錢鐘書先生以方鴻漸為中心,以極其幽默諷刺的筆調描繪了一系列知識女性在當時社會現實下的心理活動、思想行為。濃墨重彩地描寫了一系列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照射出當時中國知識女性在特定時期帶有一定思想解放下的生存狀態和命運。
一、虛偽與殘缺
在小說的開篇,首先出現的是船上的鮑小姐,“緋霞色的抹胸,海藍色貼肉短褲”。看似前衛時髦的裝扮,卻無聲的傳來肉體最原始的呼喚,甚至被稱之為“局部的真理”。在如此有滋有味的調情手段下,不經世事的方鴻漸自然成為了她的消遣伴侶。鮑小姐是為了滿足一己私欲,在寂寞旅途中隨意尋求著喧鬧一時的消遣對象,就算沒有方鴻漸,也許還會有下一個陳鴻漸,李鴻漸……男性不過是她打發寂寞與發泄情欲的玩物。但在以男性為首,引導女性“三從四德,逆來順受”的三四十年代里,以如此自傷的方式做出的反叛姿態,何嘗不是一種畸形的思想解放呢?在經歷了fiancé的真實面貌后,當鮑小姐旁若無人撲向未婚夫“黑胖子”懷里,方鴻漸才從如酥的肉體里驚醒過來,宛如一只被閹割的公雞。女性與男性第一次交鋒以勝利告終,受盡屈辱的方鴻漸只能報之一句陳腐得發霉的真理“女性是最可怕的”。不得不說,鮑小姐反映了一類人的病態心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剖析女性的生存狀況,傳統女性除了結婚以外,并沒有其他可以開展的空間;傳統社會的男人在父權體制中是“超越”或“先驗性”的化身,女性的功能則是“內囿”或“內在性”。造成女性知識分子奮不顧身的主要因素是男性的力量與資源,鮑小姐這種新時代女性也不免落入俗套,貪圖享受,毫不猶豫選擇了舒適的生活與高人一等的地位,選擇了一個其貌不揚且比自己大二十歲的婦產科醫生當未婚夫。這是女性面對虛榮身份的選擇,對光鮮生活、金錢、名譽、地位等的追逐,男性前的妥協,步入圍城的必然,在船上的露水情緣也算是對傳統意識的反叛,就如昆蟲掉入流動的樹脂用僅有能動的尾須做著徒勞無功的掙扎。
與之呈現出截然區別的是蘇小姐,法歸博士,自律莊重。但她在這種優越的環境里養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自持“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她認為自己應被眾多男士仰慕有加。但在方鴻漸這兒卻視若無睹,蘇小姐因他略微帥氣的外表與稍稍了解的家世對方鴻漸傾了心,卻被鮑小姐的引誘調情搶了先,“將愛情視如珍寶,不肯輕易給予”的她感到氣憤、悔恨與嫉妒,卻以高姿態與方鴻漸相處,甚至背地里嫌惡同艙的鮑小姐,唾棄這兩人的無恥。及至鮑小姐走后,又發現方鴻漸與她還算合適,繼而圍繞他進行“圍捕”行動,開始極盡太太對丈夫的小義務,盡力施展她的柔情俘獲她中意的男人。然而她在別人眼里名貴的才學在方鴻漸眼里不過是渣滓,并不能成為增添魅力的砝碼。眾人眼中的才女千金小姐,在處理愛情時竟顯得如此笨拙與生硬。有強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她,不甘于愛情浮光飄浮而成的旖旎泡沫這樣被打破。在較高的戰略思想與自以為掌控大局的才能下,舉行“沙龍”主持,忽然改口不叫“方先生”而叫“鴻漸”,將自己身邊的男人進行布控,成功使趙辛楣單戀自己十多年,有意讓姓趙的知道自己跟方鴻漸親密,激發鴻漸的勇氣,其間又不忘與詩人曾元朗進行糾纏,矜持自負的她不肯把愛情“輕易”交與人,而不愿意過早分出勝負,強烈的虛榮感使她挖空心思導演了一場爭風吃醋的戲,好再讓“她再像圣母一樣從天而降”,借以牢牢鎖住他。張愛玲曾說:我以為愛情可以填滿人生的遺憾。然而,制造更多遺憾的,偏偏是愛情。她丟棄女博士的尊嚴,耍小心計改變原有孤傲的性格與男士周旋,處于女性本能渴望愛情的她沉醉于男人的喜愛與爭斗的氣氛中,似乎要以男士的肯定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有現代女性意識的她意圖與傳統婚姻宣戰,這種女性骨子里是讓男人望而卻步的,方鴻漸也不例外,上演的各處鬧劇在熱鬧喧嘩后落幕,一切又歸于岑寂。蘇小姐的個性太過鮮明,以至為了鴻漸怎么改變自己都變得拙劣,固執的愛一個人,結果變成了咄咄逼人,承載了傳統女性精神中的無限麻木和痛傷。然而,她卻損失了自己原有的作為女博士的個性,這種天然個性在女性中是多么彌足珍貴,大社會背景中的浮華喧囂還是影響了她。最后的蘇文紈由愛生恨,知曉方鴻漸愛上自己表妹唐曉芙后,產生了病態心理,不肯成全表妹,亦表現出女性在父權體制壓抑下的復雜心理,女性之間相互傾軋,倘若進行深一步探索,就會發覺男性并不是出于“隱身”或中立地位,女性將心思都放在男性身上,仍自陷于宗法制父權社會影響下的政治關系中,女性依戀、依附于男性,對同性卻產生敵意,一個女性被另一個女性擊敗,連欲望和尊嚴也被之取代。[2]因此為了取得同屬邊緣地帶更優越的心理生理環境,女性往往采取對男性認同、對女性排擠的方式,就如有大多數女性形成了“壓縮型人格”,為男性忍辱善妒,不斷地壓縮自己的原有個性,結果導致人格某種程度的斷裂。或是孫柔嘉設法捕獵男人作為維系虛榮與安身立命的手段,以至獲得虛妄的婚姻。往后看則是蘇文紈對孫嘉柔的有意傲慢輕視,以及后者對蘇的背后辱罵。這些是女性在父權社會的圍圈里蒂固的劣根性。最終優秀的女性也在邊緣掙扎與圍圈的突圍中回到原點。
二、勇敢與博弈
唐曉芙,一個作者與鴻漸都偏愛的女子,摩登社會里的“罕物”,有這麼一句話“我愛的人,我要占有他的整個生命,他在碰到我之前,沒有過去,留著空白等著我。”[3]對待愛情,她有自己的思考,不受當時社會思想的控制與安排,可如此天真執拗對愛情有著理想主義向往的人,遇到了熟于情愛的方鴻漸。幾封“鴻雁傳書”,假意安慰自己說是與表姐較勁,其實她心里已然依戀上他,不然,何以打最后一通電話想聽鴻漸辯解,盼望著他能在雨中多停留一秒。但這樣的女子太過于保有自尊乃至沒有犧牲自己一直以來奉行的信條,這樣的掙扎以至二人結果終歸是悲劇。同時,也表達出人物在詩性的理想生活與現實圍城之中,與風搏斗,與自我搏擊,抖不掉焦慮的羽毛。[4]
與之相較的是孫柔嘉,女性追逐婚姻的勝利者,才情家世方面不如蘇文紈,純情美麗不如唐曉芙,但他對男性現實心理卻捉摸熟悉,從小不受重視以及等級觀念濃厚的家庭影響了她的性格,使她知道在現實面前應主動努力。一步步實施自己的小詭計,小心謹慎、先發制人,利用自己偽裝出的軟弱,以及巧妙地利用造謠寫信等計策給鴻漸施加壓力,“伸手拉他的右臂,仿佛求他保護”,一步步把鴻漸引入她的愛情圈套中。她擺脫了傳統婚姻父母包辦的體制化,用自己的千方百計與方鴻漸一同走入了圍城。在去三閭大學的路上,過險橋照顧方的面子,不讓他在眾人面前出丑,足以看出其溫柔體貼以至鴻漸想“女性這怪東西要是關心體貼起人來,真是毛孔里也能溫存到”。 但孫柔嘉對方鴻漸的愛是真情而又痛苦的,面對愛情盡管費盡心計,也難以擺脫傳統女性一輩子陷于家庭糾紛與苦難浸潤出的特征:專橫,善妒,刻薄的特質,作為普通人的缺陷是可以理解的,張愛玲不諱言自己是個俗人,并感到“自己胸前配著小市民這樣的紅綢字條”想把持家政以此約束好她自己的男人。孫柔嘉對方鴻漸的愛情有很多自私成分,但她對他的愛衍生出了妒忌、敏感等情緒,由于女性自身生理、心理的特點,她們支配著男性,而女性也依賴男性對其的承認。深知鴻漸憐惜自己,用柔情作為主要手段。波伏娃提出:“女性的‘溫存、‘柔順及一系列與此有關的觀念和產物是社會性構作,而不是由生理特點決定的。”同時,善妒、排他性、自私也是女性在后天所衍生的。二者方面都是在愛情博弈中的選擇,前是理智,后是情感。孫柔嘉固然勇敢,但仍無法打破女性對男性過于心理束縛的婚姻狀況,她不能容忍對方的現狀,她的占有欲、甚至有些蠻橫的性格與無力改變自己的方鴻漸性格相抵觸,以至于在圍城中被外力推了出來。但孫柔嘉仍顯出了自主謀事有奮斗挑戰精神的現代女性品格。
包括離經叛道的汪太太,清明理性的頭腦,反叛一切,表達了對自以為是的男性群體的不滿和反抗。最后決然從幕后太太偽裝成離經叛道者,汪太太是最決然與男性反抗的當代女性角色,然而她的所處領域處處受到男性世界的封閉,不管把自己抬的多高,頭上總有一塊天花板,四周總有圍墻攔住她的去路。只能發出“陣陣失常的尖笑”,表達她對命運的不屑與徒然的抗爭。
三、結語
女性沖出圍城的戰役一次次失敗,承受著多方壓力的掙扎與痛苦,女性的本質不是自己造就的,而是被預定好無法成為主體,只能在主體權威下異化,其主觀能動性漸漸喪失,被禁錮于男性物質精神上給定的存在。小說中這些女性與傳統體制觀念做著或悲劇或喜劇的博弈,每個女性形象都是既個體又共性的詮釋。小說以男性視角觀察感悟而寫,更多表露男權意識,對女性批判的精神,塑造了最終還是無法實現沖出生存圍城戰役的時代下的悲劇,引起了對當時文化背景大格局下女性生存心理與精神狀態的反思。三四十年代這些女性能有先進意識與反抗精神,揭竿而起帶來的影響是深刻的。女性解放必須建立在社會解放的基礎上,不然只是披著思想解放的外衣,內里卻是腐朽傳統的繼續。女性終歸還是應重塑自我,破除精神“圍城”,努力從“男權主義”中掙脫出來,從狹仄的生命格局中掙脫出來,在廣大的社會和浩浩湯湯的時代中追求存在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實現自我的真正追求。[5]
注釋:
[1]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陶鐵柱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2]朱莉莉.芭比的哭泣——論《圍城》中的女性形象[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6):89-91.
[3]錢鐘書.圍城[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4]楊超,鄭光強,宋汶陽,李建武.詩性生活與精神圍城——淺析愛麗絲·門羅《逃離》的生命哲學理論[J].青年文學家,2019(36):145.
[5]楊超,鄭光強,宋汶陽,李建武.詩性生活與精神圍城——淺析愛麗絲?門羅《逃離》的生命哲學理論[J].青年文學家,2019(3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