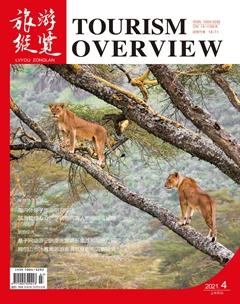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與發(fā)展研究
杜馨紫
摘 要: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華夏文明融合凝聚而成的精神文明財(cái)富,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花兒”是流傳在中國(guó)西北部,反映西北各民族社會(huì)人文、民俗風(fēng)貌的一種民謠形式的地方樂(lè)曲。古老的東方文明與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社會(huì)的飛速發(fā)展與現(xiàn)代樂(lè)曲的更迭,使“花兒”的傳承與發(fā)展被扼住了咽喉。因此,“花兒”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與發(fā)展問(wèn)題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關(guān)鍵詞:花兒;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河州
中圖分類號(hào):G12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一、“河州花兒”發(fā)展概述
“花兒”是西北廣袤的土地上婦孺皆知、流傳甚廣的一種民歌,最初是人們即興的口頭歌謠,源于公元何時(shí)已無(wú)從考證,學(xué)術(shù)上普遍認(rèn)為“花兒”產(chǎn)生于明代初期,于清代最為鼎盛。“河州花兒”“洮岷花兒”和“西寧花兒”皆為花兒的幾種類別,“河州花兒”源于甘肅臨夏西南一帶;“洮岷花兒”源于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中部一帶;“西寧花兒”則源于青海西寧周邊區(qū)域[1]。2006年“花兒”被列入我國(guó)第一批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三年后被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zhì)遺產(chǎn)代表作。
新中國(guó)成立以后幾十載,“花兒”作為西北民歌被廣泛地收集,越來(lái)越多的學(xué)者對(duì)“花兒”這種民歌的歷史、曲調(diào)、唱詞等開始了研究。20世紀(jì)后期以及進(jìn)入21世紀(jì)以來(lái),隨著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加快,“花兒”這種民歌遭到了重創(chuàng),鄉(xiāng)間少年紛紛進(jìn)入城市打工,老一輩傳唱者身后再無(wú)跟唱的少年;流行音樂(lè)、西方文化的傳入使“花兒”這種民間藝術(shù)逐漸沒(méi)落,發(fā)展?fàn)顩r不容樂(lè)觀。
二、“河州花兒”的現(xiàn)狀
“花兒”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chǔ),曾經(jīng)的家家傳唱、戶戶對(duì)歌隨著城市化進(jìn)程加快、現(xiàn)代科技文明的沖擊以及農(nóng)村地區(qū)人口的流失,其生存空間正面臨著萎縮。目前“河州花兒”的知名傳承人有何清祥、董明巧、劉國(guó)成等,其中大部分傳承者不識(shí)字,文化程度較低,嘗盡生存的苦澀也就使文化學(xué)習(xí)無(wú)從談起,平凡的土地勞作讓他們練就一身歌唱花兒這種民歌的本領(lǐng)[2]。再看80、90后的一代人基本擺脫了吃不飽穿不暖的境遇,都有機(jī)會(huì)走進(jìn)校園接受現(xiàn)代藝術(shù)的熏陶,因此流行樂(lè)以及新型娛樂(lè)方式從多個(gè)維度打壓著“花兒”在人們心中的地位。“花兒”在曾經(jīng)的傳承中,皆是憑借民間愛(ài)好者的言傳。如今,“河州花兒”的根基遭到了破壞,陷入了傳承危機(jī)。
三、“河州花兒”發(fā)展和傳承的SWOT分析
(一)優(yōu)勢(shì)
首先,其獨(dú)特的地理位置。當(dāng)前至關(guān)重要的是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最原生態(tài)、最純粹的一面留給后人,并不斷地發(fā)展創(chuàng)新,從而保持強(qiáng)大的生命活力。河州地區(qū)即如今的臨夏回族自治州南部一帶,是藏北高原與黃土梁的過(guò)渡區(qū),山谷溝壑縱橫,平坦土地稀少,多為干旱、半干旱氣候,居住著回族、藏族、撒拉族、東鄉(xiāng)族等。而這獨(dú)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環(huán)境使“河州花兒”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得到很好的保護(hù),不會(huì)輕易地被外來(lái)文化同化或異化。其次,其自身深厚的文化內(nèi)涵。在甘肅河州這片看似貧瘠的土地上孕育出“花兒”這種優(yōu)秀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并不只是由于獨(dú)特的地理環(huán)境,“花兒”更是一種活態(tài)的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在《花兒集》里,“花兒”被分為30類,后來(lái)徐英國(guó)又將其劃為50類。由此可以看出“花兒”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3]。
(二)劣勢(shì)
第一,經(jīng)濟(jì)發(fā)展落后。甘肅省經(jīng)濟(jì)發(fā)展落后,文化建設(shè)發(fā)展面臨資金短缺,雖然政府竭盡全力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但由于發(fā)展經(jīng)費(fèi)匱乏導(dǎo)致針對(duì)“花兒”的發(fā)展規(guī)劃無(wú)法具體落實(shí)。第二,研究工作相對(duì)滯后。近年來(lái),一眾“花兒”研究學(xué)者做了大量的挖掘、整理工作,為其今后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但也僅僅是針對(duì)“花兒”這一大的范圍進(jìn)行統(tǒng)一研究,而忽略了各個(gè)地方存在的差異。由于發(fā)展研究工作沒(méi)有及時(shí)跟進(jìn),理論滯后與客觀形勢(shì)的差異逐漸凸顯。伴隨著社會(huì)現(xiàn)代化進(jìn)程,“花兒”的保護(hù)、發(fā)展速度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其沒(méi)落的速度,這就警示我們要將傳承發(fā)展作為核心工作開展。第三,傳播相對(duì)落后。河州地區(qū)在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交界地帶,這里地域環(huán)境相對(duì)封閉,很少有人知道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古河州地帶。花兒的傳播僅靠當(dāng)?shù)鼗刈逋獬鼋?jīng)商時(shí)帶出,但也只是周邊陜甘寧、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能走出西北,把“花兒”唱到全國(guó)的舞臺(tái)的專門藝人少之又少,因此“河州花兒”的現(xiàn)狀令人擔(dān)憂。第四,校園普及度較低。在現(xiàn)代化教育體系中,學(xué)校忽略了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和教學(xué),甘肅省“花兒”非物質(zhì)文化也并未納入義務(wù)教育之中。河州地區(qū)素有“花兒之鄉(xiāng)”的美譽(yù),河州本地的學(xué)生只知其名,卻不知其意,學(xué)生從小學(xué)開始學(xué)習(xí)西洋與現(xiàn)代音樂(lè),這就導(dǎo)致了與當(dāng)?shù)匾魳?lè)文化相脫離的狀態(tài),很少接觸當(dāng)?shù)厍楦斜磉_(dá)的方式,自然而然放棄了本民族的特有文化與風(fēng)俗習(xí)慣。
(三)機(jī)遇
第一,政府的重視及政策支持。自2006年“花兒”申遺以來(lái),它的文學(xué)價(jià)值、社會(huì)價(jià)值、歷史學(xué)價(jià)值、語(yǔ)言學(xué)價(jià)值備受學(xué)者矚目。2016年,甘肅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huì)審議通過(guò)了《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花兒保護(hù)傳承條例》,對(duì)其進(jìn)行搶救性保護(hù)并開展相關(guān)研究,制訂了詳細(xì)的方案計(jì)劃。當(dāng)?shù)卣哟罅藢?duì)“花兒”傳播發(fā)展的資金支持,加大扶持當(dāng)?shù)亍盎▋簳?huì)”的活動(dòng)力度,廣邀全國(guó)人民前來(lái)參加;提供必要的資助支持“花兒”文集、光盤等各種相關(guān)資料的整理和出版;鼓勵(lì)“花兒”傳承人和愛(ài)好者參與社會(huì)公益活動(dòng)等[4]。有了相關(guān)政策的支持,相信“花兒”的發(fā)展會(huì)出現(xiàn)新局面。第二,甘肅省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的變化。甘肅省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一直以來(lái)以工業(yè)帶動(dòng)為主,但是近年來(lái)政府把打造文化大省的工作放在重心位置[5]。目前,已建成3個(gè)國(guó)家級(jí)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保護(hù)基地,打造了眾多像武威天馬國(guó)際旅游節(jié)、甘南香巴拉旅游節(jié)等類似的節(jié)事旅游活動(dòng),在此文化建設(shè)基礎(chǔ)上對(duì)于“河州花兒”的傳播不失為一個(gè)良好的機(jī)會(huì)。第三,文旅融合帶來(lái)新機(jī)遇。2021年3月,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第十四個(gè)五年規(guī)劃和2035年遠(yuǎn)景目標(biāo)綱要》(以下簡(jiǎn)稱“十四五”規(guī)劃)第三十六章明確提出推動(dòng)文化和旅游融合發(fā)展。旅游業(yè)經(jīng)過(guò)過(guò)去一年的停頓休整之后正在穩(wěn)步復(fù)蘇,生態(tài)游、民俗游、宗教游、鄉(xiāng)村旅游和紅色旅游是目前最受歡迎的旅游形式。“河州花兒”是甘肅省旅游發(fā)展的文化資源之一,堅(jiān)持非遺文化豐富旅游的內(nèi)涵,旅游為非遺文化提供傳播路徑。“十四五”繪畫的頒布也為“花兒”的發(fā)展帶來(lái)了一定的發(fā)展機(jī)遇。
(四)威脅
第一,傳承人難覓。“花兒”的傳承群體相對(duì)固定,以口傳心授的方式薪火相傳著,幾個(gè)世紀(jì)以來(lái),“花兒”都擁有傳承的連續(xù)性與純正性。但是,隨著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以及社會(huì)的進(jìn)步,越來(lái)越多農(nóng)村人口進(jìn)城務(wù)工,這直接導(dǎo)致了“花兒”的傳承者消失殆盡。農(nóng)村人口的流失致使“花兒”文化傳承破裂,由此面臨失傳的危機(jī)。第二,市場(chǎng)需求逐步減少,“花兒”缺乏發(fā)展的動(dòng)力。在過(guò)去傳統(tǒng)的封閉社會(huì)里,河州廣大勞動(dòng)者“晝出耕耘夜績(jī)麻”,“花兒”承載著勞動(dòng)人民的憂愁、不幸、思念和理想,封建社會(huì)下的種種不幸和天災(zāi)人禍帶來(lái)的悲苦、心酸等不幸遭遇都通過(guò)唱“花兒”得到釋放。“花兒”是河州廣大人民生活中的唯一精神支柱,勞動(dòng)累了唱上一曲,朋友之間對(duì)對(duì)歌,為了心中的姑娘唱上一曲。隨著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以及電視、網(wǎng)絡(luò)媒體的普及大大豐富了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越來(lái)越好,即便是當(dāng)代農(nóng)村,大部分農(nóng)民也會(huì)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媒體豐富平日里的生活,而創(chuàng)作“花兒”的心理動(dòng)機(jī)逐漸消失,也不再成為唯一[6]。第三,城市化的生活對(duì)“花兒”接受度低。隨著城市化進(jìn)程的加快,“花兒”也從鄉(xiāng)間來(lái)到了城市,它洗去了一身的泥土,成了城市里的“奇葩”。城市居民聽不懂歌詞所蘊(yùn)含的情感和對(duì)生活的向往之情。歌詞以日常的說(shuō)話方式歌唱底層農(nóng)民的辛酸與希冀,沒(méi)有體驗(yàn)過(guò)當(dāng)?shù)氐奈幕铙w驗(yàn)就無(wú)法感受歌詞曲調(diào)的語(yǔ)言情感,因此圍觀者也大多來(lái)自農(nóng)村。
四、促進(jìn)“河州花兒”傳承與發(fā)展的建議
(一)加強(qiáng)保護(hù)“花兒”傳承人
“花兒”申遺成功在某些意義上促進(jìn)了其傳播。但是,現(xiàn)代新型音樂(lè)氛圍以及大眾的偏好讓傳承人漸漸失去創(chuàng)新的源動(dòng)力,對(duì)于傳承人而言,保護(hù)工作是大勢(shì)所趨,他們是“花兒”的載體,“花兒”未來(lái)的發(fā)展要靠他們,須加以關(guān)注。首先,要實(shí)行適當(dāng)?shù)募?lì)措施。在經(jīng)濟(jì)方面,大多數(shù)傳承人是家境貧困的農(nóng)村人口,所以要給予一定的經(jīng)濟(jì)補(bǔ)貼;在社會(huì)地位方面,應(yīng)對(duì)傳承人進(jìn)行官方認(rèn)證,給予一定的社會(huì)定位;在名譽(yù)方面,對(duì)傳播和發(fā)展“河州花兒”具有相當(dāng)成果的繼承者給予殊榮、表彰及獎(jiǎng)勵(lì)。其次,要建立獨(dú)立的研究機(jī)構(gòu)。僅僅靠國(guó)家的扶持和甘肅省旅游發(fā)展的帶動(dòng)是不行的,必須建立“河州花兒”傳承與發(fā)展的專門機(jī)構(gòu),由專人負(fù)責(zé),鼓勵(lì)“花兒”傳承人和愛(ài)好者對(duì)當(dāng)?shù)厝藛T進(jìn)行適當(dāng)?shù)慕逃嘤?xùn),以便于尋找合適的繼承人。再次,可以組織“河州花兒”的傳承人參加比賽和文化節(jié)。“花兒”作為一種民歌,其藝術(shù)形式和曲樂(lè)之獨(dú)特是傳播發(fā)展的主要依賴。
(二)要增強(qiáng)當(dāng)?shù)鼐用竦泥l(xiāng)土文化感
西北地區(qū)環(huán)境惡劣,經(jīng)濟(jì)落后,這里的年輕人大都想走出甘肅、走出西北。很少有回報(bào)家鄉(xiāng)、建設(shè)家鄉(xiāng)的理想愿望,所以當(dāng)?shù)厝藢?duì)故鄉(xiāng)的自豪感缺乏,主要原因在于本地青少年對(duì)鄉(xiāng)土文化的認(rèn)可度較低[7]。如果從幼兒時(shí)期就培養(yǎng)鄉(xiāng)土文化感,有意或無(wú)意的灌輸家鄉(xiāng)的文化民俗等,讓“花兒”從小就走進(jìn)人們心中,相信“花兒”的發(fā)展又是另一番局面。
(三)讓“花兒”走進(jìn)學(xué)校
“花兒”是無(wú)形的藝術(shù),需要世人口口相傳方可將其千古傳唱。讓“花兒”逐步走進(jìn)校園,走進(jìn)學(xué)校音樂(lè)課堂,嘗試著把“花兒”的文化講述給年輕一輩,從娃娃抓起,體驗(yàn)、學(xué)習(xí)、傳承發(fā)揚(yáng)。如此“花兒”文化的傳承人數(shù)量質(zhì)量都會(huì)有相當(dāng)大的提升。第一,讓“花兒”走進(jìn)幼兒園的舞蹈課堂。兒童在3~6歲主要是情感認(rèn)知和行為認(rèn)知發(fā)展時(shí)期,幼兒時(shí)期的兒童主要是在活動(dòng)中進(jìn)行學(xué)習(xí)和成長(zhǎng),讓“花兒”成為幼兒的舞蹈音樂(lè),接觸本土民間音樂(lè),從小培養(yǎng)“花兒”民樂(lè)在幼兒心中的熟悉感。第二,讓“花兒”走進(jìn)小學(xué)、初中、高中的音樂(lè)課堂。這些階段的兒童都有了普遍的學(xué)習(xí)能力、判斷能力。可讓“花兒”以校本課程的形式走進(jìn)學(xué)校。讓民間的老藝人打破傳統(tǒng)的音樂(lè)課堂教學(xué)模式,用其獨(dú)特的方法來(lái)宣傳“花兒”,訓(xùn)練學(xué)生。如此一來(lái),無(wú)論是非物質(zhì)文化的生根延伸還是對(duì)文化的傳播,都可以讓學(xué)生感受非物質(zhì)文化的魅力與價(jià)值。第三,讓“花兒”走進(jìn)大學(xué)校園。大學(xué)的學(xué)習(xí)更加自由,多種實(shí)踐活動(dòng)是大學(xué)生活的主題之一。大學(xué)也應(yīng)當(dāng)適當(dāng)?shù)嘏e辦關(guān)于非物質(zhì)文化教育課堂、表演活動(dòng)、比賽競(jìng)技等,給來(lái)自五湖四海的學(xué)生提供傳播家鄉(xiāng)文化的機(jī)會(huì)。同時(shí)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的開放給予當(dāng)代大學(xué)生更多的學(xué)習(xí)機(jī)會(huì),線上可開設(shè)關(guān)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公開課,不僅是針對(duì)“花兒”,當(dāng)代青年應(yīng)多了解中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的魅力所在。
(四)舉辦相關(guān)的選秀活動(dòng)
就如旅游演出一樣,選秀活動(dòng)也會(huì)促使從事不同工作的人們?nèi)チ私狻盎▋骸蔽幕Mㄟ^(guò)選秀活動(dòng)弘揚(yáng)本民族、本地區(qū)的文化,對(duì)各族人民的思想情感都會(huì)產(chǎn)生深遠(yuǎn)的影響。這一倡議所產(chǎn)生的商業(yè)以及文化效益在很多其他類似活動(dòng)中被驗(yàn)證成功。選秀活動(dòng)作為傳播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新途徑,給“花兒”傳承人的尋找提供了舞臺(tái),也是傳達(dá)文化價(jià)值觀的一種重要途徑,它發(fā)揮的作用無(wú)可代替。
(五)打造“非遺文化+旅游”新模式
“花兒”是大西北文化的重要載體,是“花兒人民”的精神家園。將民俗文化融入旅游觀光中,可使游客更加了解西北文化。同時(shí)也可以讓“花兒”通過(guò)五湖四海的游客帶到祖國(guó)的每一個(gè)角落。因此,要重視旅行社的作用,把“花兒會(huì)”規(guī)劃到旅游線路中,同時(shí)與河州鄉(xiāng)村旅游相結(jié)合,舉辦讓游客可以參與體驗(yàn)的節(jié)目晚會(huì),讓游客真正感受河州地區(qū)的民族風(fēng)情和世界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花兒”的魅力所在[8]。
參考文獻(xiàn)
[1] 楊育玲.花兒舞臺(tái)表演與“非遺”保護(hù)探究[J].中國(guó)優(yōu)秀碩士學(xué)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2017(2):20-20.
[2] 安曉燕,宋倩.對(duì)甘肅花兒傳承和保護(hù)的探討[J].傳播力研究,2018(29):181.
[3] 阿忠榮.試論花兒的文化內(nèi)涵[J].青海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5(2):48-53.
[4] 董原,王嘉瑞.絲綢之路申遺甘肅段旅游區(qū)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與開發(fā)[J].蘭州學(xué)刊,2012(4):195-199.
[5] 張永利,李新亮.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利用與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融合的思考:以河北承德為例[J].品牌,2015(3):299-299.
[6] 蘇怡多,李坤.音樂(lè)選秀對(duì)文化傳播的意義[J].甘肅科技,2012(8):107-109.
[7] 楊妍.文化遺產(chǎn)與博物館數(shù)字化[J].智能建筑與城市信息,2004(9):37-40.
[8] 范鵬.開發(fā)資源寶庫(kù),建設(shè)文化大省[J].社科縱橫,2010(7):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