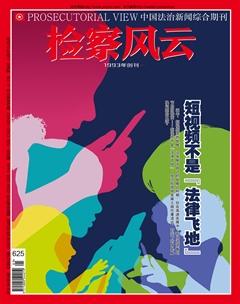短視頻騙局的套路與反套路
張宏羽
近年來,短視頻行業迎來飛速發展。根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以下簡稱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用戶規模達8.88億,占我國網民總數的94.5%。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為8.18億,占我國網民總數的87%。
有人的地方,就可能有詐騙。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騙子們也搭上了信息時代的“快車”,變得愈發猖狂。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輸入“抖音”及“詐騙罪”,共找到755條結果,僅2020年就占了614條;輸入“快手”及“詐騙罪”,共找到1082條結果,僅2020年就占了642條。
騙人的“網紅”
“親愛的姐姐,你再點一下右邊的愛心和加號,回復我一下可以嗎?”屏幕里,正播放著著名演員“靳東”的畫面,并拼接上了機器人的配音。這樣一段合成視頻,看上去如此低級與劣質。某短視頻平臺上的這個賬號,也只是將靳東本人照片作為頭像,昵稱中含有“靳東”二字的普通賬號。
“他為什么會騙我,他不可能騙我。靳東喜歡我,他向全中國宣布了!”屏幕外,江西贛州60多歲的黃女士瘋狂迷戀某短視頻平臺上的“假靳東”,為了和其談戀愛,對方的每場直播她都會買不少東西以表支持,甚至與家人大吵大鬧,還到長春去尋找“假靳東”。
去年10月,靳東工作室在微博發表聲明回應,稱靳東從未在任何短視頻平臺開設賬號,在短視頻平臺中的“靳東”系列賬號均非本人。針對這類賬號,工作室將通過法律途徑追究相關主體的法律責任。
盡管短視頻平臺對于仿冒名人進行詐騙的內容和賬號,一直持堅決打擊的態度,但記者通過網絡搜索發現,某些短視頻平臺上依舊充斥著各種“李鬼”賬號。這些賬號或以明星照片為頭像,或在昵稱中夾帶明星名字,騙取粉絲的關注與點贊,甚至將流量轉化為自己直播帶貨或者刷禮物的客源,獲取經濟利益。由于對網絡技術不太了解、辨識力和警惕性弱,中老年人更容易掉進騙子布下的各種“迷魂陣”中。
被騙的又何止中老年人?其實不少年輕人也很容易成為騙子的“盤中肥肉”。根據統計報告顯示,2020年上半年,全國電信詐騙受害者中,21歲—40歲年齡段的電信詐騙受害人數量占比達81%。
騙子們往往會利用年輕人的貪心或愛心實施詐騙,誘導其一步步進入圈套。記者在短視頻平臺搜索“免費送手機”“免費送寵物”等詞,可以看到一些所謂的“網紅”借抽獎送手機的名義,發布手機或聊天截圖,誘導潛在受害者添加微信,之后以手機激活費、運費、保證金等名義斂財,一旦轉賬完成后,受害者會立即被拉黑。在一些“免費領寵物”的騙局中,騙子在一些短視頻平臺上發布免費贈送寵物的信息,以運輸費、疫苗費、免疫證辦理費為由,騙取錢財。
還有的騙子會引誘年輕人掉進“殺豬盤”中。2019年5月,朱某通過某短視頻平臺上發布的相親網站認識騙子周某,周某騙取其信任后介紹給她一個賭博網站。周某說他可以控制網站投注的后臺,于是朱某前兩次共投了29000元,并將賺得的2900元提現出來。因為貪心,朱某不斷“加碼”,先后投進5萬元、3萬元、1萬元和10萬元。之后,騙子便不再與朱某聯系,朱某這才發現上當受騙,遂報警。
利用同情心進行詐騙,也是一些騙子的基本操作。2019年,李某在某短視頻平臺收到一條“請求添加微信好友”的信息,他便添加對方為好友。成為微信好友后,騙子甲向李某發來微信:“我同事想強奸我,我離職了,我母親生病需要照顧,而且我舅舅要我嫁出去還錢……”騙子甲冒充幼師,博取李某的同情心。之后騙子甲不斷以母親做手術、母親病情加重需要借錢等為由,先后讓李某進行50余次的微信轉賬。之后,騙子甲將李某的銀行卡與自己的微信號綁定,對方從2019年6月28日到案發為止,用李某的微信消費約10萬元。直到案發,李某共被詐騙47萬余元。
還有騙子大肆散播虛假信息,在某些短視頻上發著“國難財”。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何某利用疫情造成的口罩供應緊張局面,利用被害人迫切想得到口罩的心理,在某短視頻平臺,面向不特定人群發布口罩供應的虛假消息,吸引被害人添加其微信,以收取口罩購買款為由騙取對方錢財,最高詐騙數額為5900元。法院判決何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并處罰金2000元;隨案移送作案工具手機一部,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被騙的“網紅”
短視頻的熱度飆升,讓不少網紅一夜之間嘗到“甜頭”。一些年輕人也開始做起“網紅夢”,以為從此人生可以“躺贏”。根據統計報告顯示,54%的“95后”最向往的新興職業是主播或網紅。在不切實際的“網紅夢”中,不法分子們早已設計了套路——利用短視頻非法實施網紅培訓。
“你和網紅只差一次短視頻培訓課程”“做不了網紅,只是你不懂行業內幕”……一些所謂的培訓機構會瞄準年輕人希望“一夜成名”的心理,編出形形色色的口號,滿屏都是“偽成功學”的氣息。一些年輕人砸下去的“智商稅”越多,得到“成功”的泡沫就越大,最后換來的只可能是一聲唏噓。

(圖/視覺中國)
非法網紅培訓的套路一般是從線上的公開課開始的。曾參加過此類公開課的林女士告訴記者,所謂的公開課,就是“導師”出來介紹自己的行業背景,接著開始為學員們描繪美好藍圖,簡單講解一些短視頻制作流程后,課程戛然而止。整個過程大約半個小時。
當林女士希望了解更多網紅成功的秘訣時,會被對方告知要購買進階課程,為期7天的進階課程要價近2000元。記者調查后發現,市面上網紅培訓的進階課程,售價基本都在千元以上,多是一周或一個月的短期培訓。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這些課程教授的技巧過于簡單,沒什么真東西。”
有人看清了這種套路,便及時止損。還有些學員升級為“合伙人”,卻徹底被套牢,淪為待割的“韭菜”。想要成為“合伙人”,就要抱著真金白銀去“解鎖”更高級的課程,“合伙人”還可以負責課程推廣,掌握簡單的話術后就可以去拉人頭,讓更多人來付費,從而拿到提成。因為成為“合伙人”的代價較高,一些網紅培訓機構還會向學員推薦貸款。最后,一些學員不僅沒有成名、沒有賺錢,還遭受財產損失,甚至年紀輕輕就背上了貸款。
用“魔法”打敗“魔法”
面對短視頻詐騙的高發態勢,還短視頻一片凈土,不讓短視頻成為“詐騙天堂”已成為社會共識。雖然短視頻詐騙手法層出不窮,騙子們無孔不入,但既然有邪惡的“魔法”,就一定有正義的“魔法”,有套路就一定有反套路。
對于各大短視頻平臺而言,審核、監管及風險預警十分重要。記者注意到,“假靳東”事件發生后,抖音等短視頻平臺加強了對仿冒名人現象的打擊,積極研發上線明星人臉識別模型,查殺違規假冒賬號……但每次風頭一過去,短視頻騙局又死灰復燃,甚至催生出更隱蔽、更復雜的詐騙手法。在平臺與不法分子的對抗中,平臺需要的是持續排查清理潛在詐騙問題,并且能夠不斷升級技術策略。同時平臺也要尋求多方合作,及時向警方舉報和提供相關線索,才能對涉嫌詐騙的“黑色產業鏈”形成有效打擊。
打擊短視頻詐騙,警方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詐騙行為鏈條長、跨平臺明顯、網絡存在匿名性……盡管這些因素增加了調查取證的難度,但警方應積極研究短視頻詐騙防治的新方法、新手段,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實現多方聯動,打通破案難點、提高打擊效能。此外,檢察機關應對短視頻行業進行積極引導,對違法風險進行防范提示,也要積極參與研究、制定反詐騙機制,防止和糾正有案不移、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等問題,依法嚴厲打擊相關詐騙犯罪。
面對信息時代的發展趨勢,要想防止短視頻詐騙,法律應該是“武器庫”里的“殺手锏”。一方面我們要及時彌補新領域、新業態的法律和監管空白,另一方面我們要根據現有法律法規,從刑事、行政、民事等方面進行制裁,讓不法分子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比如,《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發布,進一步完善法律適用,同時明確法律標準,統一執法尺度。又如,今年正式實施的民法典,在數據、網絡虛擬遺產、個人信息保護和網絡侵權責任等方面進行了規定,讓執法人員在處理一些網絡詐騙問題時有法可依。
其實,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都需要擦亮眼睛、提高防騙意識,遇到“天上掉的餡餅”,更應采取理智的態度,不給騙子可乘之機,避免被騙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