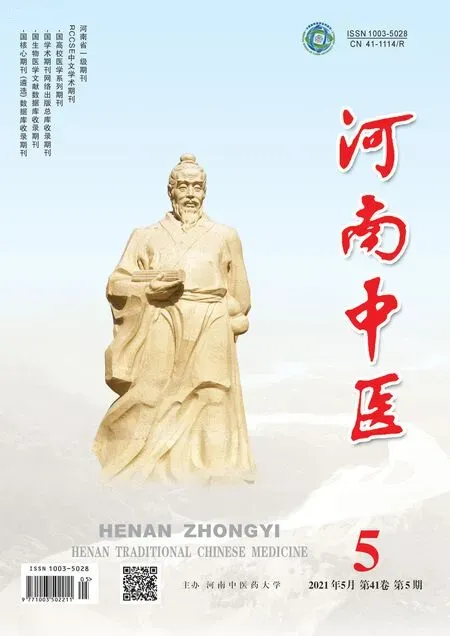《金匱要略》麥門冬湯文獻考證*
鄭豐杰,朱浩宇,曾鳳
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
《金匱要略》麥門冬湯具有清養肺胃、止逆下氣之功,為治療肺胃陰傷、火氣上逆的代表方,被廣泛應用于治療咳嗽、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及婦科、兒科、耳鼻喉科等疾病,入選首批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會同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布的《古代經典名方目錄(第一批)》[1]。然而,麥門冬湯在宋校《金匱要略》鄧珍本與吳遷本中煎服法記載存在明顯不合理之處。而宋校《金匱玉函經》《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三書中該方的文獻材料,不僅服藥量有誤,而且藥量的差異也非常明顯。筆者通過對這些文獻資料的比較分析,從共時性的維度對此一問題進行全面考證;結合時代背景,以及北宋校正醫書局的人員組成、組織架構、運行機制、整理古醫書的理念、規則、具體做法等,嘗試對這一現象的成因進行分析,并提出通過考察異文原始內涵及其所隱藏的科學價值,為澄清某些分歧模糊的認識提供參考。
1 《金匱要略》吳遷本、鄧珍本所載麥門冬湯概述
《金匱要略》為醫圣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的雜病部分,其內容屢被魏晉以后方書引用,唐《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方》均有大量收錄,而史志目錄中則未見“金匱要略”之名。北宋時期館閣官員王洙發現《傷寒雜病論》之節略本《金匱玉函要略方》3卷,校正醫書局林億等對該書的雜病部分重新編次整理,定名《金匱要略方論》,于治平三年(1066年)和紹圣三年(1096年)先后刊行了大字本與小字本。時至今日,大字本系統以元代鄧珍本(1340年)為祖本,包括趙開美本、俞橋本、徐镕本等傳本,傳播較廣,影響較大。小字本系統目前可知有明代吳遷本(1395年)傳世。張承坤等[2]認為,鄧珍本對《金匱要略》官刻做了全方位的修改,內容已非官刻原貌,應屬于民間修改重編本;吳遷本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金匱要略》北宋官刻原貌,是該書現存最正宗、最權威的傳本。兩版本麥門冬湯對比見表1(差異之處以標識)。
按:從表1可見,兩版本麥門冬湯最明顯的差異是吳遷本保存了藥物制法,如麥門冬去心、半夏洗、甘草炙等,而鄧珍本各藥則無炮制法。通觀全文,發現這是兩版本統一的體例。

表1 《金匱要略》吳遷本、鄧珍本麥門冬湯對比
考宋校各書,《傷寒論》《金匱玉函經》《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方》等書方劑基本保留了藥物制法,唯有《備急千金要方》刪除了各藥炮制方法腳注的形式,而是將相關內容集中在卷一《合和篇》敘述。對此宋臣在《新校〈備急千金要方〉例》特別作出說明:“凡古經方用藥,所有熬煉節度皆腳注之。今方則不然,撮合諸家之法而為合和一篇,更不于方下各注。各注則徒煩而不備,集出則詳審而不煩。凡合和者,于第一卷檢之[3]。”從這段話可以了解到,宋臣在校訂其他醫書時均保存了原有的炮制表述方式。從這點來看,吳遷本腳注藥物制法的特點,進一步印證了該本保留北宋官刻原貌的結論[2]。
學者陳楚為等[4]將《金匱要略》兩版本方劑先煎麻黃部分進行比對研究后指出,吳遷本所載內容更合醫理,而鄧珍本則多有不合理之處[4]。從麥門冬湯煎煮服用法來看,兩版本的文字表述雖然存在差異,但是核心內容完全相同,煎服法均為“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類似這種夜間增加服用次數的記載,同樣見于黃連湯(晝三夜二)、理中丸(日三四,夜二服)等方的后注中,意在少量頻服,使藥性持久,提高療效。
2 宋校《金匱玉函經》《外臺秘要方》《備急千金要方》麥門冬湯文本辨析
《金匱玉函經》與《傷寒論》同體而別名。宋臣在《校正〈金匱玉函經〉疏》中說:“其文理或有與《傷寒論》不同者,然其意義皆通。圣賢之法,不敢臆斷,故并兩存之。凡八卷,依次舊目,總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5]。”可見他們基本保存了該書原貌。在現存最早版本的陳士杰本(源于清代何焯手抄宋本)中,麥門冬湯見于卷八,其內容與宋校《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之異同詳見表2。

表2 《金匱玉函經》《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麥門冬湯
詳考三書的差異主要有4點,分述如下。
第一,《外臺秘要方》以腳注形式標出炮制法,如“麥門冬去心”“甘草炙”等以及“忌羊肉、餳、海藻、菘菜。并出第十八卷中”。從本文第一部分的論述,結合宋臣《新校〈備急千金要方〉例》[3]的說明,可知《外臺秘要方》所引《備急千金要方》該方藥物腳注及服藥禁忌當是保存原貌。
第二,《外臺秘要方》校正者孫奇列出“此本仲景《傷寒論》方”的校語。學者孟永亮等[6]指出,孫奇是北宋校正醫書局的主要成員,參校了《外臺秘要方》《傷寒論》《金匱玉函經》《金匱要略方論》《備急千金要方》《黃帝內經素問》等 9 書。其中從皇祐三年(1051 年)至治平四年(1067 年)十六年間,主要整理《外臺秘要方》《黃帝內經素問》兩書。因而他不僅了解各書內容并且對《外臺秘要方》更為熟悉。“此本仲景《傷寒論》方” 的校語表明,孫奇在《傷寒論》中確曾見過該方。
第三,三書麥門冬的藥量差異明顯,《金匱玉函經》七升,《外臺秘要方》二升;《備急千金要方》作麥門冬汁三升。關于藥汁制法,《金匱要略》中亦有相關記載,如百合地黃湯、防己地黃湯分別用“生地黃汁一升”“生地黃二斤”絞汁,凸顯其養陰生津之用;生姜半夏湯用“生姜汁一升”,增加全方溫胃通陽散結,和胃止嘔之功。
第四,在煎服法上,《金匱玉函經》“水一斗六升,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余二升,與《金匱要略》吳遷本、鄧珍本同;《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溫服半升,日三夜一”,余四升。各書差異明顯。
3 各書麥門冬湯文本差異的原因分析
以上所述不禁會引起一個疑問:同一批人整理醫書,而各書所載麥門冬湯在主治病證相同的情況下藥量及服藥量卻差異如此之大?排除后世流傳過程中出現的文字訛誤,這一現象很有可能與北宋校正醫書局成立的社會背景、宋臣整理中醫古籍的理念、指導原則、具體方法等因素密切相關。
范家偉[7]指出,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朝廷根據韓琦的建議設立校正醫書局,主要目的是通過整理刊行古代醫書為邊鎮軍民提供治療依據。考宋校11部書的序文有8處強調儒臣身份,《新校正<黃帝針灸甲乙經>序》更是直接宣稱:“斯醫者,雖曰方技,其實儒者之事乎[8]?”可知在該機構館閣官、通醫儒臣、醫官的三層架構中,前二者的地位更高,發揮了主導作用,醫官只是“入局支應”[7],等待解答校書時遇到的醫學難題。這就表明宋臣將此項工作視為助人君施行仁術、經世濟民的重要舉措。他們在《校正<千金翼方>表》中特地申明自己嚴謹審慎的原因,其文云:“臣以為晉有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與祖訥論。祖云:辨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于湯藥,小小不達,則后人受弊不少。是醫方不可以輕議也[9]。”在這種理念統領之下,宋臣制定計劃、確定原則,統一規范校書的步驟與方法,即:首先“請內府之秘書,探道藏之別錄,公私眾本,搜訪幾遍[3]”,以資校勘;其次通過比較不同的本子,“正其訛謬,補其遺佚。文之重復者削之,事之不倫者輯之[3]”,“編次類聚[3]”,確定醫書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內容;第三,對“文義猶或疑阻[3]” 之處,采“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于世者[10]”“敘而考正焉[10]”;第四,對“尚有所闕[3]”之處,“溯流以討源[3]”,“取自神農以來書行于世者而質之[9]”,在“凡所派別,無不考理,互相質正,反復稽參[3]”的基礎上,“據經為斷,去取非私[11]”,力求做到“一言去取,必有稽考[10]”。第五,對于疑惑難解之處,“有所闕疑,以待來哲[12]”。第六,對于各書相應內容的差異,他們認為:“凡諸方論,咸出前古諸家及唐代名醫,加減為用而各有效”,因而,“今則遍尋諸家,有增損不同者,各顯注于方下,庶后人用之,左右逢其源也[3]”。

4 結論
宋校醫書沿用至今,是中醫學傳承創新的基礎。麥門冬湯在宋校《金匱要略》吳遷本、鄧珍本,《金匱玉函經》《外臺秘要方》《備急千金要方》等書中的混亂訛誤現象,提示我們要充分認識這些傳世醫書文本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因而,對于仲景方的臨床應用與開發,首先必須扎實做好文獻考證。在具體方法上,一是應突破既往研究多囿于《傷寒論》《金匱要略》《金匱玉函經》文本的局限,將文獻參考資料的范圍拓展至宋校《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方》,以及《醫心方》(984 年,參考輯錄 200 余種中國隋唐以前中醫文獻,不改原文直接引用,基本保持了原著的本來面目)等相關醫書;二是采用計算機技術,建立宋校醫書仲景方異文動態語料庫及數據庫應用系統;三是綜合運用文獻學、傳統語言學、中醫學等多學科知識,從共時性、歷時性兩個維度對異文材料進行考釋辨別與醫理推敲,做出判斷與取舍,最大程度增加仲景方文獻的完整性與正確性;四是參考宋代醫方類代表性著作《太平圣惠方》(992 年,多采摭《傷寒論》《備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通過宋臣著書與宋臣校書在衡制單位、藥量等關鍵信息上的異同,探討宋臣校訂古醫書方劑文獻的指導原則、具體方法及其影響,為確定仲景方的關鍵信息提供參考。在扎實做好基礎性考證的基礎上,還應做好頂層設計,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布的第一批《古代經典名方目錄》為開端,分期分批對仲景方進行臨床驗證,以期最終確定其標準化的使用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