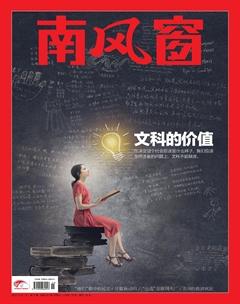高層到底怎么決策?一位國務院副秘書長的卸任后思考
高層到底怎么決策?一位國務院副秘書長的卸任后思考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小涓
本文節選自《江小涓學術自傳》,廣東經濟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年3月
當多數學者有定見時,決策層往往會認真傾聽和對待。
記得1999年起草十五屆四中全會國有企業改革文件時,研究機構和學者個人寫給起草組的研究報告、意見和建議有上百份,絕大多數都認為國有經濟改革必須有實質性進展,不應該在一般性行業中與其他類型企業相競爭。這個“意見包”對改革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例如,有一段時間某種形態的學術誠信問題成為國內學術界的大問題,在國際上也造成不好的影響。但問題的性質和程度都不易判斷,相關部門一時沒有定論,甚至有“放過”的跡象。清華大學的薛瀾教授對問題做了深入分析,認為需要認真處理,并提出了工作建議,切實推動了相關工作。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當各方面呼聲很高,要求制定某種脫離實際、不可持續的福利政策時,經濟學家有時會提出質疑,這種意見也容易被決策者重視和接受。
記得2004年前后,劉遵義先生在《比較》雜志上發過一篇關于社會保障改革不同方案的資金籌措和可持續性問題的論文,有比較詳細的數據測算。我當時正好在起草一個文件,有社會保障方面的內容,我把論文拿給一位領導看,他感嘆地說,要是這類研究多點就好了,我們都知道應該建立保障體系,但賬算不清楚就開始推動,不是負責任的態度。

還有一種情形是,學者們提出一些相對“徹底”和“根本性”的重大建議時,問題看得透徹,思路和道理都正確。但是,決策者們還希望能看到對實施中可能碰到問題的分析和對實施成本的評估,把握好措施的輕重緩急。
例如,現在有學者批評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努力救助企業,使市場不能發揮淘汰過剩產能和落后企業的作用,導致問題積累。然而在當時,多國政府都有相似行為,國家之間有合作但更多的是博弈。
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是我們40年繁榮的源頭。我國經濟社會持續高速發展,快了就容易不穩,因此調控的必要性強于穩定發展的國家。特別是GDP競爭壓力下的地方政府,既有不當干預企業的行為,也有為企業賦能的動力和能力,能夠助推企業進入市場并增強其競爭力。就連阿里巴巴、騰訊、百度這些今日的巨型企業,成長初期也得到過地方政府的諸多支持。
外資企業的立場和觀點就很有意思,它們長期受到地方政府較多有形與無形的關照,彼時并未指認這種做法不符合市場規則。最近幾年我們強調內外資平等待遇,一些外商就抱怨中國投資環境惡化。我暗自想他們以前“找市長”就能搞定的訴求,今日也要按程序辦理了。雖然投資環境還需要進一步改善,但這種內外資平等的原則沒有錯。
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2009年,中組部組織了一個領導干部培訓團,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分別接受兩個月的培訓,我擔任團長。
在哈佛期間,危機處理和應急管理是一門主課,以案例教學為主。第一堂課老師講解幾個案例后開始討論,有一位市委書記上臺說,“危機類型那么多,你們這一套太復雜了,而且掛一漏萬,我們很簡單,只要書記到場,叫誰誰來,讓誰上誰上,需要什么調什么,有預案也只是底線,現場要隨機處理的問題太多”,然后還講了一個自己城市的例子。
此頭一開,書記市長們紛紛登臺講述,后來幾次的課堂就很熱鬧,連老師也覺得很有趣,叫來助教一起聽,認為中國另有一套體制和機制,有的時候很管用。
后來,有一位書記得意地告訴我,上課還是很有用的,他回去后就在一次會議上“很有理論高度”地講了一次應急管理問題,大家都贊揚他有了“哈佛”水平。
我就想起科斯說過,他曾經當過一段時間的公務員,上司從不接受他的意見,他仍然鍥而不舍地提,因為他相信當人們請求上司給指示時,上司一定需要說點什么不同的東西,就會想起他說的。后來發生的事情果真如此。
在國家戰略體系中積極應對老齡社會問題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原新,金牛
本文節選自《人口研究》2021年第2期
伴隨工業化沖擊和現代化塑造,中國社會正由前喻文化轉向后喻文化。
發展新時代全齡友好文化,當務之急在于擺脫消極思維,積極看待老齡社會、老年人和老年生活。
發展新時代全齡友好文化,重點任務在于增強全生命周期人群的生命全程意識。老齡社會問題在老齡社會階段集中爆發,使得文化視角更多地囿于老年群體。實際上,人口老齡化是不可阻擋的人口發展大勢,人人都會變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是每個公民的基本社會責任。2002 年,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從個體角度提出積極老齡化,強調“健康”“保障”和“參與”原則。經過多年探索,中國立足國情實際,從人口年齡結構角度作出與時俱進的文化詮釋:轉變“健康”理念,實施健康中國戰略,落實大健康理念和預防為主方針,不僅關注當前的老年群體,也“從娃娃抓起”,關注未來的老年群體;拓展“保障”內涵,打破年齡刻板印象,從健康保障向精神文化保障擴展;重構“參與”價值,超越傳統的市場評判標準,以“銀齡計劃”為基礎在全齡活動中發揮老年群體潛在價值。
選邊還是對沖—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的亞太國家選擇
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曹瑋
本文節選自《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年第2期
本文的研究對此至少提供了三點啟發性思路:首先,既不要盲目相信中國經濟增長對周邊國家的吸引力,也不必過于擔心中國經濟強大對周邊國家造成的壓力。根據本文的模型結果,中國經濟實力與亞太國家的對沖傾向和外交側重均無關。其次,盡可能降低自身對亞太國家造成的軍事威脅感知。要做到這一點,可能需要中國加強與亞太國家的軍事交流與合作。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中國需要重新思考并處理好中美關系與周邊外交的優先次序問題。當前無論是中美關系還是中國外交戰略都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中國外交的首要任務究竟是保美國還是保周邊仍存在爭論。

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三點:其一,中美關系會負向影響中國與亞太國家關系,這提示我們,想要同時改善中美關系和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其難度可能比較大,特定情況下或許需要在二者之間做出一定的取舍和側重。其二,中美關系惡化的影響并非全部都是消極的。目前主流觀點認為,中美關系下行的大趨勢難以改變。本文的研究提示,中國與亞太國家的關系可能不會隨著中美關系的惡化而惡化,相反有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其三,中國軍事實力的增長會負向影響小國與中國的關系。中國顯然不可能停止發展軍力,因此根據本文的模型結果,除非中美關系惡化,否則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有可能呈現疏遠趨勢。這從一個角度突顯出中國外交在側重美國還是側重周邊之間做出取舍的迫切性。
本文的實證結果向我們提出了一些理論上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例如,本文的模型顯示,無論權力轉移進行到哪個階段,中美兩個大國的實力對比都不影響小國的對沖傾向,這暴露出我們對大國權力轉移本身對小國行為的內在影響機制尚缺乏深刻的認識。又如,無論是從直覺上還是從基本的國際關系理論分析上,小國對大國的經濟和軍事依賴都應當影響小國的行為選擇,但本文的模型結果完全不支持這一點,反倒是此前被多數學者所忽視的小國國內合法性這一因素始終穩定地影響著亞太國家的對沖傾向。對這些反常識關系的進一步研究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大國權力轉移背景下小國行為規律的理解,并幫助大國更準確地制定對外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