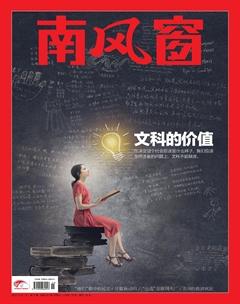文科生和理科生需要同坐“合議桌”
董可馨

央行的論文雖然再一次攪動了文科生的敏感心靈,但也不失為一個重新認識、思考文理科的契機,不僅為了證明文科的價值,也為澄清我們日常觀念中的許多誤區。
為此,南風窗記者采訪了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笑宇,他的新作《技術與文明》關注技術與文明演化的復雜關系,視野兼顧文理,極富啟發性。
啟蒙時代文科理科沒有分家
南風窗:不管在中等收入陷阱和文科生之間建立因果關系成立不成立,前提都是文理分科。但是相對漫長的文明史和教育史,文理分科的出現是比較晚近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國家都實行這個教育制度。
張笑宇:談文理分科要還原到啟蒙時代。那時候還并不存在典型意義上文理分科的想法,因為當時人的頭腦里并沒有這個框架。要說科學的起步,和基督教還有很大的關系,比如牛頓,信神使他相信“第一推動力”的存在,他的書被命名為《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自然科學那時候叫自然哲學。
相比古代,啟蒙時代發生了重要轉向,有兩個人比較關鍵,第一個是伽利略,他有一個關于天體運動的對話,對話的核心是古代的宇宙觀是靜止的,近代的宇宙觀是運動的。這是古今之別。古代宇宙觀設想了一個完美的、和諧的宇宙架構,在里邊去想象、安排、界定地球和人,還有人和事物之間的關系,但是伽利略說不是這樣子的,宇宙本來就是動的,我們要重新界定一切關系。
第二個人是培根,寫《新工具》說現代人思考科學問題要采用工具,而不是像古典時代柏拉圖說的那樣,人類世界都是模仿理念世界。培根認為亞里士多德寫《工具論》用邏輯的范疇來規范客觀世界,使自然屈從于邏輯學,但他要反過來,他的新工具是經驗方法,所有上面那套形而上學必須接受實驗的檢驗,接受不過的就不叫科學。
轉型之后開啟了兩個認知革命,一個是科學范式的,也就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里講的范式革命。另外也開啟了人重新理解社會的革命,因為原先那個模仿宇宙的社會原型被顛覆了,要轉而去研究社會結構、社會運動。這樣,就能理解現代社會所倡導的思想自由、思想解放是怎么回事了。文科生說“思想自由”,是與過去教會的束縛作斗爭,理科生說“思想自由”,是探索自然的奧秘,研究怎么用工程的方式,為人類造福。
可以說,啟蒙時代文科理科沒分家,而是坐在一張桌子上。這里邊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人物是塞繆爾·哈特利伯,他是培根的粉絲,他把自己稱作博物學家,比喻為情報員,要像一個間諜收集信息一樣,收集一切人類相關知識的信息,然后匯集起來。他組成了一個朋友圈,里面有哲學的、社會的、經濟的等各種學者,他的朋友圈到后來就成了英國皇家學會。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蘇格蘭啟蒙運動和美國大革命期間。蘇格蘭啟蒙運動后期,在英國出現了一個由哲學家、科學家、工程師等組成的協會—月光社,他們定期舉行會議,坐在一張桌子為知識拓展和人類社會的改造作貢獻。這是最初的現代啟蒙運動以來的知識體系。
英美德法等離啟蒙運動比較近的國家,比較早沐浴到這些知識革命,形成了先進的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他們來做通識教育,就和過去的古典教育完全不同了,因為那是一個被現代啟蒙精神改造過的東西。現在有些做通識教育的人,還以為應該徹底回到古典,根本不是這樣。
南風窗:在中國語境之下的文理科,和其他國家的文理科還是不一樣。很多中國人對文理科有一種典型理解,認為文科就講些虛的,理科才是干實事的。如果從社會發展的大視野來看,怎么恰當地理解文理科?
平等如何促進經濟,是社會科學研究過幾百年的一個主題,這是一個多么經典的經濟學模型,今天有些人居然以為這是“文傻”在講的。
張笑宇:舉個經典的例子吧。工業革命為什么在英國發生?很多人脫口而出的答案會是,瓦特改進了蒸汽機。但是,什么決定了新技術的應用空間呢?回到歷史,當時倫敦的工資價格相對較高,這是支撐燒煤炭的新型房屋和高額煤炭消費量的重要基礎,再加上高工資帶來的高人力成本,促使企業更傾向于采取那些能顯著替代人力的技術進步。然后在不斷地降低能耗、效率提升的過程中引發了工業革命。可以說,收入水平決定了新技術的應用空間。
一位國際投資機構在東南亞部門的負責人也告訴我,如果投資某種能夠替代勞動力的新興科技產品,他們會優先考慮人均年收入在3萬美元以上的國家,因為只有在這樣的國家,企業才有更強勁的動力來使用這種技術。所以我們看到,社會科學促進社會公平,促進每個人收入提升,保障勞動者和資本議價的權利,反過來會對技術進步產生正向推進。人類社會是在不斷的替代中向前發展的,我們的技術革命從來不是技術進步本身,而是技術在社會中的互動。平等如何促進經濟,是社會科學研究過幾百年的一個主題,這是一個多么經典的經濟學模型,今天有些人居然以為這是“文傻”在講的。
科技發明都要經過一個漏斗的篩選
南風窗:的確,對社會的發展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技術這個單一因素的直線思維上,其中的邏輯關系是很復雜的。
張笑宇:從理論上講,學科邏輯是這樣的,首先,技術、政治、制度、文明進步之間存在一個關系,我把它總結為漏斗喇叭模型,什么意思呢?先從技術的發生開始,最厲害的工程師如詹姆斯·瓦特、埃隆·馬斯克、史蒂夫·喬布斯,他們有多少人、多少發明是被我們銘記的呢?總比例是很小的,大部分的科技發明可能在實驗室里面誕生就結束了。因為所有這些科技發明都要經過一個漏斗的篩選,漏斗的名字叫作商業化或產業化。
如果這項技術能夠產生文明變革,比如蒸汽機動力替代了原來的動力,然后對世界產生以前無法預計的巨大變革,那個漏斗就具有了文明的性質。商業化是一種文明秩序,什么樣的產品會受歡迎,什么樣的產品不受歡迎,這是由文明的秩序決定的。
有一個概念叫“知識煉金術”,是說古代所有的財富都是從地里邊長出來的,或者貿易或者搶來的,但是到了現代社會,我們有知識的力量,能夠無中生有地創造財富,它和你征服了什么地域,已經沒有關系了。而要捍衛“知識煉金術”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成本,比如信用制度,比如政府必須把自己的權力限制在憲法的框架內,然后商人才能夠相信權力是不會肆意侵犯自己的財產的,然后才有更大的投資預期。
從啟蒙運動到工業革命,它造成的非常重大的文明成果是一系列的現代制度,比如產權制度、現代議會制度、公平的辯訴制度、對于大學和知識分子的保護性的制度。這一系列制度能夠很好地保護兩種人,一種是商人,一種是知識分子。這兩種人在古代社會的生存處境都是脆弱的,因為古代社會是一個暴力為主要資源的社會,這兩種人最容易被“搶”。而現在,有一些制度來保護這兩種脆弱。正是這兩種脆弱奉獻了“現代社會的根本運作模型”。
南風窗:對后發國家而言,往往是在受欺凌中感受到新技術的威力。就像近代以來的中國,一開始就是要學習新技術。但學到一定程度又發現還不行。
張笑宇:在英國是這些制度先保護社會上脆弱的人群,然后才有了工業革命的成績。而后發國家是先接觸到了工業革命的成果,然后才開始建立這些現代治理體系。那么對中國來講,我們接觸并學習現代社會的這種模型,經歷了兩個過程。 第一個過程是前30年的建立工業體系,第二個過程是改革開放后建立的保護這些脆弱人群的現代制度—現代制度的含義比較廣,不一定是狹義的現代民主,但至少是對商業和產權的基本保護。
當然,這套制度是保護脆弱的,但也是需要成本的。比如說今天學習法律,最理想的成功道路是學經濟法,畢業之后去大公司當法務,因為它的業務那么掙錢,才能高薪雇人去,在現代法律體系里面維護它的權益,如果它賺錢的那條路給切斷了,那么掌握高級法律技巧的人才就會萎縮,相應的,法律制度缺乏人才的支持,也可能會退化,其他領域也是類似的。
原生紐帶脆弱的地方會缺乏博弈機制
南風窗:我們來談談現實。最近一年來關于外賣騎手的討論很熱,對它的分析基本上是“困在系統里”的思路,你怎么看這個行業?
張笑宇:我們先看珠三角的工人的生活的基本狀況,在深圳,基本上如果廠里邊不提供食宿,工人自己解決租房、吃飯、社交、抽煙、通信、衣服等需求,大概一個月需要4000塊錢,如果要養孩子是大概4500塊,但是深圳的最低工資是2200塊,那中間差價怎么辦?加班。
最厲害的工程師如詹姆斯·瓦特、埃隆·馬斯克、史蒂夫·喬布斯,他們有多少人、多少發明是被我們銘記的呢?總比例是很小的,大部分的科技發明可能在實驗室里面誕生就結束了。
對工人來講,加班是他主動要求的,也是真的沒有辦法。他每天大概要加到11小時到12小時,周六、日不休息,才能掙夠這1800塊的差價。如果工人們的狀態一直是這樣,每天流水線的重復工作,那它就不是一個正常的人之為人的生活,他被“異化”了。
相對于這種流水線工作,做外賣的好處在于,第一,收入要高一些。 第二,做外賣有一種相對自由感,雖然他在系統里被壓榨得很累,但他在外面能碰到別的外賣小哥打個招呼,聊個天,短暫地休息一下,這些都是在流水線上不允許的—流水線上開小差就會扣錢。
現在有那么多人加入外賣行列,恰恰是因為底層人選擇了這條道路,它是一個買方市場,所以所有的外賣平臺都有底氣。也許未來會形成新的商業形態,但是最應該調整的是被騎手服務的那些人,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讓他們愿意為外賣多付兩塊錢,并且平臺企業能給騎手提供五險一金,這樣外賣騎手能稍微輕松一點,但現在這些被服務的人生活也不輕松。
南風窗:騎手相對流水線工人,還是一種相對不那么壞的職業選擇。不過現在以外賣平臺為呈現形態的這樣一種技術模式,它不斷地自我發展、擴大的傾向,已經對人的生活構成了侵壓,沒有知識和技術積累的人,也只能“困”于其中。有沒有什么能夠改進的方法,能讓這種技術模式形成一個相對良性的發展?
張笑宇:我覺得首先可能需要精準定義系統的自我擴大。一般意義上,官僚系統有一種擴張傾向,但是它的擴張和外賣這種互聯網平臺的擴張不是一個類型,互聯網的產品天生的特點就是擴張。道理很簡單,互聯網產品它多賣給一個人的邊際成本幾乎是零,只要你看到它,下載了,這個復制是不需要互聯網廠商付出額外的成本的。所以互聯網的一切產品,它都有天然的壟斷性。
首先要注意到它本身互聯網產品的屬性,這是一個技術壟斷的過程。首先歐洲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所有的互聯網體系最重要的載體是語言,而歐洲的語言是支離破碎的,所以壓根出不了這樣的大品牌。這個問題只有在中美兩國最明顯,而且中美兩國都沒有找到很好的辦法。
美國搞反壟斷業務沒有從這個角度去考慮,它只是從已有的范本的框架里面去判定,比如是否采取不公平的價格競爭等一系列標準,但還沒有從互聯網技術本身的屬性方面去考慮,中國現在要從這個角度去考慮也很困難。這個就是人類現在沒解決的問題,現在唯一看到能對它進行抵制的,或者說在它的沖擊下能提供保護的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國家的法律變革。比如要求平臺跟騎手簽三方合同或者保障五險一金,這是法律可以做的。
第二個是社會的原生紐帶,比如一個共同組織。共同組織有很多種類型,好的類型,如桑德斯很喜歡的概念“社群主義”;差的類型,黑幫、黑手黨,包括出租車組成小團體司抵制叫車平臺。不管是好是壞,有這種紐帶的地方都會形成一定的博弈機制。
比如在美國,外賣服務開展得很早,但它的外賣服務不是國內這種,而是你叫樓下很熟的一個館子,你常在那里吃,已經建立了互信關系。在中國,尤其是一線城市,人的存在是原子化的,很難建立起彼此信任的社會關系,因為你的社會關系都是被工作關系所限定的。當沒有生活紐帶的時候,平臺的談判能力就會高于消費者,也高于騎手,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會突出地造成一些問題。
文科生要坐上“合議桌”
南風窗:所以,很多人強調文科的價值的時候,強調人文關懷要介入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去。
技術的發展到這種地步了,文科生還只講人文關懷和幾千年前的東西,只會越來越不值錢。
張笑宇:我認為現在已經不是人文關懷的問題了,如果文科生把自己的價值局限于人文關懷,我認為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個時代大量的問題,其實已經是人類物種生存的問題。
我前幾天同一個理科生聊天,對方有一句話很經典,他認為一切問題都是工程學問題,既然如此,那么社會問題也是工程學問題。我說你這個說法本身沒錯,但是工程師是以什么樣的標準來制定的?如果你的圖景是真的能夠建立在全人類的立場上,那可以,但如果不是的話就很麻煩。
我在書里也舉了一個例子。受二戰和意識形態對抗影響,美國一些頂尖學者和決策層提出了所謂“人口—國家安全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人口過剩會引發資源枯竭和饑荒,從而導致政治動蕩和叛亂,在政治動蕩中,主張土地改革、均分財富的社會主義政黨會贏得支持,這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進而引發戰爭。那怎么辦?美國人就用工程學的思維,在發展中國家倡導“綠色革命”,為當地推廣新品種農作物、化肥和灌溉技術,讓農民吃得飽飯,以“遏制”共產主義革命。
這個工程學思維當然有效果,墨西哥等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比較弱,但是它也產生很多相應的后果,比如人口的爆炸性增長、外資對本國小農業主的擠壓、延緩了本應進行的社會結構改革等等,這是當年工程學思路沒有解決的。
當有一套工程學的方法被提出時,一個好的方案是,文科生也坐在桌子上一起探討,但是不講虛的,就講實的。比如要搞基因編輯,可能會對社會的哪些基本倫理產生破壞,甚至摧毀人類的存在基礎。這些要討論清楚。
南風窗:其實這是對文科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靠單純的知識記憶或者風花雪月肯定已不足以應付未來的需要。
張笑宇:當然是了。技術的發展到這種地步了,文科生還只講人文關懷和幾千年前的東西,只會越來越不值錢。文科生真正該做的事是找到“合議桌”,提出一個關于技術進步能夠分庭抗禮的方案,能夠告訴決策者,你這么搞的后果可能是 ABCD,這個 ABCD真的是你想要的嗎?這個“合議桌”是能夠發揮新作用的一個形式,如果搞通識教育,也不是回到柏拉圖,不是回到孔子,我們不可能停留在那個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