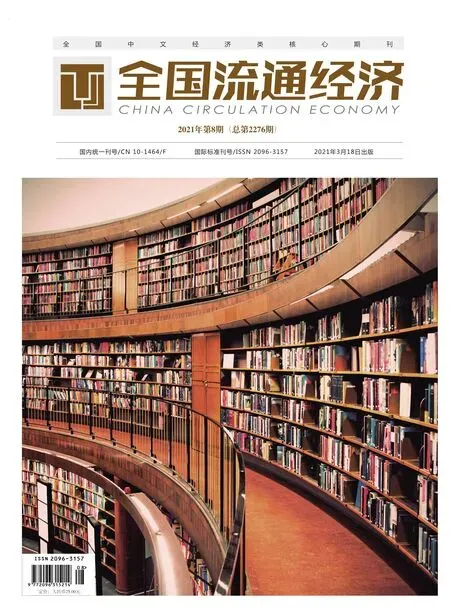異質化視角下信貸資產證券化動因研究
——基于2014年~2019年我國商業銀行面板數據
陳玉馨 陳 偉
(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081)
一、引言
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定義,目前國內外普遍的說法是:將原本不流通的金融資產轉換成為可流通資本市場證券的過程。Hess&Smith(1988)和Zweig(1989) 指出信貸資產證券化是指能使基礎資產重組成一種多個現金流、低風險的資產組合,同時對基礎資產信用增級及評級,原始權益人可以獲得更低成本的款項。自2012年我國重啟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后,信貸資產證券化也逐漸成為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之一。呂懷立等(2017)認為,它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為發起人將其持有的信貸資產組合打包成資產池,并以該資產池在未來產生的現金流為支持,向投資者發行受益證券的一種結構性融資活動。
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動因的研究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發達市場國家出現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趨勢。通過文獻梳理發現,現有的關于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流動性動因(Lourskina,2009;Samaniego-Medin,2010)、資本監管應對動因(Ambrose,2005;Christian,2015)、盈利性動因(Greenspan,2004;Massimiliano,2010)和信貸風險轉移動因(Cakern,2010;Le,2016)。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學術界當前的研究關于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動因的差異性研究較少。因此,本文擬通過首先尋找對我國各種規模的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生影響的因子。在此基礎上,將我國樣本對象分為大型商業銀行和中小型商業銀行,進一步剖析分別影響不同類型商業銀行證券化動機的主要因素。最后,結合國內外先前發展經驗,對我國商業銀行未來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發展提出可行性建議。
二、變量說明與模型構建
1.變量說明
本文通過梳理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影響因素的理論基礎,兼顧數據的可得性和統計口徑,構建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驅動因素的指標體系如下:
(1)被解釋變量
本文以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度為研究對象,并將其定義為:銀行ABS發行總額與當年商業銀行總貸款余額之比表示。由于各銀行均未披露信貸發行總額數據,因此本文采用其基礎資產類型統計加總得到。
(2)核心解釋變量
①貸款增長率(lgrit)
貸款增長率是指商業銀行本期總貸款余額相對上期貸款余額增長的速度。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越高,其流動性風險就越大。銀行為了保證持續經營,避免出現“擠兌”,就需要有更多的流動性資金支持,而適當的流動性水平對商業銀行的存續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提出假設1: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lgrit)越大,其發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意愿就越強烈。
②非利息收入占比(nippit)
非利息收入占比是指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與當年總營業收入的比值。由于利率市場化的趨勢加強,傳統的通過存貸款利息差額來盈利的方式已經不能滿足當前商業銀行的發展需求,因此國內大部分銀行開始加大對非利息收入業務如投資業務與理財業務的投入。基于分析,提出假設2: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越大,其發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③凈資產收益率(rnait)
凈資產收益率是指商業銀行的稅后利潤除以凈資產得到的百分比率。凈資產收益率值越高,說明投資(包括信貸資產證券化)帶來的收益越高,由此提出假設3: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度與凈資產收益率呈正相關關系。
④不良貸款比率(nplrit)
不良貸款比率是指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總額占總貸款余額的比重。不良貸款率越高,也預示著面臨較高的資金安全性風險。該指標也是衡量銀行綜合考慮風險性與收益性進而選擇是否參與信貸證券化的指標。基于分析,提出假設4: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率越高,其越有可能發行信貸資產證券。
(3)控制變量
本文選取資本充足率和存貸款比率作為控制變量。

表1 變量及其定義表
2.模型構建
根據上述變量說明和理論分析,本文采用與 Farruggio &Uhde(2015)一致滯后一期的研究方法,以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參與度為被解釋變量,選擇核心變量,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pisit指第i個商業銀行在第t年的信貸證券化參與度,lgrit-1指第i個商業銀行在第(t-1)年的貸款增長率,nippit-1為第個商業銀行在第(t-1)年的非利息收入占比。
為驗證其他因素對商業銀行信貸證券化的影響,在核心解釋量的基礎上加入所有選取的控制變量后,構建模型如下:

三、實證分析結果與討論
1.數據來源
基于數據可得性和統計口徑等因素,本文選取2014年~2019年共37個上市商業銀行(12家大型商業銀行和25家中小型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數據庫、CSMAR 數據庫、中國資產證券化分析網等。
2.主要實證結果
(1)實證結果

表2 實證結果與穩健性檢驗
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證券化參與度(pisit)進行Logistic回歸檢驗,結果如表3第(1)、(2)、(3)列所示,模型(1)和(2)為未完全加入控制變量的結果,模型(3)為將本文選取的所有解釋變量納入模型的結果。第(4)列回歸結果說明,貸款增長率的系數在9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負;非利息收入占比對商業銀行參與信貸證券化的積極性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凈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負債率和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度都呈現正相關關系。從不良貸款比率對信貸證券化參與度的影響來看,不良貸款率越高,相應的信貸證券化參與度也越高。
表3第(1)、(2)、(3)列的實證結果顯示了商業銀行各項財務指標對其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參與度的影響。
第一,實證結果表明貸款增長率與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參與度負相關,與假設1矛盾。現有觀點一般認為:銀行的貸款增長率越高,表明需要準備更多的流動性資金以應付客戶隨時的提款需要,因此銀行傾向于通過發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以盤活經濟,避免出現流動性危機。而通過實證研究結果卻不然,這可能是受到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發展歷程影響所致。2012年我國資產證券化試點重啟以來,一直沒能突破“叫好不叫做”,甚至有人認為是監管機構的“一廂情愿”,因為發行人證券化動力不足。
第二,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參與度與非利息收入占比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一現象的可能原因在于:由于傳統的存貸款業務所帶來的利息收入無法使得商業銀行獲得較多的超額收益,因此商業銀行傾向于選擇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來盤活總體資金存量,增加銀行收益,假設2正確。
第三,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度同凈資產收益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一方面,經濟效益較高的銀行開展信貸ABS的動機較強,以求獲得更多的收益,另一方面,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所帶來的收益越高,也會使得商業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越高。二者具有雙向互動機制,假設3正確。
第四,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與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度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隨著不良貸款率的上升,商業銀行資產質量趨向惡化,此時商業銀行會面臨較大的信用風險。因此,商業銀行傾向于發行信貸證券化產品,以減少不良貸款在總資本中的占比,擴大總體資本規模,假設4的正確性得到了驗證。
總體上說,非利息收入占比、凈資產收益率、凈資產負債率和不良貸款比率是驅動我國商業銀行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的主要原因,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具有較強的內生動力。
(2)穩健性檢驗
①刪除部分數據
本文采取隨機刪去2014年數據的方法以證明內生性變量基本已被控制,表3第(4)列為保留80%樣本的實證結果。再次進行回歸,結果表明:核心變量仍然顯著,且估計出的系數符號與大小同原模型較為接近,實證結果穩健。
②替換實證模型
為檢驗以上實證結果是否具有可靠性,本文進行實證結果的替換,采用probit模型進行再次檢驗,表3第(5)列為使用probit模型的結果。研究結果表明,替換實證模型后,本文的五個解釋變量在 95%的置信水平下依舊顯著,與前述實證分析結果一致,說明計量檢驗結果非常穩健。
(3)差異化分析
由于不同銀行的各項財務指標對其信貸證券化參與度的影響不同,因此本文結合我國商業銀行體系的實際特征,將商業銀行分為中小型銀行組和小型銀行組,進行差異化分析。其中大型銀行組包括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和部分股份商業銀行,共12家;中小型銀行組包括部分城市商業銀行和部分農村商業銀行,共25家。差異化分析結果見表3,第(1)、(4)列分別是中小型銀行和大型銀行加入部分解釋變量的logistic回歸結果,第(2)、(5)列分別顯示了中小型銀行和大型銀行加入本文所選取的所有解釋變量的logistic實證結果,第(3)、(6)列則是采用probit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的結果報告。
① 回歸檢驗結果
由表3的(1)、(2)、(3)列可知,在中小型銀行組的回歸結果中,非利息收入占比、凈資產負債率與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度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性,而貸款增長率、凈資產收益率和不良貸款比率的影響卻變得不顯著。
由表3的(4)、(5)、(6)列可知,在大型銀行組的回歸結果中,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度同貸款增長率顯著負相關,與資本充足率則表現顯著正相關,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參數估計變為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大型商業銀行受到監管部門較為嚴格的理財業務和債權投資嚴苛的業務監管要求,因而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和部分股份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較低,更傾向于選擇與存貸款利息收入相關的業務作為非利息收入的主要來源,因而缺乏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由于《巴塞爾協議Ⅲ》及國內金融監管政策對系統性重要銀行規定的監管要求,因此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在資本充足率方面仍有較強的動力,信貸資產證券化將對大型商業銀行擴充資本具有重要作用。

表3 信貸證券化參與度的異質性分析
② 差異化分析
由于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對于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偏好不同,因此其對于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的積極性也不同。大型商業銀行參與積極性較中小型商業銀行低,原因如下:首先,在利率逐步市場化的趨勢下,雖然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差變小,但是由于大型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基數大,從而該趨勢對其盈利情況的影響較小。因此,大型商業銀行仍可以通過貸款利差來獲取較多收益。其次,由于我國大型商業銀行的理財等其他業務受到監管部門較為嚴格的監管,為了規避風險,其對創新型業務的偏好水平較低,短期內我國大型商業銀行仍會選擇通過存貸利差來獲取較為穩定的收益。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結合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現狀,通過對銀行多個財務指標與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度進行實證分析,并對不同類型的銀行進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參與度的差異性進行分析。結果表明:第一,我國商業銀行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動因主要是非利息收入占比、凈資產收益率、凈資產負債率和不良貸款比率。第二,大型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內生動力較弱,目前仍以存貸款利差來獲取收益,資本充足率是影響其開展信貸證券化的主要原因;而中小型商業銀行受到非利息收入占比、凈資產負債率等因素的驅動,信貸資產證券化的積極性較高。基于分析,本文提出下列可行性建議:
第一,商業銀行應積極推動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多樣化,擴大投資者投資領域,但同時應堅持適度原則。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起步較晚,基礎資產較為單一,當前大部分種類仍以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為主。因此,我國證券化市場應該豐富基礎資產的種類,增加證券化種類和范圍,增加銀行的經營績效,逐漸擴大證券化市場的廣度和深度。
第二,大型商業銀行應當適當地提高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參與度。由于存款資源理財化的發展,大型商業銀行的存款優勢逐漸被削弱,流動性問題日益凸顯,而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是其化解流動性風險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應當提高發展該業務的內生動力。
第三,監管機構應當在確保金融業穩定的前提下,滿足商業銀行需求并進行合理的引導。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由于受到監管部門較為嚴苛的業務審查,為了規避風險,仍以傳統的存貸利差為主要收益來源。因此,監管部門應適當調整監管策略,避免由于監管過嚴,導致對銀行業務的擴展產生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