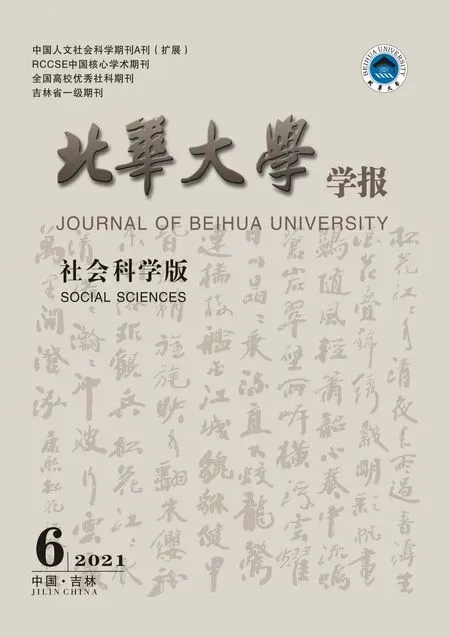明末清初漢語二語教學語法:理論框架、特點和局限性
劉振平 李倩穎
引 言
16世紀末,一些西方傳教士陸續進入中國。為了能夠順利傳教,他們開始學習漢語,并留下了一批珍貴的學習材料。根據相關文獻記載,早期來華傳教士多是跟隨中國人學習漢語,[1]接受中國傳統的語文教育。因此,重誦讀、抄錄而輕語法,主要靠背誦和抄錄一些常用詞語、句子和漢語經典著作(如“四書五經”)來逐漸獲得運用漢語進行日常交際和傳教的能力。[2]前言48;[3]28早期來華傳教士流傳下來的材料,如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1543—1607)于1584—1588年間編寫的《葡漢詞典》、利瑪竇(Matteo Ricci S J,1552—1610)于1606年出版的《西字奇跡》和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7)于1626年寫成的《西儒耳目資》等,都是主要關注漢語語音、詞語和漢字,用他們熟悉的語言來注釋漢語詞語和給漢字注音,較少關注語法[4]。
但這種較少關注語法的局面很快就發生了改變。“傳教士們都通曉拉丁語,熟知拉丁語的語法分類”[2]前言36,他們在總結漢語學習規律、不斷探尋學習方法的過程中不免會嘗試借鑒拉丁語的學習經驗,將已知的拉丁語語言模式套用在漢語上。在學習方法上,他們也深受當時拉丁語傳統教學法的影響,將背誦語法和范文作為主要的學習手段。于是,傳教士們就開始以拉丁語教學語法框架為基礎來構建漢語教學語法體系,并將漢語語法知識的講解和訓練作為所編教材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們能見到的第一本以語法為主要內容的漢語二語教材,是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1614—1661)于1653年用拉丁文寫成的《中國文法》(GrammaticaSinica)。該教材在漢語與拉丁語對比的基礎上,借助拉丁語教學語法術語,簡單介紹了漢語語法的基本情況。隨后,傳教士們編寫的漢語教材大都把語法作為重要的內容。如西班牙傳教士瓦羅(Franciscan Varo,1627—1687)于1682年用西班牙文寫成的《華語官話語法》(ArteDeLaLenguaMandarina)、法國傳教士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于1728年用拉丁文寫成的《漢語札記》(NotitiaLinugaeSinicae)等。
一、明末清初漢語二語教學語法的理論框架和內容編排
(一)套用傳統的拉丁語教學語法框架

拉丁語在西方社會曾長期作為課堂教學語言,同時也是教會活動語言,所以,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都系統學過拉丁語。傳統的拉丁語教學一般都要求學生背誦拉丁語語法規則,因此,這些傳教士也都比較熟悉拉丁語語法體系。而且,在這些傳教士的心目中,“拉丁語似乎具有某種‘更高的威望’,而這種‘威望’會進一步影響他們對漢語的認識,以及選定拉丁語作為比較的對象”[2]前言36。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華傳教士,如衛匡國、瓦羅、馬若瑟等,都基于普利西安《語法原理》中的拉丁語語法體系來構建漢語教學語法體系。
(二)用拉丁語、西班牙語展示漢語語法框架
在內容的編排上,這個時期的漢語二語教材主要是用拉丁語、西班牙語等傳教士熟悉的語言來介紹漢語的語音、文字和語法。事實證明,用學習者的母語或其熟悉的語言來介紹漢語語法知識,能夠減少語言理解上的障礙,有著明顯的合理性。[8]但這些教材大多只是對各個方面做知識性的介紹,對漢語語法內容的講解也非常簡略,只是簡單展示了漢語語法的框架,沒有太多的例句、課文和練習等用于語言訓練,與如今的漢語二語教材相差較大。語法部分,更像當今面向漢語二語學習者并用其母語編寫的語法書。學習者學完教材,能夠對漢語語法體系有個基本的了解,對漢語與拉丁語、西班牙語等學習者所熟悉的語言之間的語法異同點也會有一定的認識。但學習者要想真正學會漢語,不能僅僅靠這么一本教材,還要閱讀、翻譯大量的經典文學作品等。[2]4,145
這個時期,內容編排上比較特殊的一部教材是馬若瑟編寫的《漢語札記》(NotitiaLingaeSinicae)。該教材編排了大量的例句,“上至經籍,旁及諸子,下涉元曲、明清小說,提供的例子超過12 000條”[3]322。馬若瑟認為單純學習語法規則會比較枯燥乏味,如果教材能夠提供大量的例句,學習者就可以通過多個例句的學習來強化語法規則的記憶,提升運用漢語的能力[3]324。然而,這種做法在19世紀中期以前是很少見的,因此,遭到了傅爾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等漢學家的非議。[3]323
二、明末清初漢語二語教學語法的特點
(一)注重研究“格”“數”“級”等語法范疇在漢語中的表達
因為漢語的詞語“缺乏形態變化”這一特點非常明顯,所以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普遍認識到了漢語沒有“格”“數”“級”“性”“時態”“式”等方面的詞形變化。但是他們并不否認漢語中也存在這些語法范疇,認為漢語主要是依靠一些“小詞”或“虛詞”來表達這些語法范疇。因此,又都努力找尋漢語中表達這些語法范疇的手段,并詳加闡明。
衛匡國《中國文法》第二章介紹了漢語中表達名詞、代詞“數”和“格”,表達動詞“時”(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和“式”(主動式、被動式、祈愿式)的一些具體手段;第三章第五節具體介紹了形容詞“級”在漢語中的一些表達形式,第六節補充說明了代詞“格”的一些表達形式。瓦羅《華語官話語法》第三章介紹了漢語名詞、代詞如何與“小詞”配合表達“格”“數”等語法范疇;第四章第三、四節分別介紹了形容詞“比較級”“最高級”的一些具體表達形式;第八章介紹了動詞“時態”(現在時、未完過去時、過去完成時、先過去時、未完將來時、將來完成時等)和“式”(祈愿式、虛擬式和不定式)的表達形式;第九章介紹了“被動式”的表達形式。馬若瑟《漢語札記》在第一編第一章第一節里,首先明確指出了漢語沒有表達“性”“數”“格”等語法范疇的詞形變化,然后介紹了名詞“格”“數”和動詞“式”“時態”在漢語中的表達形式;在第一章的第二節里介紹了漢語中表達形容詞“級”的一些手段。
“因為第二語言學習者,頭腦中已建立起母語的語法體系”,[9]當再接觸一種新語言的語法體系時,勢必要從母語中尋找一些可遵循的理據。正是因為教學者意識到了這一點,“格”“數”“級”“性”“時態”“式”等語法范疇在漢語中的表達方式便成了各時期漢語二語教學語法體系的重要內容。上文的分析表明這些17—18世紀的漢語教材對此非常重視,19世紀漢語二語教學語法體系同樣如此,現行漢語二語教學語法體系的奠基之作《國語入門》(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10]《漢語教科書》(時代出版社,1958)[11]亦是如此。指導漢語二語教學和教材編寫的多個教學語法大綱,也一直把“動作的態”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如:《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試行)》(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8)[12]和《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語法等級大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13],在甲級大綱中專門設置了“動作的態”的語法點;《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大綱》(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14]在“詞類”部分專門講了“時”“態”等語法范疇在漢語動詞上的表現;《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教學大綱》(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15]對動作的完成、持續、進行、變化、經歷等都設立了專門的語法條目(見大綱的第11、14、41、42、43、75、76、81、82條);《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言專業教學大綱》(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2)[16]和《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大綱(長期進修)》(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2)[17],分別在《一年級語法項目表》和《初等階段語法項目(二)》專門設置了“動作的態”的語法點;《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級標準》(GF 0025—2021)在一級和二級語法點中都有“動作的態”條目,分別列出了“【一40】變化態”、“【一41】完成態”、 “【一42】進行態”、 “【二70】持續態” 、“【二71】經歷態”五個語法點。
(二)借用拉丁語語法術語,對術語不做過多解釋
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所編的漢語二語教材,普遍以學習者已經具備拉丁語語法知識為前提來講解漢語語法。因此,教材在介紹漢語語法時,會直接使用拉丁語語法體系中已有的術語,但不會對這些術語做過多的講解。如拉丁語語法體系中有“名詞、代詞、動詞、分詞、介詞、副詞、感嘆詞,以及連詞”[2]30,無論是衛匡國的《中國文法》,還是瓦羅的《華語官話語法》和馬若瑟的《漢語札記》,都是首先分析漢語中是否有對應的詞類,在發現漢語中有對應的詞類后,便直接用這些術語來稱說,根本不去對這些術語進行解釋說明。
從現在的語言教學理念來看,該時期的教學語法在這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是因為長期以來的教學實踐和研究表明:少用語法術語是描述語法點時應遵循的一個重要標準。如朱德熙指出:“講語法概念的目的,只是為了說明語法規律。我們不能本末倒置,把解釋概念本身當成教語法的目的。”[18]學習者的語言能力跟掌握多少語法術語沒有密切的關系[19],因此,不應引導學習者把注意力放在語法術語和分類上[20],描述語法內容時也不應過多地使用語法術語。過多地使用語法術語,會增加學習者的負擔,使其疲于理解和記憶一些晦澀難懂的術語概念。呂叔湘指出:“很多人要求語法學家不用術語講語法。這當然是理想的辦法,可就是不容易辦到。雖然不容易辦到,跟一般人講語法的確應該盡可能這樣辦。”[21]因此,在描述每一個詞的用法時應“力求少一個術語,多用簡單的文字說明”[22]。
(三)具有語言對比意識,重點介紹漢語語法特點
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所編寫的漢語二語教材,對漢語與拉丁語語法的相同之處,未做過多的介紹,而是重點講解其不同于拉丁語語法的地方(即漢語語法特點)。這表明這一時期的來華傳教士在一開始確定漢語教學語法的內容時,就具有了語言對比的意識。如漢語跟拉丁語語法之間最為明顯的不同——漢語缺乏形態變化,而拉丁語可以通過形態變化來表達“格”“數”“級”“性”“時態”“式”等語法范疇。來華傳教士不難發現這一點,因此,他們就在教材中詳細地介紹漢語表達這些語法范疇的手段,以讓學習者認識到漢語在這些語法范疇表達上的特點。又如,漢語中擁有豐富的量詞,這也與拉丁語明顯不同。這一時期的來華傳教士對此也都很重視,衛匡國、瓦羅就把量詞作為一個獨立的詞類,進行了詳細介紹。馬若瑟雖把量詞作為名詞的一個附類,但也同樣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講解。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表明,成人漢語學習者在語言學習過程中,能夠利用已有的語言系統、知識結構和思維能力對漢語的語法進行邏輯思辨,從而產生一系列語言遷移現象。例如,學到一個語序排列,他們會馬上跟母語里相對應的排列比較有什么不同。[23]因此,進行語法對比是選擇漢語二語教學語法內容的一個重要步驟,也是學界的共識。如《漢語教科書》雖然采取的是分課編排語法點的做法,但還是在緒論中點出了漢語語法的一些特點。[11]16呂叔湘指出:“英語的語法跟漢語的語法比較,有很多地方不一樣。當然,相同的地方也不少,不過那些地方不用特別注意,因為不會出問題,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地方。”[24]趙金銘指出:“給外國人講漢語語法,不能就事論事,只講漢語本身。因為外國學生的頭腦里早已先入為主地有了其母語或所學外語的語法規律,他們會時時拿來比附。如果通過語際對比來講,就會更加顯露漢語語法的特點。只有突出漢語語法特點并講透了,外國學生才易于理解。”[25]陸儉明也認為,對英語背景的漢語學習者進行語法教學時,漢語中有而英語中沒有且學習者常出錯的語法現象是教學的重點內容。[26]另外,還有一些面向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漢語語法書,如孫德金的《漢語語法教程》(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2)[27]、徐晶凝的《中級漢語語法講義》(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8)[28]等也都先介紹了漢語的語法特點,然后才詳細介紹具體的語法點。后來的這些研究證明,明末清初的來華傳教士在構建漢語教學語法體系時,能夠具有語言對比意識,重點介紹漢語語法的特點,是非常正確的做法。
(四)認識到漢語語序和虛詞的重要性
由于漢語的詞語缺乏形態變化,因此詞語間的語法關系需要靠語序和虛詞來表達。《中國文法》里有如下表述:“由于位置的變化,同一個詞可分別做名詞、形容詞和副詞” ,“如果不是因為位置不同的話,形容詞與名詞的區別不大。”[29]這表明衛匡國認識到了漢語語序的重要性。《華語官話語法》第一章“若干戒律”中指出:“為了說好這種語言,有三件事要牢記于心:……;第三,一個要素在句子里必須有適當的位置。這三點都是必要的,尤其是詞序(word order),因為如果詞不在適當的位置上,句子就會變得不能理解。”[2]12-13“我們的教士不要忘記這一點:措辭和詞序是漢語的精要所在,缺了它們就不可能正確地說這種語言。”[2]16馬若瑟同樣注意到了漢語詞序對意義表達的影響,即詞序不同所表達的意義也不同。他在《漢語札記》中明確指出,形容詞放在名詞前和名詞后,意思迥然不同,如“大房子”和“房子大”;“惡人”和“人惡”等。[30]此外,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也都認識到了漢語中虛詞的重要性。這從他們都努力尋找漢語中表達“格”“數”“級”“性”“時態”“式”等語法范疇的虛詞(衛匡國稱作“助詞”、瓦羅稱作“小詞”)就能看出。
傳教士們能夠認識到漢語詞序和虛詞的重要性,這對他們學好漢語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漢語中虛詞數量眾多,且用法復雜,功能多樣,是表達語法意義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以來的漢語二語教學實踐也表明,學習者大量的語言偏誤與虛詞的使用有關,如虛詞缺失、虛詞誤用、虛詞搭配不當、虛詞的擺放位置不當等。[31]因此,掌握虛詞的意義和用法也就成了學好漢語語法,乃至學好漢語的關鍵。[32]
三、明末清初漢語二語教學語法的局限性
(一)重詞法輕句法,以詞法為綱
衛匡國的《中國文法》主要是用拉丁文寫成的,有三章內容。第一章是講漢語語音的,第二、三兩章才是講語法的。第二章有三節,分別為“名詞及其變位”“代詞”“動詞的變位”;第三章有七節,分別為“介詞”“副詞”“感嘆詞”“不常用連詞”“名詞的原級、比較級和最高級”“代詞附錄”“數詞和數量詞”。這兩章的內容基本上屬于詞法范疇。
瓦羅的《華語官話語法》對句法有所關注,單獨設置了一章來介紹一些句法內容,即第十一章“構句方式”。但這一章的內容很有限,只是簡單介紹了漢語的四種基本句型(兩種主動句型:施動者+動詞+受動者,施動者+動詞;兩種被動句型:受動者+表被動的小詞+施動者+動詞+“的”,受動者+施動者+動詞),以及領屬格、與格、賓語、離格、副詞等在句中的位置。另外,第八章講動詞的變位時對祈使句式的結構有所介紹。
馬若瑟的《漢語札記》對句法論述的嚴重不足是其一大缺憾。[33]雖然第一編第一章第二節名為“句法”,但實際講解的內容卻是“級”范疇在漢語中的表達形式。第二編第一章名為“書本中的語法和句法”,但下面三節的內容分別是“表多數的詞”“代詞”“字類活用”,依然屬于詞法內容。整體而言,全書跟句法有關的內容不多,只是在講有些詞時會涉及一些有關句式和語序的問題,如講解“把”的用法時,根據“把”的意義將它出現的句子分為了三類,但是,做此分類并不是為了深入認識“把”字句,而是為了突出“把”這個詞的多義性。
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只注重漢語詞法內容的講解顯然是沿襲了古希臘—拉丁語語法教學和研究的傳統。因為無論是狄奧尼修斯的《讀寫技巧》,還是普利西安的《語法原理》,都是只論述了詞法。希臘語和拉丁語都是具有豐富形態的語言,只講解詞法足以能夠幫助人們理解和生成句子,因為詞形變化能夠清楚地表明詞語在句中的位置和功能。但是,漢語中的詞語缺乏形態變化,靠語序和虛詞標明詞語之間語法關系,分析這種語言的結構規律,只講解詞法顯然是不夠的。
(二)混淆名詞和形容詞的界限
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基本上都是將漢語名詞和形容詞混作一類。如衛匡國、馬若瑟都是將形容詞歸入名詞類。衛匡國在《中國文法》第三章第五節中主要介紹的是形容詞“級”的表達,卻命名為“名詞的原級、比較級和最高級”;馬若瑟的《漢語札記》認為物質名詞加上“的”就有了形容詞的意思;瓦羅的《華語官話語法》第四章認為名詞和形容詞同屬靜詞(nomimal,西班牙文nombre),靜詞有格但無時態,有比較級和最高級的區別。
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未能厘清名詞和形容詞的界限,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早期拉丁語法中,名詞包括實體名詞(noms substanties)和形容名詞(noms adjectives)。形容名詞也稱為‘附加名詞’,是名詞的一個附類,可變格,但要附加在實體名詞上。”[3]153-154傳教士受拉丁語語法的影響,將拉丁語中實體名詞和形容名詞的關系套用在漢語名詞和形容詞的區分上,認為二者同屬一類。其二,漢語中詞語缺乏形態變化,傳教士們無法通過形態來判斷漢語的詞類。由于拉丁語中每類詞充當的句子成分是基本固定的,通過觀察詞充當的句子成分也能判斷出詞類,所以當無形態可據時,傳教士勢必會轉而通過觀察詞語充當的句子成分來判斷其類別。然而,漢語的詞類與句法成分之間并非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名詞和形容詞都可以做定語、主語、賓語、謂語、狀語,因此他們也就很難把兩者區別開來。
(三)介詞和副詞的界定脫離漢語語法實際
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對漢語介詞和副詞的認識也比較模糊。比如,將一些方位詞視為介詞。漢語方位詞的主要語法功能是放在名詞后面構成方位短語,而方位短語“名詞(名詞性短語)+方位詞”基本對應拉丁語的介詞短語“介詞+名詞(名詞性短語)”,因此,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們都簡單地將漢語方位詞看作介詞。《中國文法》里介紹的介詞基本上都是方位詞,《官話口語語法》介紹的介詞有一大半是方位詞,《漢語札記》介紹的介詞有10個,其中6個(里、中、上、下、前、后)是方位詞。
再比如,把時間名詞和一些形容詞、指示代詞、數量短語等視為副詞。這主要是因為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依據拉丁語中副詞的判定標準來判定漢語副詞。具體來說,一是靠句法位置,在句子中能夠修飾動詞或形容詞的詞語被認定為副詞;二是靠語義,如果漢語句子中的某個詞語翻譯成拉丁語是副詞,或者與拉丁語中的副詞語義相近,那它也會被認定為副詞。正是因為他們簡單地運用拉丁語中的副詞判定標準,從而把漢語中很多能夠做狀語的形容詞、指示代詞、時間名詞、數量短語等都認定為副詞。如《中國文法》中介紹的副詞主要有以下幾類:(1)表示選擇的“巴不得”;(2)表示回答的“是、自然”;(3)表示確認、肯定的“貞的、貞貞的、果然、真真的(真正的)”;(4)表示否定、禁止的“不、莫、無、不可、不然”;(5)表示疑惑、不肯定的“或、或者”;(6)表示選擇性的“寧、寧可”;(7)表示比較級的“更、更多、更好”;(8)表示聯合、結合的“同、一同”;(9)表示轉折的“另、另外”;(10)表示做法、傾向于……的“謹、強、茍且”;(11)表示時間的“今日、明日、昨日、前日、后日”;(12)表示地點的“這里、那里、各處”;(13)表示數量的“一次、二次、多”(包括概數和序數);(14)表示事件發生得偶然、意外的“或然”;(15)表示類同的“如、比如、不同”;(16)表示性質的“善、妙、好、好得緊、巧”;(17)表示量的“少、多、夠、夠了”;(18)表示唯一的“但”;(19)表示非全部、不完整的“差不多”等。這些所謂的“副詞”當中,實際上包含了一些時間名詞、指示代詞、形容詞、數詞和數量短語等,如“今日、明日、昨日、前日、后日、后來”“這里、那(哪)里、各處”“善、妙、好、巧、多、少”“一次、二次、十年多、十多年、第一”等。
《漢語札記》同樣是簡單靠句法位置和語義來判定副詞的,只不過舉例更多,還把一些文言疑問代詞(“如何”“何如”等)也看作了副詞。而《華語官話語法》除了把動詞前后、語義上修飾動詞的詞語看作副詞,甚至還把名詞的一些修飾成分和作主語的時間詞也都看作副詞,如把“年邊來了”“月尾采取”中的“邊”“尾”,以及“將暮來了”“半夜來了”中的“將暮”“半夜”,也都看作副詞。
由于中國當時并沒有出現系統的漢語語法著作,傳統語文學的研究并沒有對副詞和介詞進行劃類(多以“虛字”“助字”等統稱),明末清初的傳教士們無現成的研究成果可據,便簡單地對照翻譯進而依據自己母語中兩類詞的界定標準來區分漢語的副詞和介詞,最終做出不符合漢語詞類實際的判斷也就在所難免。
(四)對語氣詞的詞類地位認識不充分
明末清初的來華傳教士并沒有認識到漢語中“語氣詞”應具有的獨立詞類地位。在他們所編寫的漢語教材中,有些對語氣詞根本不予理睬,如瓦羅的《華語官話語法》。有些雖對語氣詞有一定的關注,但并未將其視為一個獨立的詞類,而是與其他詞類混雜在一起,如《中國文法》把語氣詞混在了感嘆詞和連詞中。該書第三章第三節“感嘆詞”,總共列出了6個詞,其中實際上只有“唹呼”是感嘆詞,“苦、苦惱、可憐、奇”是形容詞,“哉”是語氣詞;這一章的第四節講解“不常用連詞”,其中卻講解了“也矣”,并又稱其為“語氣助詞”。《漢語札記》構建的漢語詞類系統中,語氣詞和連詞、助詞都沒有作為獨立的詞類,而是跟一部分副詞合在一起統稱“虛詞”。該教材中例解的虛詞,有一些(如“也、耶、邪、阿、呵、呀、哩、呢、波、那、與、耳、焉、哉”等)應當歸為語氣詞。可見,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對漢語語氣詞關注不夠,沒有給予其獨立的詞類地位,這可能跟拉丁語里沒有語氣詞有很大的關系。
結 語
明末清初的漢語二語教學語法體系主要是由來華傳教士構建的。受其拉丁語語言背景和當時教學法的影響,傳教士們主要套用傳統的拉丁語教學語法框架來構建漢語教學語法體系,并用拉丁語、西班牙語來展示漢語語法框架。因此,明末清初的漢語二語教學語法體系大致呈現出如下特點:關注“格”“數”“級”等語法范疇在漢語中相應的表達形式;盡可能借用拉丁語中的語法術語,但對術語不做過多解釋;具有語言對比意識,重點介紹漢語語法特點;認識到了漢語中語序和虛詞的重要性。同時,簡單套用拉丁語語法框架也導致這種教學語法重詞法輕句法、混淆詞類界限,以及未充分認識到語氣詞在漢語中的獨立詞類地位等不足與局限。
梳理明末清初漢語二語教學語法的特點,對當下一直呼吁的漢語二語教學語法改革有以下兩方面的啟示:一是在語法內容的選取上,應針對學習者的母語背景,加強漢外語言對比,將漢語相較于學習者母語而體現出的語法特點作為重要內容,如“格”“數”“級”“時態”等語法范疇的表達方式、語序和虛詞的重要性、詞類句法功能的多樣性、量詞和語氣詞的獨特性等;二是在語法術語的使用上,可以直接借用學習者母語的一些術語概念,避免用晦澀的語言對術語做過多的解釋,以減輕漢語二語學習者語法學習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