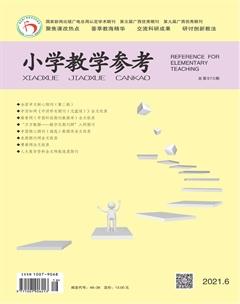語文活動設置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童其貴
[摘 要]語文是一門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學生語言能力的生長,不是依托于豐富的語文知識,而是需要在綜合性、實踐性課程中加以歷練形成的。這就意味著教師要設置契合學生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學習活動,以凸顯語文課程的綜合性、實踐性。教學中,教師要把握特質,設置有思維含量的語文活動;合理遴選,匹配有內在關聯的語文活動;對接認知,設置統整覆蓋的語文活動。
[關鍵詞]語文活動;設置;綜合性;實踐性
[中圖分類號] G623.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7-9068(2021)16-0047-02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明確指出:語文是一門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學生語言能力的生長,不是依托于豐富的語文知識,而是需要在綜合性、實踐性課程中加以歷練形成的。但縱觀當下的語文教學,很多教師并沒有認識到設置語文活動的重要性,或者對語文活動的認知與設置還存在著較大的偏見。這就需要教師及時轉變觀念,積極設置有價值、有意義的實踐活動,為推動學生言語實踐能力的生長助力。
【誤區一】零散膚淺,無法助力能力生長
不少教師對語文學習中的實踐活動存在一個明顯的認知誤區,他們認為在課堂中帶領學生進行學習實踐都是語文實踐活動。如果我們將朗讀、圈畫、思考、交流等教學操作都歸于語文實踐活動,那么這種活動必然是淺層次的。在這些所謂的活動中,學生的思維是逼仄的,他們只能局限于字詞、糾纏于語段、留戀于文本的淺表性知識,獲取的也只是零散的信息資源,并不能將所有的信息都立體化,也就無法將思維推向深刻的層面,導致語文學習的整體性效益大大降低。
比如,教學統編教材六年級下冊《真理誕生于一百個問號之后》一文時,為了讓學生感受作者運用事例來論證中心論點的寫作方法,教師設置了這樣的教學環節:1.整體朗讀課文,初步理解文本內容,劃分“總分總”結構;2.相機概括作者所選用的三個事例,找出三個事例都是通過不斷追問才獲得真理的共性特征;3.再次朗讀課文,回歸作者的寫作思路。
在這樣的教學中,學生雖然經歷了兩次課文整體朗讀,也對文本的內容進行了概括,并進行了統整對比,但對于高年級學生而言,這樣的學習環節并沒有充分調動他們內在的認知意趣和思維,語文活動的真正價值并沒有得到彰顯。
【對策一】把握特質,設置有思維含量的語文活動
皮亞杰說過:“語言是思維的載體。”作者創作文本時,將自身的思維、情感都蘊藏在字里行間,所以在文本閱讀過程中,無論是感知體驗,還是梳理洞察,都需要激活學生內在的思維意識,使之與作者蘊藏在文本中的思維形成同頻共振的學習效果。為此,教師就需要借助學生的原始思維,將學生推向文本的最深處,引領學生在深入實踐中進行體悟和思考,與文本作者進行深入對話。
還是以《真理誕生于一百個問號之后》這篇課文為例,怎樣才能讓學生更好地感受到作者運用事例來論證的方法呢?教師可以針對課文內容,在學生整體把握文本的基礎上,設置這樣的語文活動:首先,從課文中心論點入手,鼓勵學生以目標歸屬為抓手,逆向閱讀,概括作者所選用的三個事例;其次,洞察三個事例與中心論點之間的關系,引導學生以第一個“波義耳發明石蕊試紙”的事例為載體,對作者所描寫的事例進行解構,先從司空見慣的現象入手,然后描寫主人公的質疑追問,接著展現人物的嘗試和實踐,最后獲得真理;再次,由此及彼,擴散輻射,教師鼓勵學生自主閱讀其他兩個事例,并依托“現象—追問—嘗試—真理”的模式,對這兩個事例進行洞察與分析,找準三個事例在創作上的結構特征;最后,鼓勵學生進行言語實踐,借助敘事結構,對三個事例進行復述,在言語思維的運轉和組織下,理清事例與中心論點之間的關聯。
在這一案例中,教師除了關注學生的朗讀和概括之外,所設置的語文實踐活動還包含了對比辨析、解構洞察、復述表達等。這些活動將學生的思維引向了文本語言的內核,改變了淺層性活動的弊端,將學生的認知推向了更高境界。
【誤區二】關注形式,學習效益提升無果
很多時候,由于教師認知偏差和操作失當,常常會使得原本真實的形式成了虛假效果的載體與渠道。這里所謂的“真實”指向于活動形式,如針對某一觀點或者具體的任務進行交流分享時,教師常常會組織學生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展開,學生在交流時合作的形式確實是真實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語文學習活動中學生并不一定是真的學習。比如,很多學生會沉迷于活動的多樣化形式中,有的學生會在活動中跟不上節奏,自身的思維并沒有完全打開,或者來不及打開,活動就已經結束。真實的效果被活動的形式所遮蔽,反而對結果造成了影響。
比如,統編教材四年級上冊《西門豹治鄴》一文所在單元的語文要素是:學會簡要復述。教師在學生整體把握文本之后,要讓學生認識到“簡要復述”是對于重要的內容要復述得詳細些,而對于次要的內容可以復述得簡略一些。一位教師在“懲治惡人”這個環節的教學中,就組織學生以角色表演的方式,關注文本中描寫人物言行的語句。但在具體表演的過程中,很多學生難以真正走進人物內心,而其他學生也容易出現笑場的情況,看似新穎、獨特的形式,對于學生能力的發展卻沒發揮出相應的作用。
【對策二】合理遴選,匹配有內在關聯的語文活動
不同的活動形式所關乎的思維形式也是完全不同的,教師無論是在選擇形式,抑或是操作形式時,都需要關注兩個問題:第一,這樣的活動是否契合這個學段學生內在的認知能力,是否能夠有效喚醒學生的思維意識;第二,這樣的活動,是否與文本所表達的內容密切相關。借助這兩個問題,教師要辯證地考量活動形式與實效之間的關聯,讓學生在深入實踐中進行體悟,從而更好地達成教學目標。
還以《西門豹治鄴》一文為例,所設定的語文要素是“簡要復述”,且不談上述案例中表演形式的最終效果,單從活動形式與所要達成的“簡要復述”這一訓練重點來看,就沒有任何的關聯。復述是用口頭語言對文本信息進行組織與統整,而表演是個體化內容的呈現。對此,教師應改變角色表演的形式,設置鮮活的情境:假如原本已經逃走的鄉親們聽說了西門大人的事情之后,紛紛重新回到家園,向你詢問西門大人是怎樣懲治惡人的,你會怎樣講給鄉親們聽呢?這樣的形式,借助鮮活情境,讓學生轉換角色進行講述,與這個單元的復述要求契合;同時,角色置換的方式將原本傳統狀態下的第三人稱轉變成第一人稱,有助于學生形成鮮明的帶入感,有助于學生靈活地調整自己的認知思維,從而真正促進學生言語實踐能力的生長。
【誤區三】畫蛇添足,活動設置可有可無
很多教師一提到活動就認為是要讓學生動起來,于是很多教師就容易將認知思維局限在固有的教材或者所要教學的內容之中。基于這種模式下的語文實踐活動,的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學生言語關鍵能力的生長,但所關涉的內容和范疇,卻只能停留在固有的層面上,無法真正將學生的認知視野進行擴展。
比如,教學統編教材六年級上冊《夏天里的成長》一文時,教師緊扣“圍繞中心來表達”的語文要素,在學生初讀課文之后,先讓他們交流并確定文本表達的中心句:“夏天是萬物迅速成長的季節。”然后,從文本內容的角度入手,讓學生洞察作者描寫的三個維度:動物、植物、人物。作者為什么要從這三個角度來寫呢?教師設置了語文活動:站立在作者的視角,嘗試借助作者的口氣,將如此構思和選材的用意說出來。
從實踐的效果來看,很多學生都能夠從文本的內容去理解作者設置的用意,也能夠與作者形成認知上的共鳴。但遺憾的是,每個學生所表達的內容完全是課堂正常情況下的師生對話,根本無須借助作者的口吻來表達。這就意味著,教師在這節課中所設置的活動其實是可有可無的,并沒有對學生的思考、交流和表達形成有效的促動。
【對策三】對接認知,設置統整覆蓋的語文活動
鑒于上述板塊的闡述,教師所設置的活動不能僅僅關注其外顯狀態,更為關鍵的是要能夠真正觸動學生內在的思考。因此,教師在選定了語文活動之后,更需要從操作的細節入手,盡可能地與學生的學習實際鏈接起來,真正推動學生言語實踐能力的生長。
以統編教材五年級上冊《太陽》一課為例,教學中,學生從文本語言內容的維度出發,把握了太陽遠、大、熱的特點。但語文教學的最終目標不是讓學生獲取更多的文本知識,而是要在習得知識、統整知識、運用知識的過程中,提升學生的言語實踐能力。鑒于此,教師設置了這樣的活動:設置“天文學家答中外記者問”的新聞發布會情境,組織學生在綜合性吸收文本知識的基礎上,積極收集、悅納、整合課外收集的資料,以“新聞發布會”的形式,由一些學生扮演中外記者現場提問,另一些學生綜合運用課文內容和收集的資料作答。為了防止活動變成知識信息的機械搬運,教師要求“天文學家”在回答問題時,要積極運用從課文中學習到的說明方法。這種以實踐的方式來鞏固積累的表達方法,激活了學生的思維,推動了學生言語表達素養的高效發展。
語文教學不能是零散的環節拼湊,而應該是板塊中的整體推進。因此,教師要認識到語文學習活動的重要性,積極設置有價值、有意義的語文實踐活動,真正推動學生言語實踐能力的生長。
(責編 劉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