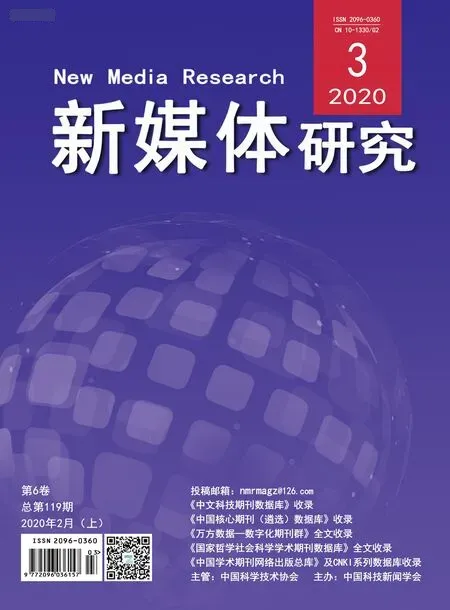移動新聞直播:場域新變下新聞敘事的重構
李古淞
摘 要 移動直播平臺作為新的新聞敘事窗口,勢必會使傳統的新聞敘事場域(場域內的時間、空間、關系)產生新變,由此衍生出新的敘事邏輯與表征邏輯。從敘事場域的變化看,敘事者與受眾形成了平等的交流態勢;新聞敘事的“場域模式”使敘事節奏變得自然平和;敘事空間的互動性滿足了受眾對新聞事件的介入欲望。從敘事方式的變化看,移動新聞直播的敘事動力從“時間”轉變為“懸疑”;全知視角和限制視角相結合的方式,構建出了平等、互相尊重的敘事關系,同時也全面地展現了新聞事件的全貌;觀眾的互動過程成為了新聞敘事內容的一部分。
關鍵詞 移動新聞直播;敘事;敘事策略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03-0008-03
庫爾特·考夫卡認為,個體所發生的每一個行為均會受到其行為發生時,所處場域的影響。場域既包括物理場域,也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其他因素。移動新聞直播作為內容與新場域(移動直播平臺如抖音、快手等)的融合,它給新聞內容的呈現帶來了全新的敘事方式。但在業界的實踐過程中,也出現了內容呈現表象化、敘事邏輯混亂、語態不適等一系列問題。這主要歸因于媒介人員融媒體思維意識的滯后,即采制人員的思維滯后于融媒體時代的發展。以往對于移動新聞直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個案研究或是停留在事物的介紹層面。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意義,但研究內容缺乏扎根性,針對性,實用性較低。因此,本文旨在研究移動新聞直播的新聞敘事場域及敘事方式的新變,并為其未來的發展提出實用性的思路。以此為業界人員提供現實性、扎根性的理論指導。
1 新聞敘事場域的變化
1.1 關系:平等、平視關系的構建
移動新聞直播在敘事主體與用戶(觀眾)之間構建出了平等、自由的交流態勢。用戶通過互聯網的虛擬場景遮蔽了身份、階層的差異,建構出了一個主播與用戶、用戶與用戶之間的平等關系,實現了用戶平等話語權的“自我賦權”。并且在敘事主體與用戶的不斷互動中,這種“自我賦權”會被進一步強化。在移動新聞直播中,現場記者在多數情況下只能以限知視角傳遞現場信息和敘述事件的過程。加之直播過程中的不穩定性、突發性因素,敘述者難以全面的了解、講述事件的全貌及所有細節[1]。因此,記者的信息“壟斷地位”及自身的優越感將逐漸喪失,最終被迫與用戶平視,即用戶獲得了與敘事主體的平等地位。同時,移動新聞直播也在進一步依托手機媒介,從視覺距離(人與手機的視距約為0.3米,這屬于親密距離的范圍)、呈現構圖(親人、朋友式的視頻畫面呈現)及后臺場景(處于后臺場景中,可消解距離過于接近所導致的緊張、焦慮的情緒)等方面,來構建敘述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親密關系。
1.2 時間:自然、平和的敘事節奏
移動新聞直播敘事的“場景模式”使事件的敘事節奏降低。場景模式即故事的時間長度與故事敘事的時間長度等同。概括模式即故事敘事的時間長度小于故事的時間長度[2]。傳統的電視新聞直播常以“概括模式”來敘述整個事件的因果邏輯鏈條,即以省略、停頓以及概括等方式對敘事時長進行壓縮,以此加大敘事跨度,提升敘事節奏。這是由于傳統電視新聞直播的節目形式以及有限的報道資源決定的。但在直播時代,內容的生產與播送不再占用頻譜資源、不受許可限制、不再需要向廣電總局申請以及內容制作的成本大大降低,這就決定了直播敘事無需壓縮話語時長,即實現了故事時間與話語時間的同步。這使移動新聞直播的敘事更加具有“記敘文”的特色,敘事節奏也大幅降低。相對較慢的敘事節奏不僅使新聞事件的敘事有了輕快、自然的起伏,還能夠有效緩解單一敘事帶來的審美疲勞。
1.3 空間:互動、自由的敘事場域
移動新聞直播打破了電視新聞直播的封閉性傳播模式,滿足了觀眾對新聞事件的介入欲望,即與信息輸出者進行互動、溝通的渴望。傳統電視新聞直播的內容輸出屬于封閉性的單向信息流傳播,記者與觀眾位于信息傳播鏈的兩端,處于一種“社交分離”的狀態。兩者在信息傳播中承擔的角色也是固定的、單一的。但移動終端的流量保證和大規模普及,為新聞直播敘事構建出了全新的敘述語境,即一種公開、多元、互動的敘事空間。一方面,平臺給與了記者與用戶自由發言的機會,實現了主動的、自由的“電子民主”。此時,受眾也成為了重要的新聞敘事主體之一。另一方面,場域中敘事主體與用戶、用戶與用戶之間將形成兩個信息的交流場域。這兩個場域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牽制,最終實現用戶活躍度的提升和信息傳播內容的多元化走向,即用戶導致話題內容的無限延伸[3]。需要注意的是,當敘事主體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時,對于同一事件就會產生出紛繁復雜的態度,因此無論是敘事主體或是用戶,都必須對其進行仔細的辨析。
2 新聞敘事方式的變化
2.1 敘事動力:懸念為主要驅動力
移動新聞直播最主要的敘事動力是懸念,即讓懸念帶動對未知真相的探索。懸念是由緊張和疑問這兩個情感要素共同構成的[4]。緊張源于重大事件的影響力,影響力既源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也源于事件發展過程中某一節點或事實的重要性。疑問則源于一種意欲回答問題和閉合開放模式的智利需求[5]。在移動新聞直播過程中,觀眾對事件的疑問具有某種終極色彩,即在事實發生前,一切都是未知的。并且新聞事實的發展事態不斷變化,使觀眾閉合開放模式的智利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由此,一種塵埃未落定之感便不斷促使媒體進行報道。2016年7月,《新京報》通過騰訊新聞客戶端對北京豐臺西路等積水內澇區進行移動新聞直播(北京內澇關乎千萬人的利益),并對人們心存疑慮的北京各區域積水情況、救災信息等情況進行重點直播(不斷消解受眾對事態發展過程中的核心事件的疑慮)。最終此場新聞直播的觀看人數超過了296萬。
2.2 敘事角度:全知視角與限知角度相結合
不同的敘事視角會引起觀眾不同的感知反應和情感效果[6]。礙于版面、時間的限制,傳統的電視新聞直播常以“全知視角”講述新聞。全知視角是一種全景式、全方位描述的大視角,能夠對新聞事件進行深刻的剖析,以此挖掘新聞事件的本質[7]。但這種帶有“俯視性”的視角往往會拉遠敘事文本與受眾之間的距離。使受眾產生壓迫感、緊張感,甚至不信任感。在移動新聞直播中,事件的發生與播送具有同步性,因此“限知”視角是記者講述新聞的主要視角。這種視角能構建出新聞發生的真實、自然的場景,新聞敘述也更容易被觀眾接受。但新聞事件的敘述可能會流于表面化、淺層化。因此在移動新聞直播中,敘事者常以全知視角(這里的全知視角是相對的,是由多維度的限知視角組合而成。)與限知視角相結合的方式講述新聞,即讓觀眾客觀、全面、立體的了解新聞事實的同時,敘述方式也要體現對觀眾的尊重。在2016年7月,騰訊新聞派出“追洪小組”奔赴長江水患的抗洪前線,運用多維度鏡頭對各區域的降水積雨、受災、居民安置以及官兵搶險抗洪等情況進行報道。每個鏡頭都極具親歷感,整個報道也富有全面性、真實感。
2.3 敘事內容:發散性的敘事內容
移動新聞直播的敘事內容是發散性的,既包括新聞事件本身,也包括用戶與用戶、敘事主體與用戶在互動中產生的其他內容。能夠成為敘事內容的有效互動主要有兩類:
第一類是觀眾對新聞直播的內容以及評論區的內容展開的提問與補充。一方面,觀眾能夠對新聞直播呈現出的內容進行有針對性的提問,以此引導新聞敘事的方向;另一方面,新聞直播的受眾可能兼具觀眾、新聞事件當事人及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等多個角色,他們會在評論區中對新聞內容的盲點進行補充。記者對觀眾的問題做出實時的回答,不僅能夠滿足受眾對新聞敘述的參與、介入的欲望,還能夠不斷發現新的新聞線索。
第二類是觀眾在觀看完整個新聞事件后,具有渴望與他人分享內心情緒并得到響應的互動需要。這樣的互動以統一的新聞事實為基礎,極易產生“共情效應”。2016年7月,在“安徽蕪湖隨軍抗洪”的直播報道中,報道了一線官兵在酷熱的高溫下為生命奔波的救援場景,許多觀眾在評論區中為抗洪戰士加油、鼓勁。這種場景既激發了觀眾的愛國情緒,引發“共情效應”,同時也成為了新聞報道的重要內容。
3 移動新聞直播的敘事 發展思路
3.1 敘事邏輯:及時性、層次感的敘事邏輯
在移動新聞直播中,事件的發生與播送具有同步性。因此其內容呈現在單位時間內會出現有效信息密度不足、信息冗長、專業性及內容關聯度較低的情況,非常容易出現“信息泡沫”。因此移動新聞直播在內容的規劃上要“精耕細作”。首先,時間較長的直播應該以直播內容為劃分依據,分階段的設置直播主題,把內容呈現的即時性體現在細節中。其次,可以分階段制定直播預告文本以及可視化的內容總結。直播預告可以對觀眾設置“懸念”,吸引受眾的興趣,增強受眾黏度。可視化總結可以讓不同時段進來的觀眾了解已經播完的內容,彌補稍縱即逝的遺憾。再次,在直播結束后可設置周邊話題,拓展內容傳播的廣度。如新華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國慶閱兵直播報道中,依據實時的直播內容,三次修改直播標題,六次更換直播封面,將內容呈現的即時性體現在細節中。在直播結束后,新華社還積極設置與閱兵相關的周邊話題,以此實現了話題的延續,拓展了信息傳播的廣度。
3.2 敘事場景:“全感官”的在場感
移動新聞直播需要為用戶構建“全感官”的在場感。目前移動新聞直播所采用的主流成像技術為5G+4K+VR、AR等虛擬現實技術,以此增強受眾的“親臨感”。如“武漢洪水VR全景直播”采用航拍與地面拍攝相結合的方式展現南湖地區、漢口江灘等地的全景圖像。觀眾則通過VR眼鏡進行觀看。但這種成像技術依然處于限知的視角。一方面視角單一,盲點較多,不能從整體上觀察事件發生的整個面貌。另一方面,時間相對滯后,時效性較差。但全息圖技術(即一種二維物體上的三維表示)可記錄、呈現物體的形狀、尺寸、對比度及亮度等信息,這將會給移動新聞直播的內容呈現帶來顛覆性的改變。從內容呈現上看,全息圖能夠呈現物體的三維立體影像以及局部的細節信息。從感官上,東京大學前沿科學院研究所研發出了全息圖視觸覺技術,用超聲波將觸覺傳送到皮膚上,由此可讓使用者全感官的接觸全息影像。并且這種圖像呈現技術在使用上更加便利、智能,因此全息圖新聞也終將重新定義未來新聞的輸出形態。
3.3 敘事互動:多樣、精準的互動
在移動新聞直播中,傳統的互動場景和互動形式拘泥于評論區及文字。形式單一的互動場景、平淡無味的交流形式使場景中的社交互動效果大大折扣。因此需要從技術和形式上構建新型的社交互動場景,以此增加用戶黏性,提高直播的影響力、傳播力。在技術層面上,首先運用大數據、算法等智能技術對用戶評論區的數據進行采集、分析以及整理。一方面,挖掘觀眾不同的需求點,對于已經解釋過的、介紹過的信息應給與及時的推送。對于受眾新形成的、具有焦點性的信息需求,需及時反映給直播記者及團隊,記者和團隊也將根據需求點進行敘事方向及策略上的調整。另一方面,可對用戶進行“畫像”,了解不同觀眾的喜好,即內容類型、接受方式的偏好。以此有針對性的進行信息的個性化推送。在形式上,可以在直播中設置網絡投票、答題彈窗、VR特效等互動模式,增加內容互動的“可玩性”,以此增強觀眾的興趣。以大數據、算法為基礎的互動模式,不僅搭建了用戶與記者之間溝通的橋梁,還能夠極大地提升互動的有效性。
4 結語
以移動新聞直播為基點探討科技對敘事的賦能,其意義不在于移動新聞直播本身,而是通過“以小見大”的方式,來窺視媒介敘事發展的潮流,即媒介技術決定敘事能力,敘事方式又促進媒介技術的發展。以科技為驅動力,“物”與“物”的碰撞、融合勢必會帶來新的生產方式,也會極大地延展內容呈現的可能性。至此,媒介人員能力的現實指向不再是“采、寫、編、評”,而是一種融媒體的實踐操作能力與思維。因此,跨領域、跨學科的職業技能的綜合建設已經成為了當下必須研究的現實命題。
參考文獻
[1]石艷紅.21世紀的網上新聞工作者[J].新聞通訊,1999(4):8-9.
[2]孫振虎,唐中科.敘事學視角下的電視現場直播信號:以CCTV日本地震報道中對NHK直播信號使用為例[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1(6):56-59.
[3]詹晨林.移動新聞直播的敘事特點與語態創新[J].新聞戰線,2017(16):86-88.
[4]聶欣如.電影懸念的產生:以影片《精神病患者》和《化裝殺人》為例[J].世界電影,2004(5):22-40.
[5]羅伯特·C·艾倫.重組話語頻道[M].麥永雄,柏敬澤,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49.
[6]羅鋼.敘事學導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58.
[7]楊先順.試論新聞寫作的敘事角度[J].新聞大學,2001(2):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