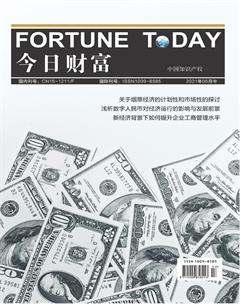魔術的可版權性研究
潘韻倩
按照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魔術是一種作品類型,屬“雜技藝術作品”而受著作權法的保護。然而,這種作品的是如何界定的,法律對其保護范圍是哪些卻沒有明確規定,為此,學者們也有不同的看法。有觀點認為,僅用著作權法并不能很好地保護魔術的核心的部分,魔術中秘密的部分不符合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的要求。為此,有必要對魔術是否符合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的定義進行討論,厘清著作權法對魔術的保護范圍,并進一步探討魔術的法律保護出路。
一、魔術的著作權保護爭論
2001年,我國修訂《著作權法》,首次將“雜技藝術作品”列為保護對象。為此,學者們開始爭論雜技、魔術和馬戲是否符合著作權法要求的作品。魔術是依據科學的原理,運用特制的道具,巧妙綜合不同學科領域的智慧,以不斷變化讓人捉摸不透而帶給觀眾驚奇體驗的表演藝術。又因為魔術的變幻莫測現象背后的原理和秘密不為觀眾所感知,有學者提出,魔術的這個特點使其不滿足作品的要求,而不應列為著作權法中的作品。將魔術視為著作權法上的作品,在其他國家中是罕見的。我國關于魔術作品的著作權糾紛案件雖少,但確實存在引人關注的案例。
(一)我國首例魔術作品著作權糾紛案
我國發生的第一起涉及“雜技藝術作品”的訴訟,是一名以色列的魔術師起訴他人未經許可使用其設計的“狼蛛魔術”。法院認定,原告魔術在呈現給觀眾的形體動作、姿勢的編排上體現了一定構思,整體上屬于《著作權法》所保護的魔術作品,并認為魔術里的被技巧、裝置掩蓋的動作由于沒有辦法被觀眾所客觀地感知,所以不可以受著作權法的保護。至此,法院把“魔術作品”限定在“魔術中呈現給觀眾的形體動作、姿勢的表達”。
(二)學者爭鋒
針對上述案件的判決,有學者提出質疑,著作權法已經規定了“舞蹈作品”,那么,在排除了魔術技巧的情況下,“魔術作品”這一種“形體動作、姿勢的表達”與“舞蹈作品”之間關系要如何處理,它是否值得在“舞蹈作品”之外另設一種與之并列的作品類型呢。對于這個問題,可以總結為目前的著作權法將魔術列為一種作品的類型是否合理,其是否應作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予以保護。筆者通過閱讀文獻,整理出學者們對于這個問題的三種看法和理由。
第一種觀點是以王遷為代表的反對派,認為魔術不符合作品的要求,也不應該作為一種獨立的作品類型,應當在著作權法的保護對象中刪除這一項。理由如下。
一是從作品構成要件角度展開。魔術的內容通常可以劃分為一明一暗兩部分。明是指觀眾可以感知的背景音樂、舞蹈、魔術師臺前的動作等,暗的部分是觀眾所看不到的魔術的原理、魔術師的隱秘動作及其對道具、機關的使用。后者因觀眾無法感知,而使魔術這種藝術形式存在表達的不完整性,不符合作品須能為觀眾所感知的要求,因而這部分不屬于著作權法保護的內容。而前者又與其他舞臺藝術形式沒有區分的必要。
二是從著作權法不予保護的對象論證。根據思想表達二分的原則,著作權法不保護魔術的創意及原理、操作方法、魔術中的手法及技巧,否則會打擊和窒息魔術創作的熱情。
三是,就魔術作品而言,由于魔術背后的秘密設置,使得他人抄襲和本人維權舉證都難以實踐。在作品是否侵權的比對中,司法實踐里常使用的“接觸加實質相似”的方法,在比對魔術作品是否侵權的時候就會失靈。一是很難證明實質接觸。二是很難證明實質相似。哪怕魔術師看到了他人表演的相同的魔術,也不容易確定他人使用了和自己一樣的手法。實際中,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來達到相同的魔術效果。
第二種觀點是以張丹丹為代表的支持派。認為魔術符合作品的構成要件,能夠是獨立完成的,具有一定的創新的高度,具有獨創性。而且那些具有藝術性、可供觀賞的成分是具有可復制性的,其意義只在于強調作品不能停留于主觀狀態,只要用文字腳本、表演將魔術表現出來,使之不再是魔術師頭腦中的精神活動,這時也就具有了可復制性。另外還認為魔術可以獨立存在,它和音樂、舞蹈作品在表演上以及由之產生的藝術美感上是存在差異的。此外應澄清魔術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范圍,可以免去反對派的爭論。
第三種是以學者王勉青為代表的部分肯定觀點。認為魔術的部分內容可以構成作品。其具有獨創性部分可以主張著作權保護。學者承認魔術是作品,其獨創性和可復制性的認定和第二種觀點相同。魔術在滿足一定的條件的時候確實可以成為作品,不過即使是這樣,除去魔術衍生品比如魔術道具等等,魔術往往還有很多方面:魔術原理、技巧、動作造型、表演等,其中并非所有元素都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
在討論此問題的時候,應針對魔術的不同部分進行,而非一概而談,也因為這樣,對魔術的保護應該是全方面的,多種法律手段的,而不應僅局限于著作權法。
二、魔術的可版權性分析
整理上述學者們的思想交鋒,本文擬從以上的討論點出發,分別從這幾個方面進行論述。分析魔術的可版權性問題的思路在于,探究魔術是否符合作品的構成要件,但往往魔術的構成復雜,性質具有復合性,則還要分析魔術是由哪些部分構成的,再一一探討這些部分是否符合作品的要求。魔術由很多部分組成:原理、技巧、腳本、道具、動作、造型、表演等等。根據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條規定,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從中可得知,要成為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必須具備獨創性,并且是能夠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另外,一些智力成果是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因此還需探討魔術是否落入此范圍。
(一)獨創性的分析
對于獨創性,其中的“獨”,即獨立創作,源于本人。“創”是指一定水準的創造高度,勞動成果需要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創造性”,即能夠體現作者獨特的智力判斷與選擇,展示作者的個性并達到一定的創作高度要求。當創作者用自己的構思,利用各種道具和動作,來進行自己的魔術表達,這種動作編排的創造性可以滿足作品“創”的要求。在此基礎之上,魔術創作者如果是自己獨立創作的,或在前人的基礎上創作出更好的作品,那也可以滿足“獨”的要求。
(二)可復制性的分析
對于可復制性,魔術的動作編排,可以用文字、圖畫等有形形式表現出來,從而為觀眾所感知;可復制性還要求作品能夠被復制,讓使用人可以制作出和原作品一樣的復制品,換句話說,是可以實現從一份到多份。不少反對派的觀點在此認為,因為魔術的生命就在于神秘,恰恰是那些不能公開的魔術奧秘,導致魔術不能被復制,因為表演的不完整性,從而也無法滿足重復再現的要求。本文對這種觀點持保留的意見。魔術的秘密不能公開,并不是因為客觀上的不能,任何一個魔術,只要創作者、表演者愿意,完全可以將其背后的奧妙示人。這些奧妙的構成,或是科學原理的應用,或是創作者的奇思妙想對道具物品的安排使用,或是精心的動作言語構思,在客觀上,這些因素都能夠被記錄和復制的,例如文字、圖像、視頻等。在魔術表演中魔術師的各種形體、動作等表演活動或者魔術師以腳本的方式將魔術固定到載體上,都證明了魔術是具有可復制性的。另一方面,在主觀上,表演人、創作者為了保持魔術的神秘性及商業價值,絕大多數情況下選擇不公開魔術的奧秘部分。但是這不是阻卻魔術的可復制性的理由,魔術也并不因此而喪失可傳播、可被感知的基礎。至于什么情況下公開魔術秘密,是否適宜用著作權法來保護,其中價值的取舍,將在下文中討論。
(三)著作權法不保護的對象之排除
關于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根據思想表達二分的原則,著作權法不保護思想,操作方法、技術方案和實用功能。討論至此,需要對魔術構成進行拆分并逐一分析。思想與表達的分界并不能簡單斷言,對所有類型的作品一刀切,但是在思想與表達的“金字塔”中,總會存在一個分界線。具體到魔術這一作品類型中,魔術的總體構思、核心創意、變幻原理,越是靠近這一方向的內容,越有可能屬于思想的范疇;魔術的動作編排、手勢、舞蹈、言語引導,則更有可能屬于表達的范疇。操作方法、技術方案和實用功能也屬于思想的范疇。對于魔術來說,其中用到的操作方法、手法和技巧,不少觀點不加分析便下結論,認為這符合了著作權法意義上所說的操作方法和技術方案,所以魔術這部分應被排除在著作權法保護的范圍之外。
著作權法中所言的操作方法、技術方案和實用功能等,是指具有實用因素的、會產生思想和表達混同的內容,而魔術中所指的操作方法、手法和技巧,未必和這是同一回事。魔術中的思想領域,更可能是構思以某一些科學原理實現某種藝術效果,而在實現這個藝術效果的過程中,可以有很多創作者個人的判斷選擇和安排,在某一時刻展現還是收藏某物品,在此時刻而非彼時刻進行某一動作,在魔術某一刻的進程中進行何種明的動作或暗的動作,說什么樣的話語引導或迷惑觀眾等等。這些都是魔術創作者為實現其魔術構思而進行的個性化的表達,不同創作者之間能夠有很大的選擇和創作空間,并不必然產生如果某一創作者壟斷了它,則讓其他后來者無法創作的后果。魔術中的操作、手法和技巧是魔術中非常細小的單元,就如文學作品中的字、詞一樣。而對這些最小單元遣詞造句,寫成段落、篇章,則具有了作者個性的烙印,能夠成為作品。同理,魔術對手法、技巧這種基本單元的編排,也是創作者的個性化表達,達到了獨創性的要求,并且是足夠具體的。如同文學作品中的單個字詞不能受到著作權法保護一樣,作為魔術基本單位的操作、手法和技巧當然也不是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原因并不是它們過于抽象,接近思想的范疇,而是它們作為作品的長度還不足以構成一個具有獨創性的表達。當它們以體現作者個性的編排方法組織起一部有足夠長度的魔術作品的時候,是能夠成為作品的。在我國的魔術著作權糾紛案中,判決所指出的魔術作品系指“魔術中呈現給觀眾的形體動作、姿勢的表達”,也不排除是魔術中的操作和手法的組合和編排這種理解方式。
綜上所述,魔術能夠具有獨創性。而且在可復制性上,也能滿足作品的要求。魔術作品并不因為其專有權人不愿意公開的魔術奧秘,而在可復制性、可為他人所感知的要件上有所缺陷。完整的魔術作品,包括其中奧秘的部分,依然具有被他人所感知、傳播的可能性。著作權不保護思想、操作方法和技術方案,但魔術的操作手法和技巧僅為基本組成單元,足夠數量的基本單元的編排組成的整個魔術的動作組織,是創作者思想的個性化具體表達,符合作品之要求。至此,魔術是符合著作權法上的作品的構成要件的。
三、魔術各組成部分的著作權保護之取舍
盡管從理論上論證了魔術符合著作權中作品的定義,我國《著作權法》也規定了魔術是作品。但是在實踐中,依然很少看到關于魔術的著作權糾紛案例。因為提起魔術作品的侵權訴訟,這會使得公眾進一步了解魔術關鍵部分,從而使之失去吸引力。經過利弊的權衡,理性的權利人往往選擇謹慎訴訟。這一現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著作權法的保護規則與魔術的特點無法內在統一,因此用著作權法保護這種它,不是最好的途徑。
作為魔術奧秘的一部分的各種操作、手法和技巧的編排,盡管不阻礙魔術成為著作權法中的作品,且能夠讓著作權人有權控制他人的復制行為,但這種奧秘一旦公開,能夠為他人所感知、復制、傳播,似乎更不利于其商業價值的實現。探尋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將某種藝術形式確認為作品后,能夠讓其創作者從中享有專有權,獲得名譽和財富,鼓勵創作者和后來者進一步創作,從而使文化成果更豐富繁榮。當魔術的著作權人發現,著作權的并不是保護魔術的最完善的方法時,有必要存在其他的渠道維護魔術的商業價值。無論是訴諸商業秘密的方法進行保護,還是參照域外經驗,承認魔術表演者在魔術表演中的創造性勞動,即使這沒有達到著作權法中作品的高度,對表演者作廣義的理解,對表演非作品的表演者也給予表演者權的保護,還是利用專利權保護魔術道具,輔之以行業規范和職業操守規范同行之間魔術揭秘行為,這些法律保護進路都很值得進一步討論和參考。
但是,提供給魔術創作者以著作權保護的方法是不可缺少的,無論權利人進一步選擇以哪一種或幾種方式進行保護。對魔術秘密的部分的著作權保護方法的取舍,取決于權利人利益的衡量、價值的判斷等。魔術作為一種獨立的作品類型,也是有其存在的必要。除卻魔術的秘密部分的內容,也不能完全由其他的作品類型單一地或組合地替代,魔術作品類型有其單獨存在的價值。
四、結語
魔術作品因為其秘密的部分不宜公開,致使其在可復制性、可為他人感知上受到質疑,同時因為著作權不保護操作方式、技術方案等,可能會得出魔術作品能夠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范圍有限且沒有必要作為獨立作品類型的結論。但是,魔術的可復制性是客觀存在的,不因主觀上的不愿意公開而有所減損,因此也是可以完全為他人所感知的。魔術作品中足夠多的操作、手法和技巧以一定方式的編排組合,成為能夠體現創作者個性和獨特選擇的足夠具體的表達,就能夠滿足著作權法上作品的要求。魔術滿足作品的構成要件,是作品。但是基于魔術的神秘性和商業價值等考慮,權利人可以選擇多種法律方式對魔術作品進行保護。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 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