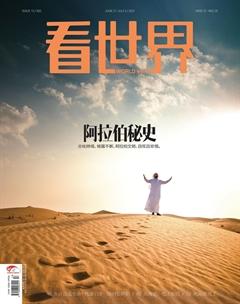曾經滄海阿拉伯
趙博淵

阿拉伯之名,意為“沙漠”。
阿拉伯半島原住民稱自己的居住地為“沙漠島”。這一稱謂概括了該區域的地理特征:中部大片沙漠,東、南、西瀕海,是個半島。而在北方內夫德沙漠更北邊,是被譽為“新月沃地”的兩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拉丁語音譯,意為“日出之地”)。
兩河流域的沃野適合農耕,黎凡特水陸要沖適合貿易,因此該區域很早就誕生了先進文明。

兩河流域的沃野適合農耕,圖為2021年6月8日,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農民收獲土豆
“真阿拉伯人”“純阿拉伯人”
曾幾何時,阿拉伯半島氣候宜人,但逐漸變化成熱帶沙漠氣候,環境劣化,生產力難以提升,雖地域遼闊,但人口居住分散,部族林立,文明演進落后于古埃及和波斯一大截。
就像城鄉差距懸殊的大背景下,農村青年為擺脫貧困,通常選擇源源不斷奔赴繁華都市打工一樣,源于阿拉伯半島的閃米特諸族——阿卡德、阿摩利、迦勒底、迦南、腓尼基、阿拉米、希伯來(以色列、猶太)——也不得不用腳投票,選擇遷徙移民,并繁盛于兩河或黎凡特地區。
這種遷徙呈現出一定的周期性,常常是上一波在外剛混得風生水起,下一波已經在蠢蠢欲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牧人部落沖出了半島,征服富庶繁華的文明世界,然后沉醉于溫柔鄉里,但沒有人愿意反哺故鄉,即使回歸,也是亞述式的鐵血手段。
有人外出闖蕩,自然有人閉門留守。留下來的阿拉伯原住民,被沙漠地帶大致南北分割成了遵循兩種社會經濟模式的兩類人:以定居經商為主的西部、南部農商人口,和以游牧掠奪為主的中部、北部游牧人口。前者被稱作“綠洲之民”,后者自稱“帳篷之民”,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貝都因人。
“綠洲之民”人口眾多,依托與波斯、羅馬、拜占庭等帝國的過境貿易而富裕,但軍事上很弱小;“帳篷之民”雖然人口不多、組織渙散,但依靠過硬的馬上功夫,常被周邊大國雇來作戰,軍事上畸形強大。
阿拉伯半島儼然成了一個蒸鍋:當生產力低下和人口激增不平衡導致的社會壓力上升突破閾值,通常通過對外人口遷徙實現“泄壓”。這一模式維持了數千年,運轉自如。
盡管半島社會在不平衡和再平衡之間輪番切換,但惡劣的地理環境和不穩定的人口流動,并不利于統一民族的形成。而隨著羅馬、波斯等域外大國的統治固化,上古時代行之有效的老套路,面對旨在遏止閃族人溢出擴散勢頭的新移民政策,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形象點說,鍋蓋封死了,壓力亟待宣泄。
這真是內憂外患:一方面,阿拉伯各部落及部落內部貧富差距擴大,加劇了內部傾軋,部落爭戰和血族仇殺不斷;另一方面,域外大國間的戰爭經常波及阿拉伯半島,甚至直接侵略半島,危及原住民的基本生存。
然而,憂患之間又見機遇:雖然域外大國壓制了閃族人外溢,但半島原住民經大浪淘沙后成分反而更加純粹,民族意識覺醒,出現了“真阿拉伯人”“純阿拉伯人”的自我認知。先前只是地理概念的阿拉伯半島,終于冒出了民族一體化的思想萌芽。
沒有伊斯蘭,就沒有阿拉伯
阿拉伯民族一體化的星星之火,最先出現在宗教領域。
/雖然域外大國壓制了閃族人外溢,但半島原住民經大浪淘沙后成分反而更加純粹,民族意識覺醒。/
半島的多神教、偶像崇拜、原始信仰林立的宗教格局,作為半島一盤散沙的政治分裂現實的集中體現,成為統一派先驅的優先開刀對象。現實中,也有希伯來人創立的一神制的猶太教和基督教提供寶貴經驗。
如果說公元6-7世紀的哈尼夫清修運動僅僅是反多神、崇一神的先聲,那么稍后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則將之組織化、系統化和實踐化。

先知穆罕默德(中)與軍隊
事實上,穆罕默德曾參與過哈尼夫清修。區別在于,興起于經濟最發達的漢志(音譯“希賈茲”,即瀕紅海地區)的哈尼夫派,主張奉宗教中心麥加的古萊西部落主神為唯一真神;反倒是根正苗紅、正經出身于古萊西部落的穆罕默德,與所屬集團決裂,創立了完全獨立的伊斯蘭教。
白紙之上方好作畫,這一橫空出世、獨立于所有偶像神之外的新信仰,不僅規避了紛爭,更憑借意為“順從、平和”的教名和“平等、大同、止殺”的綱領主張,迅速獲得上至貴族、下到黔首的共同擁護。
在一神教的精神指引下,穆罕默德在麥地那建政,采用了迥異于腐敗的世俗政權,且更為高效的政教合一式的宗教公社政體。而在與麥加舊貴族僵持的同時,穆罕默德派出使節分赴半島各部吸收信徒。集中于半島中央核心地帶內志(音譯“納季德”)的貝都因人被教義吸引,站隊到穆罕默德一邊。
有了半島最強武力投靠,穆罕默德輕松順利地統一了阿拉伯半島主體部分。阿拉伯半島諸部經伊斯蘭宗教爐火淬煉,終于融合成為一個統一的阿拉伯民族。
穆罕默德在統一半島后病故,但新興的阿拉伯民族余勇可賈。繼任哈里發們接過了伊斯蘭“圣戰”的大旗,貝都因人的鐵蹄終于沖出半島,踏上了征服世界之旅。
分裂速朽的帝國
憑借高度機動的龐大騎兵,和政教合一的高效體制,阿拉伯人狂飆突進、摧枯拉朽,創造了直追前人亞歷山大大帝的軍事奇跡,甚至觸角延及歐洲的伊比利亞半島,最終在諸多大國的尸骸之上,建立起地跨亞非歐的阿拉伯大帝國。
沖出半島、征服世界的阿拉伯人,從未有過治理如此遼闊疆域、眾多人口和多種族的經驗,只能在征戰中學習,積攢經驗。
宗教、軍事和商業,成為阿拉伯人捆綁各區域文明的三大紐帶:以強大軍事為基礎,宗教賦予教徒各種特權以瓦解被征服者的反抗意識,商業提供經濟收益以提升被征服者的向心意識。
概而言之就是,“不聽話就挨打,跟著你有肉吃”。
令阿拉伯人始料未及的是,最引以為傲的宗教紐帶,偏偏成為最先松弛的那一個。
毋庸置疑,阿拉伯人高效的傳教對大征服事業助力良多,但也存在巨大bug:為減少進軍阻力,賦予穆斯林各類特權,尤其是免稅一條,惹得被征服地人民趨之若鶩。然而,當遍地都變成穆斯林時,帝國則面臨稅源枯萎的尷尬局面。于是乎,阿拉伯人只能選擇言而無信,由此引來被征服地民眾的反噬。
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引以為傲的政教合一體制,在穆罕默德死后就遭遇了原則性挑戰。圍繞著最高權位哈里發職務,身兼地方總督身份的教內大佬不惜兵戎互見,直接導致伊斯蘭教大分裂,以及神權共和制、軍事民主制向家族世襲制的體制轉變。宗教的無上權威性受到損害,帶來意識形態領域的失分和現實政治的持續內耗。
接下來,是軍事分封制對帝國根基的侵蝕和分裂。
阿拉伯人戰時匯聚成軍,宛如驚濤洪流,令人震怖;戰后化整為零,以接收大員身份分赴各處,如同洪水掠過沙地,瞬間被吸收干凈。這樣雖對開疆拓土有利,但阿拉伯人面臨前人亞歷山大大帝未曾克服過的政治難題——少數征服者如何有效治理大多數被征服者?若一味倚賴根正苗紅的阿拉伯人,則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管控必定鞭長難及,本土化治理是必然選擇;同時,阿拉伯人棄武加入官僚隊伍,則無法保障兵源充足。
在治理結構的選擇上,阿拉伯人思慮顯然不及手下敗將波斯人深沉,而是本著論功行賞的簡單心理,選擇了蘊含離心主義傾向的軍事分封制。此制的弊端,早在立國之初倭馬亞篡政時就已露崢嶸,一待普及,封疆大吏軍政兩手抓兩手硬,中央控制力日益松弛。
/為填補阿拉伯本族人分流帶來的人力資源缺口,朝廷選擇了波斯人治政理財、突厥人當兵打仗。/
而在中央,為填補阿拉伯本族人分流帶來的人力資源缺口,朝廷選擇了波斯人治政理財、突厥人當兵打仗。后者的“古拉姆”制度,促進了國家軍隊私兵化,反過來為地方割據推波助瀾,甚至于連哈里發也淪為突厥近衛軍肆意廢立的傀儡。
商業功能萎縮,同樣導致中央對地方控制力松弛。
“阿拉伯征服”將東西方陸地商路連為一體,不僅降低關稅成本,更將沿途各地方置于同一商業體系中來。問題是,中國唐朝自安史之亂后,關中凋敝,長期倚賴南方江淮地區的經濟輸血,首都經濟圈輻射力驟降,活力四射數百年的西北絲綢陸路,迅速讓位給海上商路。然而,海上商路興旺固然保障了阿拉伯人的商業收益,但船運點對點的物流模式無助于強化陸上各地的經濟聯系。最終,占帝國東部半壁江山的中亞,回歸到了過去游牧王國林立的舊格局。
如果說阿拉伯人是怒濤、是洪流,那么被征服文明就是原本干涸的河床溝壑,它們盛載了怒濤,也馴化了洪流。盡管帝國分裂速朽,但阿拉伯人畢竟因帝國肇興而開枝散葉于遠比半島更為廣闊的天地間。只是,部分阿劃白人后來被文明程度更為先進的被征服者同化、稀釋,更因宗教分歧而加劇了民族內部的分化。

1904年美國圣路易斯世界博覽會,貝都因人在耶路撒冷展區舉行婚禮游行
平庸,但不平靜
公元1258年,蒙古西征軍攻陷巴格達,處死了末代哈里發穆斯臺綏木,阿拉伯帝國滅亡。
早在歐洲十字軍入侵之前,阿拉伯帝國的可轄之地僅剩首都巴格達一隅之地,與同期內有宦官專權、外有藩鎮割據的中國唐朝可謂難兄難弟。哈里發的主角光環變得黯淡,伊斯蘭世界的舞臺轉屬大小埃米爾、蘇丹們。憑借這些非阿拉伯籍諸侯,阿拉伯帝國安然渡過了十字軍危機,卻沒能逃過蒙古的鐵蹄。
阿拉伯帝國哈里發的死,意味著此時伊斯蘭世界再無共主,兵強馬壯者皆可為之。然而,不管如何折騰,玩家始終是突厥人,阿拉伯人只是被動的脅從者,再要么蜷縮在半島老家庸碌度日,直到有一天伊斯蘭世界的新霸主——奧斯曼土耳其人找上門來。
突厥系出身的奧斯曼土耳其,因為地理位置的關系,早期傾注于對歐攻勢和稱霸地中海上,對阿拉伯世界的注意力長期放在以埃及、敘利亞為核心的環地中海地帶,直至16世紀對歐、海上連連遇阻,才開始轉向伊斯蘭世界的內陸。渙散的阿拉伯人完全不敵土耳其人,除了摩洛哥和阿曼因為地緣位置敏感免遭吞并外,悉數被土耳其納入囊中。
主仆易位,阿拉伯人的不甘自不待言。而對于土耳其人來說,領有阿拉伯世界,意味著人口結構驟變,阿拉伯人一躍成為帝國境內最大族裔,如何治理須慎之又慎。
務實的土耳其人選擇了本土化策略,除了敘利亞這樣的“近畿重地”,對阿拉伯世界各區賦予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權。理論上,本土勢力越強大或是離帝國核心越偏遠,被賦予的治權就越大。前者典型如埃及,后者典型如內志。相對寬松的政策,加上同屬遜尼派,阿拉伯人對土耳其人的惡感不甚強烈,甚至認為奧斯曼官員的直接管理,比阿拉伯酋長們的治理套路更好。
這種折衷主義的治理策略,預埋了分離主義的種子。且不論心活眼亮的埃及,就連貧困閉塞的內志也不安于室。內志作為貝都因人的聚居地,向來被公認為最具阿拉伯氣質的地區。正是在這片窮鄉僻壤的大漠深處,誕生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瓦哈比派。
瓦哈比派以伊斯蘭正宗自居,將包括遜尼、什葉等主流派別統統視作叛教者,叛逆如斯卻奇跡般地獲得了內志酋長沙特家族的支持——因為野心勃勃的沙特家族需要為自身軍事行動提供宗教詮釋,將對手打上“叛教者”的紅字簡單粗暴,但在貝都因人的世界行之有效。
阿拉伯世界平庸,卻從不平靜。世界里不平靜,世界外更不平靜。進入18世紀,歐洲列強在與奧斯曼帝國的競爭博弈中漸占上風,土耳其人的邊疆危機拉開了序幕。
重視商路的英法,將勢力楔入阿拉伯半島沿海,起初是設置據點,而后逐步蠶食。半島上的阿拉伯接應者,也在等待擺脫奧斯曼統治的契機。
現代阿拉伯國家的誕生
進入19世紀,奧斯曼帝國全面沒落,危機全面加劇。外有俄羅斯鯨吞在北,英法蠶食在南,歐洲大革命帶來了工業時代的先進成果和民族國家的思想理念,在帝國內部產生了一系列反應。

沙特阿拉伯麥加大清真寺,在它的背后吊塔林立
/內志作為貝都因人的聚居地,向來被公認為最具阿拉伯氣質的地區。/
為應對危機,埃及首先進行了洋務運動。其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意圖被英法聯手撲滅,但埃及仍舊成為帝國內部“時代變革”的旗手。
作為阿拉伯發源地的半島也深受影響,民族主義熱情被點燃。沙特家族統一內志,于1811年首建王國;瓦哈比派的極端排他性,引來土耳其人的鎮壓,但奧斯曼帝國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掌控江河日下,已是不爭的事實。
反奧斯曼統治的理念自16世紀半島被吞并起,就一直貫穿于阿拉伯世界,只是想法很多,做法較少。阿拉伯人一度打算利用宗教旗幟團結整個伊斯蘭世界,但因宗教內部分歧根深蒂固難以消弭,只得作罷,改弦更張鼓吹起了阿拉伯民族主義。
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基本訴求,是建立獨立、統一,涵蓋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國家。假設該訴求付諸實施,那么奧斯曼帝國也就剩不下多少家當70感覺危險迫近的土耳其人,對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嚴防死守,刀來槍往數十年,矛盾愈加激烈。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成功提供了大好機遇。為抗擊同屬德國陣營的土耳其,英國選擇在阿拉伯世界推波助瀾。阿拉伯人抓住契機,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大起義,配合英軍戰局,以爭取民族獨立。但實際上,除了已被歐洲列強控制的奧斯曼非洲行省,大起義真正席卷的區域,僅限黎凡特和阿拉伯半島。
教祖穆罕默德所屬的哈希姆家族和信奉瓦哈比派的沙特家族兩相呼應,前者催生了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后者以姓為國名建立了沙特阿拉伯。
至此,現代阿拉伯半島國家的雛形,已然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