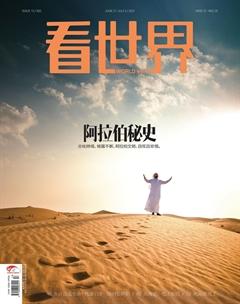阿拉伯世界為何不統一?
趙博淵

1981年埃及總統薩達特遇刺
因以色列反擊哈馬斯而全面爆發的新一輪巴以沖突,僅持續11天就迅速停火,回歸和平。關于沖突的動機眾說紛紜,有美國黑幕論,有內塔尼亞胡野心說,以色列軍方甚至指責伊朗暗中操縱。中東局勢向來復雜詭譎,面對此次號稱7年來最嚴重的巴以沖突,敘利亞之外阿拉伯諸國表態之克制,甚至還不如非阿拉伯的土耳其來得強硬,令人稱奇。
外界的刻板印象是,阿拉伯人因為不團結,才會被以色列屢屢以小擊大。然而,阿拉伯人的身份更多注重部落血統,對于更廣泛區域的利益并不那么重視。縱觀阿拉伯歷史不難發現,除去中世紀大征服時期政教合一的大團結,大部分時間里阿拉伯世界力量分散才是常態。
該選擇哪種政體?
阿拉伯世界并非鐵板一塊,存在諸多差異:地理上,可分成北非、地中海東岸、兩河、半島、海灣五個板塊;經濟上,可分成產油國和非產油國;人口結構上,可分為純阿拉伯國家和混合民族國家;宗教上,可分為遜尼派、什葉派等。
但最大的分歧在于政治——既有君主制,又有共和制。一般來說,前英屬殖民地最大限度保留了君主制,而前法屬殖民地通常采用共和制。
一戰期間的“阿拉伯大起義”,摧毀了奧斯曼帝國在阿拉伯半島的統治,但那些領土既未統一,甚至都未獲獨立。戰后,約旦和沙特以外,許多阿劃白人地區成為英法的托管地。送走病夫般的土耳其,又迎來巨龍般的英法,半島阿拉伯人可謂是驅狼進虎。
英法當時自有不容放棄阿拉伯半島的理由。除了傳統的地緣政治考慮,最大的誘惑就是石油。自1908年在伊朗西南首次勘探到石油后,阿拉伯國家陸續都有發現石油,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內燃機的問世,使得以石油為主的液態燃料成為主流能源。沉淪數百年的阿拉伯半島,重新變成了戰略要地。
托管局面直到二戰后才真正改變。二戰削弱了英法,至1950年代,除去少數邊角旮旯,東起波斯灣、西至非洲西北角,一個獨立的阿拉伯世界出現在世人面前。
獨立問題解決了,阿拉伯人很快發現,統一是遠比獨立更困難的課題。譬如,假設阿劃白世界統一,該選擇哪種政體?

阿拉伯世界(黃色區域)
阿拉伯人仿佛一夜回到“大征服”后的歷史十字路口:如何將多個民族、信仰、政治、經濟基礎不同的異質文明,整合到同一國家框架內?彼時,有伊斯蘭教這一黏合劑,問題是伊斯蘭教早已內部分成無數教派,黏性大大不足,更遑論阿拉伯諸國各有利益訴求,小國只求平安度日,大國都想成為現代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國家,難免生出齟齬。
埃及的統一嘗試
在推動阿拉伯一體化的過程中,埃及是最早吃螃蟹的那個。
歷史上,成功抗擊歐洲十字軍、蒙古西征軍的阿尤布王朝、馬穆魯克王朝,均出自埃及;近代阿拉伯世界自我變革最早、反抗土耳其人最力的也是埃及。埃及有著充足的實力和威望,行此非常之事。
1945年,在埃及首倡下,阿拉伯聯盟于開羅成立。阿盟成立后,積極對付由美英安插進來的異質勢力以色列。
對抗以色列,帶有延續反殖民、彰顯阿拉伯力量的意味;應對巴勒斯坦問題,更成了塑造阿拉伯一體化的煉金爐。
埃及1952年由君主制改為共和制后,在軍人掌權下愈加活躍,對外頻頻組織對以戰爭,對內則就阿拉伯一體化作出各種嘗試。
1958年,埃及與敘利亞組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這個糾合了共和國和君主國的松散邦聯,僅僅存在3年就因為埃及人的霸權主義而解散,但埃及仍保留該國名至1972年。
相形之下,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國就顯得沉默許多。這些君主國本是一戰前后第一波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角,但與英國的密切關系令它們名譽掃地,而二戰后英法介入巴勒斯坦問題,更讓君主國背負了政治原罪。埃及作為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大國,1952年棄君主制改共和制,正是這一思潮的集中表現。
就在埃及嘗試“聯合共和國”的同年,作為回應,源出哈希姆家族的約旦和伊拉克王室,組建了“阿拉伯聯邦”。但這一年伊拉克發生軍事政變,推翻了國王。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是阿拉伯泛區域民族主義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六日戰爭”慘敗不僅僅是軍事問題,更醞釀著深刻的政治危機。作為阿拉伯核心國的埃及喪師失地,空耗國力,對阿拉伯一體化事業的熱情大減。此戰后,美蘇取代英法成為左右本區域局勢的域外黑手,格外打臉當初倡導不結盟運動的埃及。
盡管6年后,埃及為收復1967年的失地發動了第四次中東戰爭,但最終卻是拜美國調停,靠和平談判才拿回西奈半島。此后多年,埃及因“對以媾和”被阿拉伯世界視為叛徒,阿拉伯一體化于它已是無心、無力、無顏以對的奢望。
泛區域民族主義退潮
埃及之后,強人薩達姆執政的伊拉克,接過阿拉伯泛區域民族主義的衣缽。
冷戰結束前后,對阿拉伯世界而言,如果說兩伊戰爭抗擊什葉派波斯人還算大快人心,那么為石油吞并科威特純屬同室操戈,令人齒冷。海灣戰爭時歐美大兵堂而皇之進駐、科威特人簞食壺漿以迎的場景,訴說著阿拉伯泛區域民族主義的衰落和退潮。
如果排除全面復古的泛伊斯蘭主義成分,脫胎自伊斯蘭文化傳統、經近代國家主義強化的阿拉伯泛區域民族主義,不乏可取之處。然而,伊斯蘭主義是漫長的農牧封建時代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傳統智慧,國家主義卻是近代歐美工業化時代的產物,兩者間天然存在抵觸,難以兼容。

1945年,阿拉伯聯盟于開羅成立

1958年,埃及與敘利亞組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作為阿拉伯核心國的埃及喪師失地,空耗國力,對阿拉伯一體化事業的熱情大減。
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普遍避重就輕地選擇了一鍋燴,因而在政治實踐中充滿矛盾感,缺乏可操作性。國家工業化改造順利時,國家主義壓制伊斯蘭主義占據上風,一旦工業化改造受挫,必遭伊斯蘭主義反噬。1981年埃及總統薩達特遇刺事件就是范例:宗教極端分子行刺時,直斥“法老”薩達特反伊斯蘭。
令人憂慮的是,冷戰晚期起,隨著阿拉伯各共和國先后陷入經濟、社會危機,國家主義弱化,泛伊斯蘭主義抬頭。泛伊斯蘭主義者自詡完美,喜歡抱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習慣于將問題歸咎于外界。而坐在油田上致富的幾個君主國,則異曲同工地將經濟成功歸因于真主對虔誠穆斯林的回報。執牛耳者沙特甚至金元開道,致力于瓦哈比教派的意識形態輸出。
21世紀的今天,科技革命、經濟全球化極大豐富了阿拉伯世界的社會經濟生活,阿拉伯泛區域民族主義式微,但伊斯蘭主義+國家主義=阿劃白民族主義這一公式似乎并未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