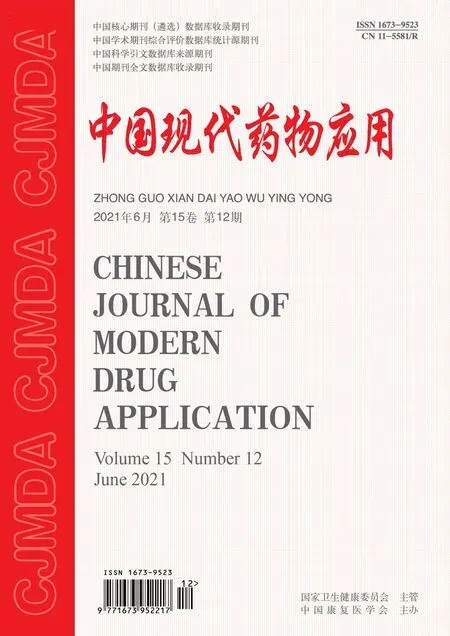PGⅠ、PGⅡ、胃泌素-17在萎縮性胃炎及胃癌中的診斷價值
李擁寧 楊進興 陳彩玲
胃癌是消化道的常見惡性腫瘤,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發病率較高。現階段,受到生活節奏變快、工作壓力增大、人們飲食結構改變、幽門螺桿菌感染等因素的影響,我國胃癌發病率不斷升高,并呈現日益年輕化趨勢[1]。因胃癌早期常無特異性癥狀,極易與常見消化道疾病相混淆,如胃潰瘍、胃炎、慢性胃部疾病等[2],因此,導致胃癌早期診斷率較低,很多患者發現胃癌時多已處于晚期,臨床預后較差,死亡率較高。在臨床實踐中,胃部黏膜的嚴重萎縮狀態被認為是胃癌疾病的癌前階段,對萎縮性胃炎的篩查與早期治療是當前胃癌防治的重點。臨床診斷萎縮性胃炎常用方法為胃鏡檢查,但借助胃鏡進行篩查、隨訪存在一定痛苦,且費用較高,患者依從性較差。血清學指標檢測則具有無創、操作簡便、患者依從性好等優勢,在發達國家已開始用于胃癌早期與胃癌癌前病變的篩查及預測[3]。但在我國,血清學指標檢測用于胃癌、癌前病變篩查診斷的研究較少。有研究表明精確預測胃癌的生物標志物有利于在早期發現胃癌疾病,早期積極對癥支持治療有助于改善患者預后,增加患者生存率,降低患者死亡率[4,5]。胃生物學標志物包括PG 和胃泌素,其中PG 可反映胃黏膜結構,胃泌素可反映胃黏膜功能,兩者聯合檢測可識別胃黏膜的變化情況,如胃黏膜炎癥或胃黏膜萎縮等。近年來國內外許多研究均認為血清中PG 含量、胃泌素含量檢測可用于萎縮性胃炎及胃癌的篩查與診斷。基于此,本研究納入新胃癌量表評分在12~25 分之間的中高危人群60 例作為研究對象,對患者血清PGⅠ、PGⅡ、G-17 水平進行分析,重點分析血清PG 聯合G-17 水平檢測診斷萎縮性胃炎與胃癌的應用價值。具體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20 年1 月~2021 年1 月期間至本院體檢及門診收治的30~50 歲健康體檢者及慢性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首先應用新胃癌量表評分進行胃癌風險分層,納入新胃癌量表評分在12~25 分之間的中高危人群60 例,根據胃鏡檢查、病理組織學檢查結果分為慢性非萎縮性胃炎組(25 例)、萎縮性胃炎組(28 例)、胃癌組(7 例)。所有納入對象均對本研究知情同意,所有數據結果均用于研究,不涉及個人隱私,符合醫學倫理。三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三組患者一般資料對比(n,)

表1 三組患者一般資料對比(n,)
注:兩組對比,P>0.05
1.2納入及排除標準
1.2.1納入標準 ①新胃癌量表評分在12~25 分之間;②年齡30~50 歲,性別不限;③合并慢性萎縮性胃炎史、胃十二指腸潰瘍史、胃息肉史;④家族直系親屬存在消化道惡性腫瘤病史者;⑤合并吸煙史、重度飲酒史,喜食高鹽飲食或煎烤油炸食物者;⑥胃鏡檢查前30 d 未服用抗生素、質子泵抑制劑或胃黏膜保護劑等藥物;⑦14 d 內未服用抗凝藥物者,如阿司匹林、華法林等。
1.2.2排除標準 ①合并重要臟器功能嚴重不全者;
②合并嚴重精神障礙者;③合并凝血功能障礙者;
④資料不全者;⑤既往已明確有消化道惡性腫瘤病史者;⑥存在活動性感染性疾病者;⑦妊娠期女性。
1.3檢測方法 三組患者均行靜脈穿刺取空腹血樣5 ml,將血液樣本置入光管中,血液凝固后離心分離10 min,而后置于≤25℃室溫下待測,血液樣本檢測由上海蘭衛醫學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東莞蘭衛醫學檢驗室完成。檢測三組PGⅠ、PGⅡ、G-17 水平并比較。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 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t 檢驗,多組計量資料采用F 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胃癌組、萎縮性胃炎組患者PG Ⅰ水平低于慢性非萎縮性胃炎組,G-17 水平高于慢性非萎縮性胃炎組,且胃癌組患者PG Ⅰ水平低于萎縮性胃炎組,G-17 水平高于萎縮性胃炎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胃癌組患者PG Ⅱ水 平(18.7±3.8)μg/L 高于萎縮性胃炎組的(15.2±3.4)μg/L 和慢性非萎縮性胃炎組的(14.1±4.7)μg/L,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慢性非萎縮性胃炎組和萎縮性胃炎組患者PG Ⅱ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三組血清PGⅠ、PGⅡ、G-17 水平比較()

表2 三組血清PGⅠ、PGⅡ、G-17 水平比較()
注:與慢性非萎縮性胃炎組比較,aP<0.05;與萎縮性胃炎組比較,bP<0.05
3 討論
胃癌是我國第二大常見癌癥,且死亡率較高,高死亡率主要與晚期發現有關。因此,早期發現與治療對于改善胃癌患者預后、降低胃癌死亡率至關重要。現階段,臨床迫切需要早期胃癌檢測的有效方法,但國內尚無全國范圍內的胃癌篩查計劃,早期檢測主要依靠機會檢查。在臨床實踐中,胃鏡檢查和胃活檢組織學檢查是篩查診斷胃癌的金標準,但使用胃鏡檢查篩查高危人群的效率較低,費用較高,受檢者依從性較差。故臨床亟需一種可作為胃鏡檢查之前的初始預篩查方法,對有胃癌風險的人群進行早期風險分層,并進一步在先前定義為高風險人群中識別出真正的胃癌高風險人群[6]。本組研究中納入新胃癌量表評分在12~25 分之間的中高危人群60 例作為研究對象,該量表是中國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聯盟醫院歷時超過2 年的研究,制定的適合中國人群特點的、可操作性強的、經濟可行的胃癌高危人群風險預測模型,可以提供較好的預篩選性能。選定的納入對象經胃鏡和病理學檢查進一步確診為慢性非萎縮性胃炎25 例,萎縮性胃炎28 例,胃癌7 例。
PG 即胃蛋白酶前體,人胃黏膜細胞主要產生兩種不同形式的PG,即PGⅠ、PGⅡ。有研究表明,成人幽門螺桿菌感染者PGⅠ、PGⅡ值升高,血清PGⅠ、PGⅡ是診斷幽門螺桿菌感染的有效指標[7]。分子生物學研究和流行病學研究均表明,在胃癌發生、發展中幽門螺桿菌感染有著重要的參與作用。Charvat 等[8]建立基于幽門螺桿菌感染和胃萎縮的胃癌預測模型,并發現了導致胃癌發生率升高的危險因素。血清G-17含量降低一直被認為是胃竇萎縮的重要血清學標志,與胃竇萎縮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近年來,大量研究表明血清G-17 可用于評估萎縮性胃炎的發生和發展情況[9]。故本研究重點對納入研究對象的血清PGⅠ、PGⅡ、G-17 水平進行分析,旨在評估血清PG 水平與血清G-17 水平檢測在萎縮性胃炎與胃癌診斷中的應用價值。在胃部疾病的不同階段,血清PGⅠ、PGⅡ水平也呈現出不同的表達。目前血清PGⅠ、PGⅡ檢測在胃部疾病的初篩和治療監測中應用廣泛,一線臨床人員通常將其稱為血清學活檢指標。在輕度或中度萎縮性胃炎患者中,因受到幽門螺桿菌感染誘導的胃泌酸腺體刺激,血清PGⅠ、PGⅡ水平可呈現高表達。在嚴重胃部萎縮患者中,因假幽門腺細胞取代了位于胃底下部的主細胞,主細胞中PG 基因受損,喪失分泌PGⅠ的能力,血清PGⅠ水平可呈現低表達,這一點在本研究中也得到證實。
本組研究中慢性非萎縮胃炎組與萎縮性胃炎組血清PGⅡ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胃癌組血清PGⅡ水平顯著高于慢性非萎縮胃炎組與萎縮性胃炎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目前,臨床普遍認同非賁門部胃癌在癌變前,胃黏膜會經歷炎性病變、腺體萎縮、腸化生、異型增生等演變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伴隨炎癥的不斷進展,血清PGⅠ、PGⅡ水平也呈現高表達水平,其中血清PGⅡ的升高尤為明顯。伴隨胃部病變的進一步加重,因幽門腺細胞取代了主細胞,導致血清PGⅡ水平繼續升高。本組研究結果提示血清PGⅠ、PGⅡ在慢性非萎縮性胃炎、萎縮性胃炎、胃癌三種不同胃黏膜病變中差異顯著,其中萎縮性胃炎、胃癌患者血清PGⅠ水平低于非萎縮性胃炎組,胃癌組血清PGⅡ水平顯著高于慢性非萎縮性胃炎與萎縮性胃炎患者。
本組研究中慢性非萎縮性胃炎患者血清G-17 水平呈低表達,明顯低于萎縮性胃炎、胃癌患者。胃泌素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胃腸激素,主要由胃竇的G 細胞分泌,十二指腸及空腸上段的G 細胞也可分泌胃泌素,促進胃酸分泌、調節胃腸運動、促進胃黏膜細胞增殖是胃泌素的主要生理功能[10]。臨床研究表明G-17 水平升高與胃癌有明顯的相關性,在胃底癌、胃體癌中G-17 水平升高更為明顯。對于萎縮性胃體炎患者胃炎,血清G-17 水平的高表達對胃黏膜癌變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本次研究中,與慢性非萎縮性胃炎患者對比,萎縮性胃炎、胃癌患者血清G-17 水平顯著升高,證實了上述觀點。但值得注意的是,胃竇部黏膜萎縮會導致G 細胞減少,血清G-17 水平在抑制和刺激狀態下均表現出低水平,故血清G-17 低水平可能為萎縮性胃竇胃炎診斷的重要血清標志物。本研究中萎縮性胃炎患者較慢性非萎縮性胃炎患者血清G-17 水平升高,可能與納入病例中萎縮性胃竇炎患者較少有關。故在萎縮性胃炎、胃癌的臨床診斷中,還應聯合血清PGⅠ、PGⅡ進行共同篩查。
綜上所述,血清PGⅠ、PGⅡ、G-17 是萎縮性胃炎及胃癌診斷中的重要生物學標志,其中低血清PGⅠ可作為鑒別胃萎縮及胃癌高危人群的重要標志,血清G-17 在一定程度上也提示了萎縮性胃炎、胃癌的高危風險。血清PG 與G-17 聯合檢測可作為萎縮性胃炎及胃癌普查中一類簡便、有效的指標,對于血清PG、G-17異常者可進一步行胃鏡檢查,結合病理結果確定有無胃癌發生,從而提高胃癌的早期診出率。但本研究樣本量有限,今后仍需繼續開展多中心、大樣本量的深入研究,進一步分析三者單獨或聯合診斷胃癌的有效性。血清PG 與G-17 檢測在萎縮性胃炎及胃癌篩查中具有積極意義,可作為萎縮性胃炎、胃癌診斷中的重要生物學標志進行推廣使用。